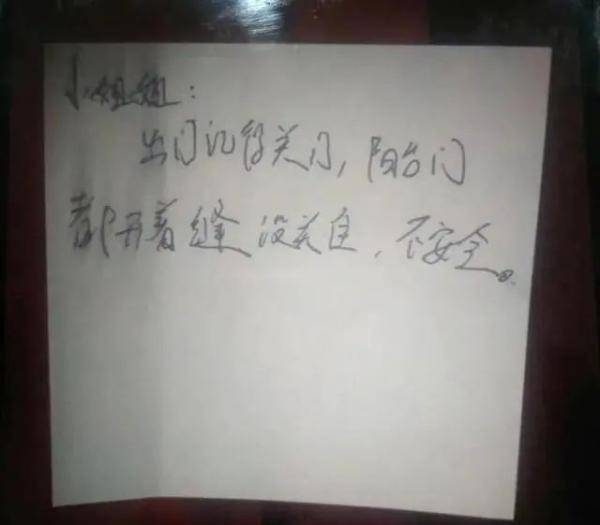中国古代写本学的特点( 五 )
中国古代写本学对古代文学写本整理与研究的促进作用表现在很多方面 , 以下仅以敦煌写本为例略作说明 。
古代文学写本与传世印本的一个显著差异就是写本保存了大量当时流行的俗体字和异体字 。 由于这些俗体字和异体字流行于数百年乃至一千多年前 , 已久不见于传世的印刷文本 , 所以学界最初面对这些俗异字体 , 可以说茫然不知所措 , 以致早期的敦煌文学写本释文 , 如《敦煌变文集》等 , 在文字辨认方面出现了很多错误 。 一百多年来 , 敦煌写本学取得最大成就的领域就是对敦煌俗字的整理和研究 。 早年给前辈学者造成困扰的绝大部分俗体字和异体字 , 现在多数都得到了正确的释读 。 如敦煌写本斯4398《降魔变文》中有“舍利弗者 , 是我和尚甥” 。 这个“”字 , 在《伍子胥变
文》中也曾出现 。 早年罗振玉认为“”是“甥”之别体字 , 现在我们可以依据《龙龛手鉴新编》等记录写本时代俗字的工具书 , 轻松地将其确定为“外”之俗体字 , 系涉下文“甥”而成之类化俗字 。 又如斯328《伍子胥变文》中之“乘肥却返 , 行至小江” 。 “肥”原作“” , 《敦煌变文集》将“”校改作“肥” , 现在我们依据记录写本时代俗字的《干禄字书》等工具书 , 可知“”即“肥”之俗字 , 不是错字 , 可以直接将“”释作“肥” 。 类似例证甚多 , 不胜枚举 。 总之 , 敦煌俗字研究的进展 , 极大地推进了敦煌文学写本的整理工作 , 使敦煌文学写本的释文更加接近原貌 。推荐阅读
- 明星|男明星的发型有多重要,多位代言人中国风小视频,邓伦真是一言难尽
- 姐姐|恭喜!中国又一游泳名将公开恋情,女友身材高挑长相貌美气质极佳
- 基努·里维斯|冒天下之大不韪!又一位艺人人设崩塌,中国的钱他是别想挣了
- 张常宁|中国女排第一美女即将大婚!提前穿“婚纱”,婆婆神似董明珠,家缠万贯
- 谷爱凌|“天才少女”谷爱凌: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坐拥千万独栋别墅
- 陈情令|2021泰网评选TOP1中国男星!周生如故火爆全泰,陈情令CP烧不完
- 赵丽颖|赵丽颖穿中国风旗袍,尽显中国传统经典之美!秒变性感小女人
- 国籍|女模钱凯丽:拒绝承认中国血统,却想在中国捞金,遭全体网民抵制
- 钟汉良|她是中国第一美人,连续8年荣登全球百美榜,如今36岁低调结婚
- 长津湖之水门桥|中国内地女星之性感的王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