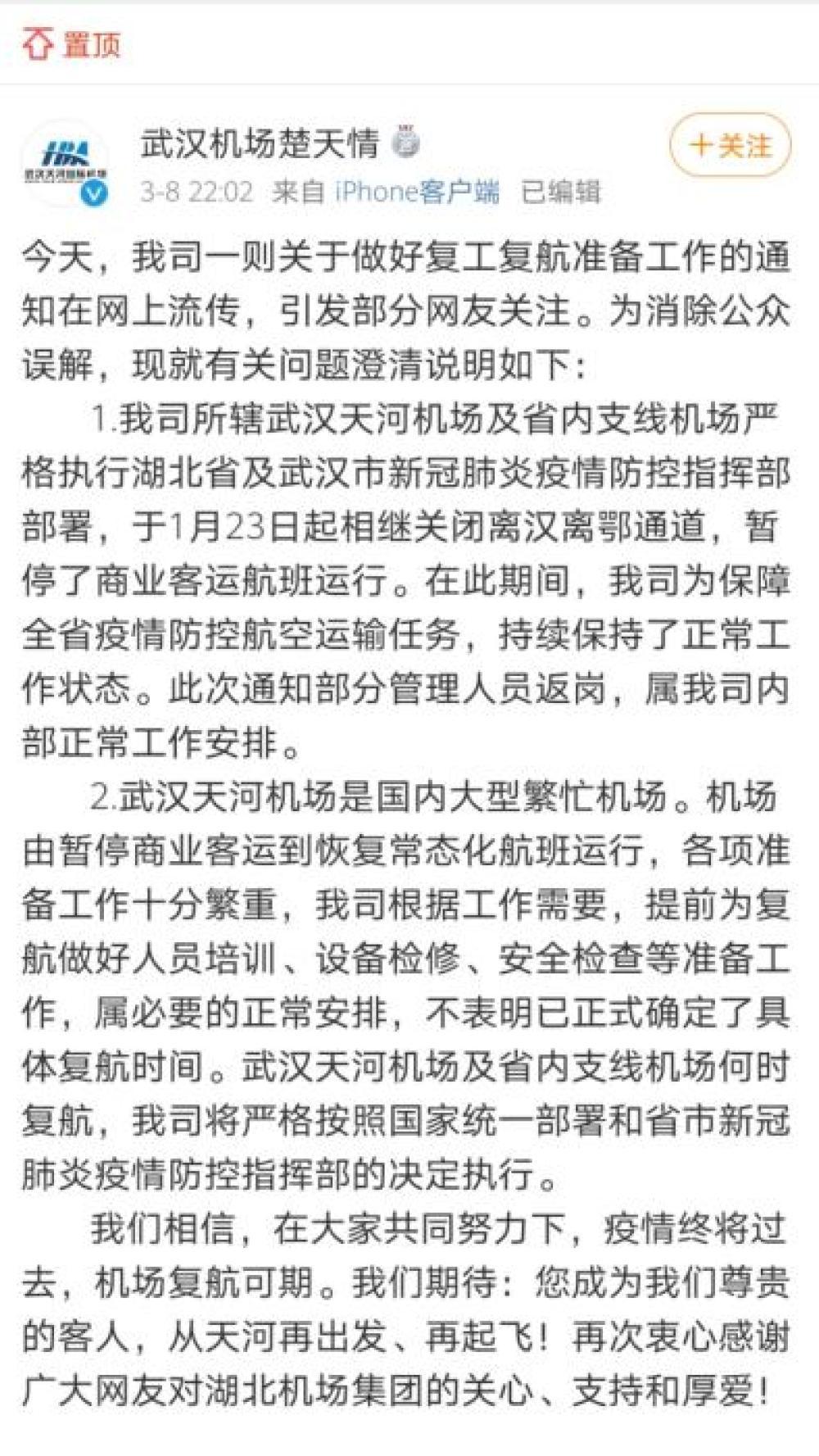гҖҗж–ҮжұҮжҠҘгҖ‘е°ҡй•ҝиҚЈпјҡиүәж— еқҰйҖ”пјҢе”Ҝжңүж”Җзҷ»( дәҢ )
гҖҖгҖҖвҖңйӮЈдёӘе№ҙд»Ј пјҢ еӨ§е®¶йғҪз»ҸеҺҶзқҖзӨҫдјҡе·ЁеҸҳгҖҒиЎҢдёҡеҸҳеҠЁ пјҢ вҖҳе”ұжҲҸзҡ„вҖҷжҲҗдёәж–Үиүәе·ҘдҪңиҖ…гҖҒдәәж°‘иүәжңҜ家гҖҒеӣҪ家зҡ„дё»дәә гҖӮ иҝҷдёҚд»…жҳҜз§°и°“зҡ„еҸҳеҢ– пјҢ жӣҙжҳҜж”ҝжІ»ең°дҪҚгҖҒеҝғзҗҶи®ӨеҗҢзҡ„ж”№еҸҳ пјҢ иҝҷжҳҜд»ҺжңӘжңүиҝҮзҡ„гҖҒжү¬зңүеҗҗж°”зҡ„иҮӘиұӘж„ҹдёҺдәІеҲҮж„ҹ гҖӮ вҖқе°ҡй•ҝиҚЈеӣһеҝҶ пјҢ зҲ¶дәІе’Ңе“Ҙе“Ҙ们еҸӮеҠ дәҶз”ұи§Јж”ҫеҢәж–Үиүәе№ІйғЁжҺҲиҜҫзҡ„жҲҸжӣІи®Ід№ зҸӯ пјҢ иҝһзқҖдёӨжңҹ пјҢ ж•ҙж•ҙеӣӣдёӘжңҲ гҖӮ жҜҸж¬ЎеӯҰд№ е®Ңеӣһ家 пјҢ 他们йғҪдјҡ第дёҖж—¶й—ҙдёҺ家дәәгҖҒеҗҢиЎҢеҲҶдә«еҜ№ж–°дёӯеӣҪж–Үиүәж”ҝзӯ–зҡ„зҗҶи§Ј гҖӮ иҖҢе№ҙе°‘зҡ„е°ҡй•ҝиҚЈеңЁиҘҝеҚ•й•ҝе®үеү§йҷўи§ӮзңӢдәҶз§Ұи…”гҖҠиЎҖжіӘд»ҮгҖӢе’ҢгҖҠз©·дәәжҒЁгҖӢ пјҢ еӨҙдёҖеӣһжҺҘи§ҰжқҘиҮӘи§Јж”ҫеҢәзҡ„ж–ҮиүәдҪңе“Ғ пјҢ еҸ—еҲ°дәҶеүҚжүҖжңӘжңүзҡ„йңҮж’ј пјҢ з•ҷдёӢжһҒе…¶ж·ұеҲ»зҡ„еҚ°иұЎ гҖӮ иҝҷз§ҚеҚ°иұЎ пјҢ йҖҗжёҗжҲҗдёәдёҖз§ҚзғҷеҚ° пјҢ ж·ұж·ұең°еҪұе“ҚдәҶд»– пјҢ и®©д»–жҮӮеҫ—жҲҸжӣІжүҺж №дәәж°‘гҖҒеҸҚжҳ зҡ„жҳҜдәәж°‘зҡ„еҝғеЈ° гҖӮ
гҖҖгҖҖз”ҹжҙ»еӨ©зҝ»ең°иҰҶең°еҸҳеҢ–зқҖ пјҢ жўЁеӣӯд№ҹеҗ‘д»–ж•һејҖдәҶжҖҖжҠұ гҖӮ е°ҡй•ҝиҚЈ10еІҒжӢңеёҲеҮҖи§’еҗҚ家йҷҲеҜҢз‘һжӯЈејҸеӯҰиүә пјҢ д»–еҰӮйҘҘдјјжёҙең°жұІеҸ–иүәжңҜе…»еҲҶ пјҢ жӣҙз”ЁжңҖеӨ§зҡ„зғӯжғ…жӢҘжҠұз”ҹжҙ»гҖҒжӢҘжҠұдәәж°‘ гҖӮ 1959е№ҙ пјҢ е°ҡй•ҝиҚЈжқҘеҲ°йҷ•иҘҝзңҒдә¬еү§йҷў гҖӮ еңЁз”ҹе‘ҪдёӯжңҖз№Ғзӣӣзҡ„е№ҙеҚҺ пјҢ д»–ж·ұе…ҘеҶңжқ‘гҖҒе·ҘеҺӮе’ҢйғЁйҳҹ пјҢ еҲ°з”°й—ҙең°еӨҙдёәд№ЎдәІд»¬жј”еҮә пјҢ дёӢе·Ҙең°гҖҒеӯҰзғ§зӮӯ пјҢ дҪ“йӘҢз”ҹжҙ» пјҢ дҪңе“ҒгҖҠ延е®үеҶӣж°‘гҖӢгҖҠе№іжұҹжҷЁжӣҰгҖӢзӯүзҡҶеҫ—зӣҠдәҺиҝҷдәӣз»ҸеҺҶ гҖӮ 1965е№ҙ пјҢ еү§еӣўжҺ’жј”еҸҚжҳ й“Ғи·Ҝе·Ҙдәәз”ҹжҙ»зҡ„зҺ°д»Јдә¬еү§гҖҠз§ҰеІӯй•ҝиҷ№гҖӢ пјҢ д»–еҲ°еҳүйҷөжұҹз•”зҡ„й“Ғи·Ҝе»әи®ҫе·Ҙең°дёӢз”ҹжҙ» пјҢ дёҺе·Ҙдәә们дёҖиө·зқЎвҖңжіҘзӘқеӯҗвҖқ пјҢ дёҖиө·еҸӮеҠ еҠ еӣәи·Ҝеҹәзҡ„еҠіеҠЁ гҖӮ ж”№жҲҸж—¶ пјҢ еҢ…жӢ¬д»–еңЁеҶ…зҡ„18дҪҚдё»еҲӣжқҘеҲ°жҲҗжҳҶй“Ғи·Ҝе·Ҙең° пјҢ е°ҡй•ҝиҚЈдҫқж—§дҪҸе·ҘжЈҡгҖҒй’»йҡ§жҙһ пјҢ з”ҡиҮізҲ¬дёҠй«ҳй«ҳзҡ„жЎҘеў©дёҺе·Ҙдәә们дёҖиө·е№ІжңҖеҚұйҷ©зҡ„йҮҚжҙ» гҖӮ еңЁйӮЈдёӘзҒ«зғӯзҡ„е№ҙд»Ј пјҢ д»–зҡ„жұ—ж°ҙжҙ’еңЁдәҶйӮЈдёҖеқ—еқ—зғӯеңҹдёҠ гҖӮ
гҖҖгҖҖвҖңжҲ‘иҝҮеҺ»зҡ„з”ҹжҙ»жҳҜиө°вҖҳдёүй—ЁвҖҷвҖ”вҖ”家门гҖҒеү§еӣўй—Ёе’Ңеү§еңәй—Ё гҖӮ ж·ұе…Ҙе·ҘеҶңе…өд»ҘеҗҺ пјҢ жҲ‘иў«еҹәеұӮж°‘дј—зҡ„иү°иӢҰе’Ңжңҙе®һжү“еҠЁдәҶ пјҢ жј”е‘ҳе°ұеә”иҜҘдёҺ他们жү“жҲҗдёҖзүҮгҖҒиһҚдёәдёҖдҪ“ гҖӮ иҝҷж ·жј”еҮәжқҘзҡ„жҲҸ пјҢ жүҚиғҪзңҹе®һең°еҸҚжҳ 他们зҡ„з”ҹжҙ»д»ҘеҸҠ他们зҡ„жүҖжҖқжүҖжғігҖҒжүҖзҲұжүҖжҒЁ гҖӮ вҖқе°ҡй•ҝиҚЈи®ӨиҜҶеҲ° пјҢ жҲҸжӣІе·ҘдҪңиҖ…иҰҒж„ҹзҹҘе’Ңзҙ§иҙҙдәәж°‘зҡ„еҝғ пјҢ жүҚиғҪеҲӣдҪңеҮә满足他们зІҫзҘһйңҖжұӮзҡ„дҪңе“Ғ гҖӮ
гҖҖгҖҖеҝғдёӯвҖңдёҚе®үеҲҶвҖқеӣ еӯҗеңЁдёңжө·д№Ӣж»Ёеҫ—д»ҘвҖңеӯөеҢ–вҖқ
гҖҖгҖҖзҲ¶дәІе°ҡе°Ҹдә‘иҝҮдё–еҗҺ第дёүе№ҙ пјҢ жҲ‘еӣҪжӢүејҖдәҶж”№йқ©ејҖж”ҫзҡ„еәҸ幕 пјҢ жҳҘйЈҺеҗ№жӢӮзҘһе·һеӨ§ең° пјҢ д№ҹжҺҖеҠЁдәҶиҘҝеҢ—зҡ„жҲҸжӣІиҲһеҸ° гҖӮ еҪ“ж—¶зҡ„е°ҡй•ҝиҚЈе·ІжҳҜдә«жңүзӣӣеҗҚзҡ„иҠұи„ёеӨ§е®¶гҖҒеҪ“д»ҒдёҚи®©зҡ„вҖңеҸ°жҹұеӯҗвҖқ пјҢ еңЁеҪ“ең°жӢҘжңүдә”е®ӨдёҖеҺ…зҡ„еӨ§еұӢе’Ңдё“иҪҰ гҖӮ ж—ҘеӯҗиҝҮеҫ—зәўзҒ« пјҢ еҸҜд»–еҝғйҮҢдә§з”ҹдәҶдёҖдёӘвҖңдёҚе®үеҲҶвҖқзҡ„еҝөеӨҙ гҖӮ
гҖҖгҖҖд»ҺйӮЈдёӘе№ҙд»Јиө°иҝҮжқҘзҡ„дәә пјҢ еӨ§еӨҡжңүиӢҸиҒ”ж–ҮеӯҰжғ…з»“ гҖӮ е°ҡй•ҝиҚЈжңҖзҲұгҖҠй’ўй“ҒжҳҜжҖҺж ·зӮјжҲҗзҡ„гҖӢдёӯзҡ„дёҖж®өиҜқвҖ”вҖ”вҖңдәәжңҖе®қиҙөзҡ„жҳҜз”ҹе‘Ҫ гҖӮ з”ҹе‘ҪеұһдәҺдәәеҸӘжңүдёҖж¬Ў гҖӮ дәәзҡ„дёҖз”ҹеә”еҪ“иҝҷж ·еәҰиҝҮпјҡеҪ“д»–еӣһйҰ–еҫҖдәӢзҡ„ж—¶еҖҷ пјҢ дёҚдјҡеӣ дёәзўҢзўҢж— дёәгҖҒиҷҡеәҰе№ҙеҚҺиҖҢжӮ”жҒЁ пјҢ д№ҹдёҚдјҡеӣ дёәдёәдәәеҚ‘еҠЈгҖҒз”ҹжҙ»еәёдҝ—иҖҢ愧з–ҡвҖқ гҖӮ з№Ғзҗҗзҡ„еү§еӣўз®ЎзҗҶе·ҘдҪңзүөжүҜдәҶе°ҡй•ҝиҚЈеӨ§йҮҸзІҫеҠӣ пјҢ з”ҡиҮіи®©д»–ж— жҡҮйЎҫеҸҠиҲһеҸ°еҲӣдҪң гҖӮ 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жҲҸжӣІжј”е‘ҳ пјҢ жІЎжңүжҲҸжј”гҖҒеҲӣдҪңеҒңж»һ пјҢ е°ұжҳҜвҖңзўҢзўҢж— дёәвҖқ гҖӮ еҗҢж—¶ пјҢ д»–д№ҹеңЁдёәдә¬еү§зҺ°зҠ¶жҸӘзқҖеҝғ пјҢ з”өеҪұгҖҒз”өи§ҶгҖҒиҜқеү§ пјҢ з”ҡиҮіе…„ејҹеү§з§ҚйғҪеңЁиҝӣжӯҘ пјҢ е”ҜзӢ¬дә¬еү§д»Қ然д»ҘвҖңеӣәе®Ҳдј з»ҹвҖқиҮӘеұ…иҖҢиёҹи№°дёҚеүҚ гҖӮ 1987е№ҙ пјҢ дёҖе№ҙеҸӘжј”дәҶ6еңәжҲҸзҡ„е°ҡй•ҝиҚЈ пјҢ з»ҲдәҺиҖҗдёҚдҪҸиҖ—иҙ№иүәжңҜз”ҹе‘Ҫзҡ„вҖңе®үзЁівҖқ гҖӮ д»–жҖҖжҸЈгҖҠжӣ№ж“ҚдёҺжқЁдҝ®гҖӢзҡ„еү§жң¬ пјҢ еҗ¬зқҖиҙқеӨҡиҠ¬жӮІжҖҶзҡ„гҖҠе‘ҪиҝҗгҖӢ пјҢ зҷ»дёҠз»ҝзҡ®зҒ«иҪҰдёҖи·ҜеҚ—дёӢ пјҢ ж•Іе“ҚдәҶдёҠжө·дә¬еү§йҷўзҡ„й—ЁзҺҜ гҖӮ вҖңйӮЈж—¶зңҹзҡ„жҳҜеүҚйҖ”жңӘеҚң пјҢ дҪҶе°ұжңүйӮЈд№ҲдёҖиӮЎеӯҗеҠІе„ҝжғіеҒҡзӮ№дәӢжғ… пјҢ иҰҒи·іеҮәиҝҷжұӘе№ійқҷзҡ„жёҠж°ҙ гҖӮ жҒҚжғҡй—ҙ пјҢ жҲ‘з”ҡиҮіеңЁжғі пјҢ иҝҷ究з«ҹжҳҜжҲҸеү§иһҚе…Ҙж—¶д»Јзҡ„вҖҳе‘ҪиҝҗжҠ—дәүвҖҷ пјҢ иҝҳжҳҜжҲ‘дёӘдәәиүәжңҜеүҚйҖ”зҡ„вҖҳе‘ҪиҝҗжҠ—дәүвҖҷпјҹвҖқйӮЈдёҖе№ҙ пјҢ е°ҡй•ҝиҚЈ47еІҒ гҖӮ
гҖҖгҖҖе°ҡй•ҝиҚЈеңЁдёҠжө·ж— дәІж— еҸӢ пјҢ д»–еҚҙи§үеҫ—дёҺиҝҷеә§еҹҺеёӮзјҳеҲҶж·ұеҺҡ гҖӮ 1951е№ҙ пјҢ е°ҡй•ҝиҚЈз¬¬дёҖж¬ЎйҡҸзҲ¶дәІеңЁдёҠжө·зҷ»еҸ° пјҢ и‘—еҗҚзҡ„еӨ©иҹҫиҲһеҸ°еә§ж— иҷҡеёӯ пјҢ е–қеҪ©еЈ°еҰӮеҗҢжғҠйӣ·д№Қиө· пјҢ жҠҠд»–еҗ“дәҶдёҖи·і гҖӮ зӣҙеҲ°д»ҠеӨ© пјҢ жҜҸжҜҸиө°еҲ°зҰҸе·һи·Ҝ пјҢ е°ҡй•ҝиҚЈд»Қдјҡж„ҹж…ЁдёҮеҚғгҖҒй©»и¶іиүҜд№… гҖӮ 1983е№ҙ пјҢ е°ҡй•ҝиҚЈеёҰеӣўжқҘдёҠжө·жј”еҮә пјҢ жңҖзҲҶжЈҡзҡ„дёҚжҳҜз»Ҹе…ёеү§зӣ®гҖҠе°Ҷзӣёе’ҢгҖӢ пјҢ иҖҢжҳҜж–°зј–жҲҸгҖҠе°„иҷҺеҸЈгҖӢ гҖӮ вҖңиҝҷеә§еҹҺеёӮжңҖеҜҢеҲӣж–°гҖҒжұӮж–°д»ҘеҸҠй”җж„ҸжұӮзҙўзҡ„зІҫзҘһ пјҢ иҝҷз§ҚзІҫзҘһжҝҖеҠұзқҖжҲ‘гҖҒеҗёеј•зқҖжҲ‘ гҖӮ вҖқжҲ–и®ёжҳҜдёҺиҝҷеә§еҹҺеёӮзҡ„еҲӣж–°зІҫзҘһдёҚи°ӢиҖҢеҗҲ пјҢ е°ҡй•ҝиҚЈзҡ„вҖңдёҚе®үеҲҶвҖқеӣ еӯҗеңЁдёңжө·д№Ӣж»Ёеҫ—еҲ°дәҶвҖңеӯөеҢ–вҖқ 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еӯҳеӮЁдё–з•Ң@дә‘еҲӣеӨ§ж•°жҚ®еј зңҹи‘ЈдәӢй•ҝиҚЈиҶәеҚ—дә¬вҖң科жҠҖ顶尖专家йӣҶиҒҡи®ЎеҲ’дәәжүҚвҖқ
- гҖҺеӯҳеӮЁдё–з•ҢгҖҸдә‘еҲӣеӨ§ж•°жҚ®еј зңҹи‘ЈдәӢй•ҝиҚЈиҶәеҚ—дә¬вҖң科жҠҖ顶尖专家йӣҶиҒҡи®ЎеҲ’дәәжүҚвҖқ
- [ж–ҮжұҮжҠҘ]зҪ‘еү§йӣҶдҪ“вҖңдёҠж–°вҖқпјҢи°ҒиғҪжҲҗдёәдёӢдёҖдёӘзҲҶж¬ҫ
- гҖҺиҜҒеҲёеёӮеңәзәўе‘ЁеҲҠгҖҸй•ҝиҚЈйӣҶеӣўе…ЁиҮӘеҠЁеҸЈзҪ©з”ҹдә§и®ҫеӨҮиҺ·еҮәеҸЈи®ўеҚ•
- ж–ҮжұҮжҠҘ@зІҫеҪ©й…Қи§’жҲҗе°ұиҚ§еұҸвҖңеҪ“д»ЈжҜҚдәІеӣҫйүҙвҖқ
- гҖҢж–ҮжұҮжҠҘгҖҚжҠ–йҹізҲҶж¬ҫвҖңзҘһеү§вҖқдёәдҪ•жІЎиғҪ笑еҲ°жңҖеҗҺ
- гҖҢж–ҮжұҮжҠҘгҖҚгҖҠдёӯеӣҪеҢ»з”ҹгҖӢиҝҷеҮ йғЁзәӘеҪ•зүҮдёәдҪ•иғҪеҲ·еұҸзҲҶзәўпјҹ
- гҖҢж–ҮжұҮжҠҘгҖҚгҖҠзҷҪеӨңиҝҪеҮ¶гҖӢе§җеҰ№зҜҮгҖҠйҮҚз”ҹгҖӢдёҠзәҝ еј•еҸ‘и§Ӯдј—и®Ёи®ә
- гҖҗж–ҮжұҮжҠҘгҖ‘жө·жҠҘвҖңжҲҳз–«вҖқгҖҖд»Ҙи®ҫи®Ўзҡ„еҠӣйҮҸйј“еҠІеҮқеҝғ
- #ж–ҮжұҮжҠҘ#гҖҠеңЁдёҖиө·гҖӢпјҡдёәжҲҳвҖңз–«вҖқдёӯдј—еҝ—жҲҗеҹҺзҡ„дёӯеӣҪдәәж°‘ж„ҹеҠ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