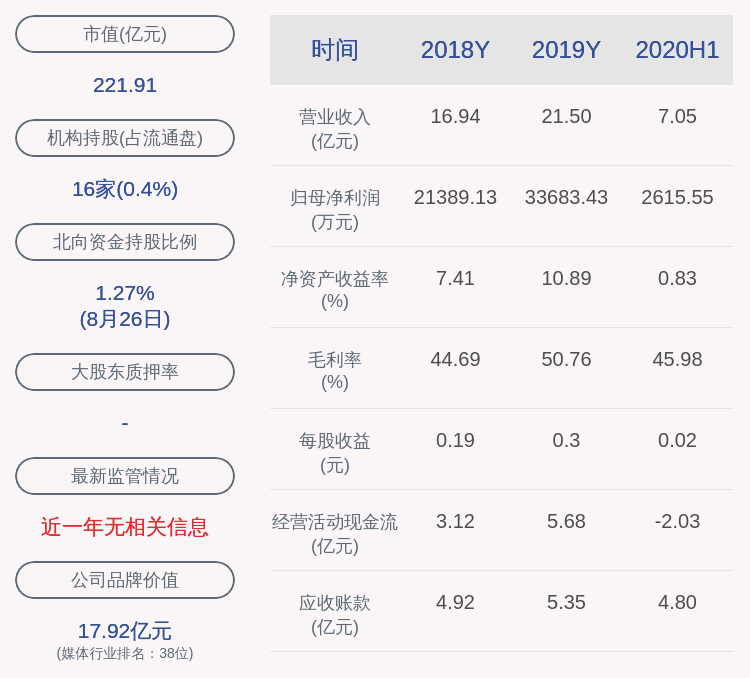дёҠдё–зәӘе…ӯеҚҒе№ҙд»ЈпјҢжҲ‘еңЁеҶңжқ‘зҡ„еІҒжңҲ
дёҠдё–зәӘе…ӯеҚҒе№ҙд»Ј пјҢ жҲ‘еңЁеҶңжқ‘зҡ„еІҒжңҲ жҲ‘еӣ 家еәӯжҳҜеҜҢеҶң пјҢ дёӯеӯҰжҜ•дёҡдёҺеӨ§еӯҰж— зјҳ пјҢ йӮЈжҳҜ1963е№ҙ пјҢ жҲ‘еӣһиҖҒ家иҫҪе®ҒзңҒжң¬жәӘеҺҝеҚ—з”ёе…¬зӨҫе°ҸеіӘеӨ§йҳҹеҠЎеҶң пјҢ ејҖе§ӢдәҶжј«й•ҝзҡ„еҶңжқ‘еІҒжңҲ гҖӮ еҜҢеҶңеңЁжҲ‘еҝғдёӯжҳҜдёҖз§ҚжҒҗжғ§ пјҢ дёҖз§ҚиҖ»иҫұ пјҢ дёҖз§ҚзҪӘиҝҮ гҖӮ иҙ«дёӢдёӯеҶңзҡ„еӯ©еӯҗ пјҢ жңүзҡ„иў«дҝқйҖҒдёҠдәҶеӨ§еӯҰ пјҢ жңүзҡ„иҝӣеҹҺеҪ“дәҶе·Ҙдәә пјҢ жңүзҡ„еҸӮеҶӣеҪ“дәҶе…ө пјҢ з•ҷеңЁжқ‘йҮҢзҡ„жңүеҪ“йҳҹй•ҝдё¶дјҡи®Ўдё¶еҮәзәідё¶и®°е·Ҙе‘ҳзҡ„ пјҢ жңүеҪ“ж°‘еҠһж•ҷеёҲдё¶иөӨи„ҡеҢ»з”ҹзҡ„ пјҢ е°ұжҳҜе№Іжҙ»д№ҹжҳҜзңӢеңәйҷўдё¶зңӢз“ңең°дё¶зңӢиҸңеӣӯдё¶иө¶й©¬иҪҰзӯүиҪ»жҙ» гҖӮ иҖҢжңҖи„ҸжңҖзҙҜжңҖиӢҰжңҖеҚұйҷ©зҡ„жҙ»е„ҝжҳҜеҜҢеҶңе’Ң他们вҖқеҸҜд»Ҙж•ҷиӮІеҘҪвҖқзҡ„еӯҗеҘід»¬ гҖӮ жҜ”еҰӮ пјҢ дҝ®жўҜз”°гҖҒдҝ®ж°ҙеә“гҖҒжҠ¬зҹіеӨҙгҖҒжһ¶жө®жЎҘгҖҒжү“зЁ»еҹӮиҝҷдәӣжҙ»е°ұжҳҜеҜҢеҶңеҲҶеӯҗеҸҠеӯҗеҘід»¬зҡ„дәҶ пјҢ еҲәйӘЁзҡ„жІіж°ҙжіҘж°ҙ пјҢ дҪҝжҲ‘и…ҝдёҠзҲ¬ж»ЎдәҶжӣІжӣІејҜејҜзҡ„йқҷи„үиЎҖз®Ўе„ҝ пјҢ жәғзғӮеҸ‘и„“ гҖӮ 1966е№ҙеҶ¬жңҲ пјҢ з”ҹдә§йҳҹдҝ®е°Ҹж°ҙз”өз«ҷ пјҢ жҢ‘йҖүжҲ‘们еҮ дёӘвҖқеҸҜд»Ҙж•ҷиӮІеҘҪвҖқзҡ„еӯҗеҘіеҲ°еҚҒйҮҢеӨ–зҡ„жІіиҫ№дҝ®з”өз«ҷ гҖӮ зҷҪеӨ©еңЁз»“еҶ°зҡ„жІійҮҢжү“жЎ©жӢҰжІі пјҢ дёҚеҲ°дёҖе°Ҹж—¶е°ұеҶ»еҫ—жө‘иә«еҸ‘жҠ– пјҢ дёҠеІёе–қдёҖеҸЈиҖҒзҷҪе№Ій…’ пјҢ еҶҚи·іиҝӣжІійҮҢ гҖӮ еӨңйҮҢжҢ–жңәеқ‘ пјҢ еңЁж°ҙйҮҢеҜ’йЈҺйҮҢ пјҢ дёҖзӣҙе№ІеҲ°ж·ұеӨң гҖӮ жҳҘиҠӮеҲ°дәҶ пјҢ ж°ҙз”өз«ҷдҝ®еҘҪдәҶ гҖӮ жҲ‘们иҝҷдәӣдәәиҝҳжҳҜдёҺ家еәӯеҲ’дёҚжё…з•Ңйҷҗ пјҢ иҝҳжҳҜең°дё»йҳ¶зә§зҡ„еӯқеӯҗиҙӨеӯҷ гҖӮ дёәдәҶеҲ’жё…з•Ңйҷҗ пјҢ дә”еҸ”家дёүејҹжү№еҲӨиҖҒзҲ¶ пјҢ е…үжү№еҲӨиҝҳдёҚиЎҢ пјҢ дё“ж”ҝеӨ§еҶӣиҝҳи®©д»–жү“иҖҒзҲ¶ пјҢ жүҚиғҪи§ҰеҸҠзҡ®иӮүзҒөйӯӮ гҖӮ дёүејҹеҮ ж¬Ўжү¬иө·жүӢ пјҢ йғҪдёҚеҝҚеҮәжүӢ пјҢ дё“ж”ҝеӨ§еҶӣеӨҙеӨҙиҜҙ пјҢ вҖқдҪ дёҚдјҡжү“ пјҢ жҲ‘ж•ҷдҪ гҖӮ вҖқиҜҙзқҖжңқдә”еҸ”и„ёдёҠжү“еҺ» пјҢ дә”еҸ”и„ёдёҠз«ӢеҚіжҲҗдәҶиЎҖйҰ’еӨҙ гҖӮ е…¶е®һең°еҜҢеӯҗеҘідёҺең°дё»еҜҢеҶңеҲҶеӯҗжІЎжңүд»Җд№ҲеҢәеҲ« пјҢ йғҪжҳҜиҙұж°‘ пјҢ иҖҒдёҖиҫҲжӯ»дәҶ пјҢ жқ‘йҮҢиҝҳеҫ—ж–—дёӢеҺ» пјҢ ж–—зҡ„еҜ№иұЎе°ұжҳҜиҝҷдәӣвҖқеҸҜж•ҷиӮІеҘҪзҡ„еӯҗеҘівҖқдәҶ гҖӮ дёҚиҝҮ пјҢ йӮЈдёӘе№ҙд»Јд№ҹжңүеҝғиӮ еҘҪзҡ„ гҖӮ е°ұиҜҙдәҢзҷһеӯҗеҗ§ гҖӮ дәҢзҷһеӯҗ并дёҚзҷһ гҖӮ еҸӘдёҚиҝҮеӨҙдёҠз”ҹиҝҮзҷһ пјҢ жқ‘йҮҢдәәжүҚиҝҷж ·з§°е‘јд»– гҖӮ еңҹж”№ж—¶еҲҶзҡ„дёүй—ҙең°дё»з©ҶиҖҒеӨ§зҡ„жҲҝеӯҗ пјҢ иҝҷдәӣе№ҙеҝ«еЎҢдәҶ пјҢ иҝҷжүҚд»ҺеҹҺйҮҢдәІжҲҡеҖҹжқҘй’ұйҮҚж–°зҝ»зӣ– гҖӮ е°ұеңЁдәҢзҷһеӯҗжӢҶдёӢиҖҒжҲҝеӨ§жўҒж—¶ пјҢ еҸ‘зҺ°еӨ§жўҒдёҠжңүдёҖеқ—е өжңЁ гҖӮ д»–жҠҠе өжңЁжҢ–ејҖ пјҢ йҮҢйқўжңүдёҖдёӘзүӣзҡ®зәёеҢ… пјҢ жү“ејҖдёҖзңӢ пјҢ жҳҜеқ—йҮ‘е…ғе®қ гҖӮ дәҢзҷһеӯҗжІЎжңүеЈ°еј пјҢ иҝһд»–зҡ„иҖҒе©Ҷд№ҹжІЎжңүе‘ҠиҜү пјҢ жҠҠе°Ҹе…ғе®қжҸЈеңЁжҖҖйҮҢ гҖӮ жҷҡдёҠ пјҢ дәҢзҷһеӯҗеҗғе®ҢйҘӯ пјҢ еҒ·еҒ·жқҘеҲ°з©ҶиҖҒеӨ§е®¶ гҖӮ з©ҶиҖҒеӨ§иҝҷдёӘз—…иҖҒеӨҙжҳҜең°дё»еҲҶеӯҗ пјҢ е·ұеҚ§еәҠеӨҡж—ҘдёҚиө· гҖӮ е…¶е®һз©ҶиҖҒеӨ§иҝҷдёӘең°дё»еңҹж”№еүҚд№ҹе°ұжҳҜ家йҮҢжңүдёүй—ҙиҚүжҲҝ пјҢ дәҢеҚҒеӨҡдә©ең° пјҢ з”ұдәҺ他家没дәәе№Іжҙ» пјҢ е°ұйӣҮдәҶдёҖдёӘй•ҝе·Ҙ пјҢ иҝҷдёӘй•ҝе·Ҙе°ұжҳҜдәҢзҷһеӯҗ гҖӮ дәҢзҷһеӯҗжё…жҘҡең°зҹҘйҒ“ пјҢ з©ҶиҖҒеӨ§иҝҷдёӘең°дё»жҳҜжҖҺж ·зңҒеҗғдҝӯз”ЁзҪ®еҠһ家дёҡзҡ„ пјҢ д»–жӣҙзҹҘйҒ“иҝҷеқ—йҮ‘е…ғе®қжҳҜз©ҶиҖҒеӨ§йӮЈе№ҙд»ҺеұұдёҠжҢ–зҡ„дәәеҸӮжҚўжқҘзҡ„ пјҢ йӮЈеӨ©ж”ҫе·ҘеӣһжқҘ пјҢ д»–зңӢи§Ғз©ҶиҖҒеӨ§е–ңеӯңеӯңд»ҺйӣҶдёҠеӣһжқҘвҖҰвҖҰеҪ“дәҢзҷһеӯҗд»ҺжҖҖйҮҢжҺҸеҮәе…ғе®қж—¶ пјҢ з©ҶиҖҒеӨ§зҡ„зңјжіӘд»Һд»–йҘұз»ҸйЈҺйңңзҡ„и„ёдёҠз°Ңз°ҢиҗҪдёӢжқҘ пјҢ д»–жІЎжңүдјёжүӢеҺ»жӢҝйӮЈе…ғе®қ пјҢ з”ҡиҮіиҝһзңӢд№ҹжІЎзңӢ пјҢ зҙ§зҙ§жҸЎдҪҸдәҢзҷһеӯҗзҡ„жүӢ пјҢ еҳҙи§’йўӨжҠ–зқҖ пјҢ жғіиҜҙд»Җд№ҲеҸҲиҜҙдёҚеҮә пјҢ и„‘иўӢдёҖжӯӘ пјҢ дҫҝж°ёиҝңзҰ»ејҖдәҶдәәдё–вҖҰвҖҰеҗҺжқҘ пјҢ з©ҶиҖҒеӨ§зҡ„еҗҺдәӢеҗ¬иҜҙжҳҜдәҢзҷһеӯҗж“ҚеҠһзҡ„ гҖӮ дәҢзҷһеӯҗдёәиҝҷдәӢиҝҳеҸ—еҲ°жү№еҲӨ гҖӮ 1968е№ҙ пјҢ ж–ҮеҢ–еӨ§йқ©е‘ҪејҖе§Ӣдёүе№ҙдәҶ пјҢ еҶңжқ‘д№ҹж—©еҠЁиө·жқҘдәҶ пјҢ еӨ§еӯ—дёҚиҜҶзҡ„зӨҫе‘ҳеңЁе·ҘдҪңз»„зҡ„йј“еҠЁдёӢ пјҢ д№ҹејҖе§Ӣе”ұиҜӯеҪ•жӯҢгҖҒи·іеҝ еӯ—иҲһгҖҒеҒҡвҖңдёүеҝ дәҺвҖқгҖҒвҖң еӣӣж— йҷҗвҖқгҖҒвҖң дә”йҰ–е…ҲвҖқ гҖӮ жҜҸеӨ©дёҠе·ҘеҲ°з”°еӨҙ,жҖ»иҰҒеҝөдёҠеҮ ж®өжҜӣдё»еёӯиҜӯеҪ•жүҚдёӢең°е№Іжҙ» пјҢ й•ҝжӯӨд»ҘеҫҖ пјҢ дҫҝи§үеҫ—д№Ҹе‘і,дҪҶи°Ғд№ҹдёҚж•ўиҜҙ гҖӮ з”ҹдә§йҳҹй•ҝзҺӢеёҢжҳҺеҝөиҝҮеҮ еӨ©д№Ұ пјҢ дёҖеӨ©еҝғиЎҖжқҘжҪ® пјҢ еҸҳдёӘиҠұж ·,и®©еӨ§е®¶иғҢиҜөжҜӣдё»еёӯиҜ—иҜҚ гҖӮ иҝҷдёҖиҠұж · пјҢ еҫ—еҲ°дәҶзҹҘйқ’们зҡ„е“Қеә” пјҢ д»Җд№ҲвҖңеӣӣжө·зҝ»и…ҫдә‘ж°ҙжҖ’ пјҢ дә”жҙІйңҮиҚЎйЈҺйӣ·жҝҖвҖқ,д»Җд№ҲвҖңйҮ‘зҢҙеҘӢиө·еҚғй’§жЈ’,зҺүе®Үжҫ„жё…дёҮйҮҢеҹғвҖқ пјҢ д»Җд№ҲвҖңиҰҒжү«йҷӨдёҖеҲҮе®ідәәиҷ«,е…Ёж— ж•ҢвҖқ пјҢ дёӘдёӘиғҢиҜөеҰӮжөҒ гҖӮ еҸҜжҳҜиҪ®еҲ°иҖҒиҙ«еҶңеј еұұеӯҗ пјҢ еұұеӯҗдёҚи®Өеӯ—,йӮЈе№ҙвҖңжү«зӣІвҖқж–—еӨ§зҡ„еӯ—жүҚи®ӨиҜҶдёҖзҹі,жҶӢдәҶеҚҠеӨ© пјҢ жұ—йғҪеҶ’еҮәжқҘдәҶ гҖӮ иҝҷж—¶ пјҢ еӨ©иҫ№ж¶ҢжқҘеӨ§зүҮд№Ңдә‘,й”…еә•дјјзҡ„ пјҢ иҝңеӨ„е“ҚзқҖй—·йӣ· пјҢ зңјзңӢйӣ·йҳөйӣЁе°ұжқҘдәҶ гҖӮ еұұеӯҗжҖҘеҫ—еӣўеӣўиҪ¬,д№ҹи®ёж—©дёҠеҗғең°з“ңеӨҡдәҶ,ж¶ҲеҢ–дёҚеҘҪ пјҢ зӘҒ然ж”ҫдәҶдёҖдёӘе“ҚеұҒ,еӨ§е®¶жғіз¬‘еҸҲдёҚ敢笑,еӣ дёәиғҢиҜөжҜӣдё»еёӯиҜӯеҪ•е’ҢиҜ—иҜҚ,жҳҜдёҖ件зҘһеңЈзҡ„дәӢ гҖӮ иҝҷж—¶ пјҢ еұұеӯҗзӘҒ然еҶ’еҮәдёҖеҸҘ:вҖңдёҚйЎ»ж”ҫеұҒ!вҖқдј—дәәеӨ§жғҠ пјҢ жҖҺд№ҲиғҢиҜөжҜӣдё»еёӯжҳҜвҖңж”ҫеұҒвҖқе‘ў!жӯЈиҰҒжү№ж–— пјҢ зҹҘйқ’дёӯжңүдёӘеҸ«жқЁж–Үзҡ„д»ҺжҖҖйҮҢжҺҸеҮәжҜӣдё»еёӯиҜ—иҜҚжң¬ пјҢ жүҫеҮәвҖңдёҚйЎ»ж”ҫеұҒвҖқйӮЈеҸҘ гҖӮ еӨҙйЎ¶дёҖеЈ°зӮёйӣ· пјҢ з“ўжіјеӨ§йӣЁйҷҚдёӢжқҘ пјҢ дәә们д№ҹйЎҫдёҚеҫ—иҝҷдәӣ пјҢ дәүзқҖи·‘еұұж №зҹіжҙһйҮҢйҒҝйӣЁдәҶ гҖӮ ж–ҮеҢ–еӨ§йқ©е‘Ҫдёӯ пјҢ еңЁжҲ‘们з”ҹдә§йҳҹд№ҹй—№еҮәеҫҲеӨҡ笑иҜқ гҖӮ еұұи°·жқ‘зҡ„зҺӢзҖҡж–Ү пјҢ жҳҜдёӘй«ҳдёӯз”ҹ пјҢ еӣ 家еәӯеҮәиә«дёҚеҘҪжүҚжІЎиў«еӨ§еӯҰеҪ•еҸ– гҖӮ иҝҷдёӘе…Ёжқ‘жңҖй«ҳеӯҰеҺҶзҡ„зҺӢзҝ°ж–Ү пјҢ еҸӘеҘҪеңЁе®¶з§Қең° гҖӮ з”ұдәҺд»–жңүж–ҮеҢ– пјҢ жқ‘йҮҢиҰҒеҶҷд»Җд№Ҳ пјҢ жҜ”еҰӮеҶҷжҳҘиҒ”гҖҒдҝЎд»¶гҖҒж–Үд№Ұд»Җд№Ҳзҡ„ пјҢ е°ұеҺ»жүҫд»–еҶҷ пјҢ е№іж—¶жқ‘дәәжӣҙеӨҡзҡ„жҳҜжұӮд»–з»ҷеӯ©еӯҗиө·еҗҚеӯ— гҖӮ д»–д№ҹеҘҪиҜҙиҜқ пјҢ жңүжұӮеҝ…еә” гҖӮ жҲ‘们жқ‘жңүдёӘ姓иүҫзҡ„ пјҢ иҝһз”ҹдәҶдёүдёӘе„ҝеӯҗ пјҢ з”ҹ第дёҖдёӘе„ҝеӯҗж—¶ пјҢ жӯЈеҖјж–°дёӯеӣҪжҲҗз«Ӣ пјҢ дёәиЎЁжӢіжӢізҲұеӣҪд№Ӣеҝғ пјҢ зҺӢзҝ°ж–Үз»ҷд»–иө·еҗҚеҸ«иүҫеӣҪ гҖӮ 第дәҢдёӘе„ҝеӯҗиө·еҗҚеҸ«иүҫж°‘ пјҢ 第дёүдёӘе„ҝеӯҗеҸ«иүҫе…ҡ гҖӮ еҲ°дәҶж–ҮеҢ–еӨ§йқ©е‘Ҫж—¶ пјҢ йҖ еҸҚжҙҫзӘҒ然еҸ‘зҺ°е…¶дёӯзҡ„еҘҘз§ҳ пјҢ жҠҠиҝҷдёүдёӘе„ҝеӯҗзҡ„еҗҚеӯ—иҝһиө·жқҘ пјҢ дёҚе°ұжҳҜвҖңеӣҪж°‘е…ҡвҖқеҗ—пјҹиҝҷдёҚжҳҜеҰ„жғізҝ»еӨ©еӨҚиҫҹгҖҒжҒўеӨҚи’Ӣ家зҺӢжңқз»ҹжІ» пјҢ д»–зҡ„й»‘еҝғиҝҳж·ұж·ұең°зҲұзқҖеӣҪж°‘е…ҡпјҒиҝҷж¬ЎзҺӢзҖҡж–ҮжІЎжңүиәІиҝҮзҒҫйҡҫ пјҢ д»–иў«жҠјеҲ°жү№еҲӨдјҡ пјҢ еҸҜжҖңзҡ„зҺӢзҝ°ж–Үиў«жү“еҫ—зҡ®ејҖиӮүз»Ҫ пјҢ е®ҡдәҶдёӘвҖңеҸҚйқ©е‘ҪвҖқзҪӘеҗҚ пјҢ еҲӨдёүе№ҙеҲ‘ гҖӮ д»ҺжӯӨ пјҢ зҺӢзҝ°ж–ҮеҶҚд№ҹдёҚж•ўдёәжқ‘йҮҢеӯ©еӯҗиө·еҗҚеӯ—дәҶ гҖӮ йӮЈж—¶ пјҢ жқ‘йҮҢйҷӨдәҶејҖжү№еҲӨдјҡе°ұжҳҜеҝҶиӢҰжҖқз”ң гҖӮ еҠізҙҜдёҖеӨ©дәҶ пјҢ жҷҡдёҠйҘӯжқҘдёҚеҸҠеҗғе®Ң пјҢ е°ұиў«еҸ¬йӣҶеңЁз”ҹдә§йҳҹйҳҹйғЁйҮҢ пјҢ з…ӨжІ№зҒҜдёӢ пјҢ е”ұзқҖпјҡвҖңеӨ©дёҠеёғж»Ўжҳҹ пјҢ жңҲзүҷдә®жҷ¶жҷ¶ пјҢ з”ҹдә§йҳҹйҮҢејҖеӨ§дјҡ пјҢ иҜүиӢҰжҠҠеҶӨдјёвҖҰвҖҰвҖқеҝҶиӢҰжҖқз”ңдјҡе°ұејҖе§ӢдәҶ гҖӮ еҝҶиӢҰжҖқз”ңиў«еҪ“дҪңдёҖйЎ№йҮҚиҰҒзҡ„ж”ҝжІ»д»»еҠЎжқҘжҠ“ пјҢ вҖңеҝҶиӢҰжҖқз”ңдјҡвҖқ еёёејҖ пјҢ вҖңеҝҶиӢҰжҖқз”ңеұ•и§ҲвҖқ еёёеҠһ гҖӮ еңЁеҝҶиӢҰдјҡдёҠ пјҢ е°Ҫз®ЎеҝҶиӢҰиҖ…иҜүиҜҙиҮӘ家иӢҰйҡҫеҸІж—¶ пјҢ дёҖи„ёз—ӣиӢҰ пјҢ еЈ°жіӘдҝұдёӢ пјҢ дҪҶеҗ¬иҖ…жҳҜиЎЁжғ…жј з„¶ пјҢ еӣ дёә他们еҗ¬дәҶдёҚдёҠдёҖж¬ЎиҜүиӢҰ пјҢ дҪҶеҶідёҚиғҪйңІеҮәдёҖдёқеҫ®з¬‘ пјҢ еӣ дёәйӮЈеҸҜжҳҜйҳ¶зә§ж„ҹжғ…й—®йўҳ гҖӮ жңүж—¶еӨҙеӨҙ们зҺҜи§Ҷдјҡеңә пјҢ еҗ¬иҖ…иҰҒйҷӘзқҖжөҒжіӘ пјҢ дёҚжөҒжіӘиҖ…е°ұиҰҒиў«жүЈдёҠйҳ¶зә§з«Ӣеңәжңүй—®йўҳзҡ„еёҪеӯҗ гҖӮ еҹҺйҮҢжқҘзҡ„зҹҘйқ’еҗ¬и…»дәҶеҝҶиӢҰ пјҢ дјҡеүҚеҮҶеӨҮеҘҪж№ҝжүӢеё• пјҢ ж·ұжҖ•ж— жіӘеҸҜжөҒ гҖӮ еҝҶиӢҰиҖ…еҝҶиө·иӢҰжқҘж»”ж»”дёҚз»қ пјҢ иғҪиҜҙдёҠдёӨдёүдёӘе°Ҹж—¶ пјҢ дҪҶеҲ°жҖқз”ңж—¶з«ҹдёүиЁҖдёӨиҜӯ пјҢ иҚүиҚү收еңә гҖӮ жңүзҡ„дёәдәҶиҜҙжҳҺзҺ°еңЁз”ҹжҙ»еҚҒеҲҶе№ёзҰҸ пјҢ иҜҙжҜҸйҖўиҝҮе№ҙиҠӮеҸ‘иӮүзҘЁйұјзҘЁ пјҢ иҝҳиғҪеҗғдёҠйұјиӮүпјӣиҝҮеҺ»иә«жҠ«йә»иўӢзүҮ пјҢ зҺ°еңЁеҸ‘еёғзҘЁжЈүиҠұзҘЁ гҖӮ жңүзҡ„еңЁеҝҶиӢҰж—¶з«ҹзҠҜдәҶй”ҷиҜҜ гҖӮ еҚ•еҫ·жё…жҳҜдёӘеӯӨиҖҒеӨҙ пјҢ ж—§зӨҫдјҡз»ҷең°дё»еҪ“й•ҝе·Ҙ пјҢ д»–еңЁеҝҶиӢҰж—¶иҜҙ пјҢ иҝҮеҺ»иӢҰжҳҜиӢҰ пјҢ зҙҜжҳҜзҙҜ пјҢ дҪҶиғҪеҗғйҘұ пјҢ еҶңеҝҷж—¶иҝҳеҗғе№ІйҘӯ гҖӮ дё»жҢҒдәәзңӢд»–иҜҙжјҸдәҶеҳҙ пјҢ еҝҷиҜҙеҲ«иҜүиӢҰдәҶ пјҢ дёӢйқўжү№еҲӨ гҖӮ иҖҒеҚ•еӨҙиҜҙпјҡвҖңдёҚиҜүиӢҰдәҶ пјҢ йӮЈе°ұжү№еҲӨ гҖӮ жҜӣдё»еёӯйўҶе’ұиҙ«дёӢдёӯеҶңжҗһдёүиҮӘдёҖеҢ… пјҢ еӣӣеӨ§иҮӘз”ұ пјҢ дҝәеҲҡеҗғйҘұеҮ еӨ©иӮҡеӯҗ пјҢ еҲҳе°‘еҘҮиҝҷдёӘиө°иө„жҙҫи·іеҮәжқҘеҸҚеҜ№ пјҢ зңҹжҳҜзҪӘиҜҘдёҮжӯ»пјҒвҖқдё»жҢҒдәәзңӢд»–иҜҙеҸҚдәҶ пјҢ ж…ҢеҝҷдёҠеҺ»еҲ¶жӯў пјҢ иҖҒеҚ•еӨҙиҜҙ пјҢ и°ҒдёҚи®©дҝәиҙ«дёӢдёӯеҶңеҗғйҘұиӮҡеӯҗ пјҢ дҝәиҙ«дёӢдёӯеҶңеҶідёҚзӯ”еә”пјҒдё»жҢҒиө¶зҙ§жҚӮдҪҸиҖҒеҚ•еӨҙзҡ„еҳҙ пјҢ иҝһжҺЁеёҰжҗЎжҠҠд»–жһ¶еҮәдјҡеңә гҖӮ еҸӮеҠ еҝҶиӢҰдјҡдёҚйҡҫ пјҢ йҡҫзҡ„жҳҜеҗғеҝҶиӢҰйҘӯ гҖӮ еҗһзі е’ҪиҸң пјҢ еҜ№еҶңж°‘жқҘиҜҙд№ғжҳҜеҜ»еёёдәӢ пјҢ еҜ№дёӢд№ЎзҹҘйқ’жқҘиҜҙ пјҢ еҸҜзңҹйҡҫ гҖӮ еҝғдёӯдҪңе‘• пјҢ дёҚж•ўдёҚеҗғ пјҢ йқўйңІйҡҫиүІ пјҢ еҝҚдёҚдҪҸе‘Ізүҷе’§еҳҙ пјҢ и№ҷйўқжӢ§зңү пјҢ иў«и§ҶдёәжҖқжғіжңүй—®йўҳ гҖӮ жңүдёӘзҹҘйқ’еҸ«й©¬й”җ пјҢ зӢјеҗһиҷҺе’Ҫ пјҢ иў«иҜ„дёәе…Ҳиҝӣ пјҢ дәӢеҗҺжүҚзҹҘйҒ“д»–дәӢе…ҲеңЁзў—йҮҢж”ҫдәҶзі– гҖӮ зҹҘйқ’йЎҫеІ©еҗғдәҶеҝҶиӢҰйҘӯ пјҢ й—№дәҶиӮҡеӯҗ пјҢ еҮ еӨ©жІЎдёҠзҸӯ гҖӮ жҲ‘们жқ‘иҷҪ然жҳҜеұұжқ‘ пјҢ дҪҶе°ҒеұұиӮІжһ— пјҢ зғ§жҹҙеҫҲеӣ°йҡҫ гҖӮ и¶ҒдёӯеҚҲдј‘жҒҜ пјҢ жҲ‘жӢҝиө·жҹҙеҲҖдёҠеұұ гҖӮ иҝңиҝңзңӢдёҠеҺ»жңүдёҖжЈөжһҜж ‘ пјҢ еҸ¶еӯҗж—©е·ІиҗҪе°Ҫ гҖӮ йӮЈж—¶з”ҹдә§йҳҹжңүдёӘ规е®ҡ пјҢ жҜҸеҲҚи§ҒеҲ°жһҜжңЁе·Іжӯ» пјҢ йғҪеҸҜд»Ҙз ҚеҖ’еҪ“жҹҙ гҖӮ жҲ‘иҝҷдёӘдәҢзӯүиҙұж°‘ пјҢ жҖ•жғ№еҮәйә»зғҰ пјҢ жғіз ҚжҺүиҝҷжЈөжһҜж ‘ пјҢ еҝ…йЎ»жүҫдёӘдәәиҜҒжҳҺйӮЈж ‘е·Іжӯ» гҖӮ жӯЈеҘҪзңӢи§Ғж”ҫзүӣзҡ„йӯҸеӨ§еҸ” пјҢ дҫҝй—®йӮЈж ‘жӯ»дәҶжІЎжңү гҖӮ йӯҸеӨ§еҸ”д№ңзңјзңӢдәҶзңӢйӮЈж ‘ пјҢ 笑йҒ“пјҡвҖңйӮЈж ‘еҲ«дәәз Қе°ұжӯ»дәҶ пјҢ дҪ з Қе®ғе°ұжІЎжӯ» гҖӮ вҖқжҲ‘еҸӘжңүиӢҰ笑 пјҢ еҸӘеҘҪеҺ»жҗӮж ‘дёӢзҡ„еҸ¶еӯҗ гҖӮ дёҚдёҖдјҡ пјҢ йӮЈжЈөжһҜж ‘иў«еҲ«дәәз ҚеҺ»дәҶ гҖӮ еӨ•йҳіжёҗиҗҪ пјҢ жқ‘еӯҗйҮҢзҡ„зӮҠзғҹе°ұеҚҮиө·жқҘ пјҢ ж·Ўи“қж·Ўи“қ пјҢ з¬јзҪ©е°Ҹжқ‘жҳҸзәўзҡ„еӨ©з©ә гҖӮ 家йҮҢе·ІжІЎдәҶзұідёӢй”… пјҢ жҲ‘дёӢең°еҪ’жқҘеҰҲеҰҲи®©жҲ‘еҺ»еҗҺжІҹе§җе§җ家еҖҹзұі гҖӮ жҲ‘ж”ҖдёҠеҗҺеұұ пјҢ иҝңиҝңзңӢеҲ°жҲ‘家зҡ„зӮҠзғҹд№ҹиў…иў…еҚҮиө·жқҘ пјҢ жҲ‘зҹҘйҒ“ пјҢ еҰҲеҰҲе·ІжҠҠж°ҙзғ§иҝҮеҮ ж¬ЎдәҶ пјҢ з«ҷеңЁй—ЁеҸЈзӯүжҲ‘еҖҹзұіеҪ’жқҘ гҖӮ йӮЈж—¶еҖҷ пјҢ жҜҸеҲ°еҒҡйҘӯж—¶ пјҢ жқ‘йҮҢ家家жҲ·жҲ·зҡ„зғҹеӣұйғҪеҶ’иө·еӨ§зғҹйӣҫ пјҢ и®©дәәзңӢзқҖж—ҘеӯҗиҝҮеҫ—еҘҪ пјҢ иҰҒжҳҜи°Ғ家зғҹеӣұдёҚеҶ’зғҹ пјҢ иҝҷ家е°ұжҳҜж–ӯзІ®дәҶ гҖӮ е…¶е®һжқ‘йҮҢжІЎжңүеҮ 家жңүзҺ°жҲҗзұідёӢй”…зҡ„ гҖӮ зӯүжҲ‘д»Һе§җе§җ家еҖҹзұіеҪ’жқҘж—¶ пјҢ е·Із»ҸжҳҜеҚҠеӨңдәҶ гҖӮ дёҠеңәеҗҺ пјҢ еңәйҷўйҮҢеҝҷжҙ»иө·жқҘ гҖӮ дёҖеһӣеһӣи°·еӯҗгҖҒиұҶеӯҗгҖҒзЁ»еӯҗеғҸе°Ҹеұұдјјзҡ„ пјҢ й»„жҫ„жҫ„зҡ„зҺүзұіжЈ’е Ҷж»Ўеңәйҷў пјҢ дёҖжҙҫ丰收жҷҜиұЎ гҖӮ иҖҒзүӣжӢүзқҖзҹізЈҷ пјҢ еҗұеҗұе‘Җе‘ҖеҸ«дёӘдёҚеҒң гҖӮ йӮЈжү¬еңәзҡ„жұүеӯҗ пјҢ дёҖй”ЁдёҖй”ЁжҠҠи„«зІ’зҡ„и°·еӯҗжү¬дёҠеӨ©еҺ» пјҢ иҗҪдёӢйҳөйҳөйҮ‘и°·йӣЁ гҖӮ ж»Ўеңәйҷўзӣӣж»ЎдәҶж¬ўд№җ гҖӮ еҝҷдәҶдёүжҳҘе…«еӨҸ пјҢ жҳҜиҜҘдә«еҸ—丰收зҡ„е–ңжӮҰдәҶ гҖӮ еҘҪзІ®дәӨдәҶе…¬ пјҢ дҪҷзІ®еҚ–з»ҷеӣҪ家 пјҢ еү©дёӢзҡ„з•ҷз»ҷеҶңж°‘ гҖӮ дёҖе№ҙеҲ°еӨҙ пјҢ дёҚе°ұзӣјиҝҷзӮ№зІ®йЈҹд№ҲпјҒеҸҜжқ‘йҮҢжҜҸдәәеҸЈзІ®жҳҜж№ҝжјүжјүзҡ„иӢһзұіжЈ’еӯҗ пјҢ е®ҡйҮҸ280ж–Ө пјҢ и„«зІ’еҗҺд№ҹе°ұжҳҜ200жқҘж–Ө гҖӮ дёҖе№ҙ365еӨ© пјҢ дёҖеӨ©иҝҳдёҚеҲ°6дёӨе‘ҖпјҒз”ҹдә§йҳҹй•ҝзңјзқӣж№ҝж¶ҰдәҶ гҖӮ йӮЈж—¶йҷӨдәҶеҸЈзІ®иҝҳеҸҜеҲҶзӮ№иҗҪеңәзҡ„еңҹзІ® пјҢ з®—дҪңйҘІж–ҷзІ® гҖӮ дәәйғҪеҗғдёҚйҘұе“ӘиғҪжҠҠеңҹзІ®е–ӮйёЎйёӯпјҹеҘідәә们用簸箕жү¬еҺ»жІҷеңҹ пјҢ з•ҷдҪңеҸЈзІ® гҖӮ йҳҹй•ҝзӢ дёӢеҝғ пјҢ жҠҠйӮЈе ҶдҪҷзІ®жҗ…жӢҢеҲ°еңҹзІ®йҮҢеҲҶз»ҷд№ЎдәІ гҖӮ йӮЈдёҖе№ҙ пјҢ жқ‘йҮҢдәәжІЎжңүйҘҝиӮҡеӯҗ пјҢ йқ’й»„жҖ»з®—жҺҘдёҠдәҶ гҖӮ йҳҹй•ҝеҚҙеӣ жӯӨж’ёдәҶ пјҢ йҖҒеҲ°е…¬зӨҫвҖңеӯҰд№ вҖқ дәҶдёҖдёӘжңҲ гҖӮ жңҖйҡҫеҝҳ1971е№ҙжҳҘ пјҢ еҰҲеҰҲиҝҗж°”зү№еҲ«еҘҪ гҖӮ з”ҹдә§йҳҹзҢӘеңәжҜҚзҢӘеҸӘдёӢ9еӨҙзҢӘеҙҪ пјҢ з”ЁжҠ“йҳ„зҡ„еҠһжі•еҲҶз»ҷзӨҫе‘ҳ гҖӮ еңЁе…Ёжқ‘30жҲ·дёӯ пјҢ еҰҲеҰҲз«ҹ然жҠ“дёӯдәҶ пјҢ зңӢеҫ—еҮәеҰҲеҰҲеғҸдёӯдәҶеӨ§еҘ–дёҖж ·е…ҙеҘӢ гҖӮ жҲ‘дёҖиҫҲеӯҗд№ҹеҝҳдёҚдәҶеҰҲеҰҲеңЁдјёиҝӣйұјзҜ“жҠ“йҳ„зҡ„жғ…жҷҜпјҡеҘ№и„ёж¶Ёзәў пјҢ еұҸдҪҸе‘јеҗё пјҢ еҸҢжүӢеҚҒеҗҲ пјҢ еҳҙйҮҢеҝөеҸјзқҖд»Җд№Ҳ пјҢ 然еҗҺе°Ҹеҝғзҝјзҝјең°жҠҠжүӢдјёиҝӣзҜ“йҮҢ пјҢ ж‘ёдәҶеҘҪд№… пјҢ зӣҙеҲ°дј—дәәйғҪдёҚиҖҗзғҰеӮ¬дҝғеҘ№ж—¶ пјҢ жүҚжҠҪеҮәжүӢжқҘ пјҢ еұ•ејҖдёҖзңӢ пјҢ жҳҜдёӘеӨҙеҸ·пјҒд»ҺжӯӨеҗҺ пјҢ жҜҸйҖўж”¶е·ҘеҪ’жқҘ пјҢ жҲ‘жҖ»жҳҜеүІдёҖдәӣзҢӘиҚүе–Ӯе…» гҖӮ иҝҮе№ҙж—¶ пјҢ иҝҷзҢӘиҷҪ然еҫҲзҳҰ пјҢ е·Ій•ҝжҲҗ200еӨҡж–Ө гҖӮ еҸҜиҝҷеӨҙзҢӘжҲ‘家没жңүжҚһзқҖеҗғ пјҢ иў«з”ҹдә§йҳҹйҖҒеҺ»иө¶вҖңзӨҫдјҡдё»д№үеӨ§йӣҶвҖқ дәҶ гҖӮ еҰҲеҰҲиҜҙ пјҢ жҜ”йӮЈдәӣжІЎжңүжҠ“зқҖзҢӘзҡ„дәә家 пјҢ зҹҘи¶ідәҶ гҖӮ еҘҪеңЁвҖңеӨ§йӣҶвҖқ иҝҳз»ҷзӮ№иҫӣиӢҰй’ұ пјҢ еҺ»жҺүзҢӘеҙҪй’ұ пјҢ пјҢ иҝҳеү©53е…ғ гҖӮ е№ҙж №дёҖеӨ©еӨ©йҖјиҝ‘ пјҢ жҲ‘дёҠеұұеҺ»еүІеҸ«жқҸжқЎзҡ„жҹҙ пјҢ дёәзҡ„жҳҜеңЁеӨ§е№ҙдёүеҚҒзғ§ж°ҙз…®йҘәеӯҗ гҖӮ иҝҷжҳҜжқ‘йҮҢзҡ„д№ дҝ— пјҢ вҖңжқҸвҖқ дёҺвҖңе№ёвҖқ и°җйҹі пјҢ жңҹжңӣжқҘе№ҙж—Ҙеӯҗе№ёиө·жқҘ гҖӮ еұұеӨ§йӣӘеӨ§ пјҢ жҲ‘еңЁжІЎиҶқж·ұйӣӘдёӯеҜ»жүҫдёҖдёӣдёӣжқҸжқЎ гҖӮ еҝҪ然еңЁиҝңеӨ„дёҖдёӣжқҸжқЎж—Ғ пјҢ жңүдёҖеҸӘйҮҺе…”еңЁи№ҝдёҠи№ҝдёӢжү‘и…ҫ пјҢ и·‘дёҠеҺ»дёҖзңӢ пјҢ дёҖеҸӘйҮҺе…”зҡ„дёҖжқЎи…ҝиў«й“ҒеӨ№еӯҗзүўзүўең°й’ідҪҸ пјҢ йӣӘең°дёҠжё—еҮәдёҖж»ҙж»ҙиЎҖзәў гҖӮ е®ғдјјд№Һиў«еӨ№дҪҸеӨҡж—¶ пјҢ ж— еҠ©зҡ„зңјйҮҢйҖҸеҮәд№һжҖңзҡ„е…ү гҖӮ жҲ‘еҠЁдәҶжҒ»йҡҗд№Ӣеҝғ пјҢ иҝһеҝҷжҺ°ејҖйӮЈеӨ№еӯҗ пјҢ еҸҲж’•дёӢеёғжқЎжҠҠе®ғи…ҝеҢ…жүҺеҘҪ пјҢ ж”ҫеңЁйӣӘең°дёҠ пјҢ е®ғеұ…然没跑 пјҢ еҫ…жҲ‘еүІдёӢж—Ғиҫ№зҡ„жқҸжқЎж—¶ пјҢ жүҚзңӢи§Ғе®ғдёҖжӢҗдёҖзҳёең°и·іеҺ» гҖӮ еӣһеҲ°е®¶жҲ‘еҗ‘еҰҲеҰҲиҜҙдәҶ пјҢ еҰҲеҰҲиҜҙ пјҢ жҲ‘е„ҝеҝғж…Ҳ пјҢ е®ғд№ҹжҳҜдёҖжқЎе‘Ҫе‘ҖпјҒйӮЈе№ҙ пјҢ е°Ҫз®ЎжҲ‘家йҷӨеӨ•еҗғзҡ„йҘәеӯҗйҮҢжІЎжңүиӮү пјҢ д№ҹеҗғеҫ—иӣ®йҰҷ гҖӮ д»ҺеӨ§е№ҙеҲқдёҖе§Ӣ пјҢ жқ‘йҮҢжҖ»иҰҒжүӯдёҠеҮ еӨ©з§§жӯҢ гҖӮ жүӯ秧жӯҢзҡ„家д»Җ пјҢ дё»иҰҒжңүе–ҮеҸӯгҖҒеӨ§йј“гҖҒй“ңй”Ј пјҢ еҗ№е–ҮеҸӯзҡ„дәәжҳҜд»ҺеӨ–жқ‘йӣҮжқҘзҡ„ пјҢ жү“йј“жү“й”ЈеҲҷжҳҜжң¬жқ‘дәә гҖӮ йј“еҫҲеӨ§ пјҢ дёӨдәәжү“ пјҢ еӣӣдёӘдәәжҠ¬ гҖӮ жҠ¬йј“иҝҷдёӘжҙ»еҺҶжқҘйғҪжҳҜеӣӣзұ»еҲҶеӯҗзҡ„ гҖӮ еҗҺжқҘвҖңеӣӣзұ»вҖқ们е№ҙеІҒеӨ§дәҶ пјҢ жҠ¬дёҚеҠЁдәҶ пјҢ е°ұз”ұвҖңеӣӣзұ»вҖқзҡ„вҖңеҸҜж•ҷиӮІеҘҪзҡ„еӯҗеҘівҖқжқҘжҺҘзҸӯ гҖӮ еҮ еҚҒж–Өзҡ„еӨ§йј“ пјҢ з»‘дёҠжңЁжһ¶ пјҢ жүӣеңЁиӮ©дёҠ пјҢ д»ҺиҝҷйҷўжҠ¬еҲ°йӮЈйҷў пјҢ д»ҺиҝҷиЎ—жҠ¬еҲ°йӮЈиЎ— пјҢ д»Һиҝҷжқ‘жҠ¬еҲ°йӮЈжқ‘ пјҢ д»Һж—©дёҠжҠ¬еҲ°жҷҡдёҠ пјҢ д»ҺеҲқдёҖжҠ¬еҲ°еҚҒдә” пјҢ дёҖиҲ¬дәәжҳҜжӢӣжһ¶дёҚдҪҸзҡ„ пјҢ еҶҚеҠ дёҠдёӨдёӘжү“йј“дәәе’ҡе’ҡзҢӣж•І пјҢ йңҮеҫ—иҖіжңөе—Ўе—Ўе“Қ пјҢ дёҖеӨ©дёӢжқҘе°ұзҳ«еңЁзӮ•дёҠдәҶ пјҢ зңҹжҳҜвҖңдәәж°‘еӨ§дј—ејҖеҝғд№Ӣж—Ҙ пјҢ е°ұжҳҜйҳ¶зә§ж•ҢдәәйҡҫеҸ—д№Ӣж—¶вҖқпјҒйӮЈдјҡе„ҝ пјҢ жңүдёӘ笑иҜқ пјҢ дёҖе°ҸдјҷеӯҗеҲ°еӨ–жқ‘зӣёдәІ пјҢ еҘіж–№зҲ№жҳҜдёӘж•ҷеёҲ пјҢ еҒҮиЈ…ж–Ҝж–Ү пјҢ й—®пјҡвҖңе°Ҹдјҷеӯҗ пјҢ еҸ°з”«жҖҺд№Ҳз§°пјҹвҖқе°Ҹдјҷеӯҗзӯ”пјҡвҖңдҝәжҳҜиҙ«дёӢдёӯеҶң пјҢ дёҚжҠ¬йј“ пјҢ ең°дё»еҜҢеҶңжҠ¬йј“ гҖӮ вҖқжҳҘиҠӮеүҚдёҖеӨ© пјҢ жҲ‘е°ұиЈ…з—…иәәеңЁзӮ•дёҠзқЎеӨ§и§ү гҖӮ иҝҮе№ҙиЈ…з—… пјҢ жҷҰж°”пјҒдёәиәІиҝҮжҠ¬йј“д№ӢиӢҰ пјҢ еҖјеҫ—пјҒ жҲ‘дёҚиғҪеҝҳи®°жҲ‘е°ҸеӯҰж—¶зҡ„еҗҢеӯҰеҳҺеӯҗ пјҢ еҳҺеӯҗеҸ«е§ҡзҰҸиҙө пјҢ д»–еӨ©иө„иҒӘж…§ пјҢ еҸЈйҪҝдј¶дҝҗ пјҢ дҪҶжңүдёӘжҜӣз—… пјҢ зҲұжҸҗй—®йўҳ пјҢ жңүж—¶еј„еҫ—иҖҒеёҲеј еҸЈз»“иҲҢ гҖӮ иҜҫжң¬з¬¬дёҖиҜҫжҳҜвҖңжҜӣдё»еёӯдёҮеІҒвҖқ пјҢ иҖҒеёҲеҲҡеңЁй»‘жқҝдёҠеҶҷе®Ң пјҢ еҳҺеӯҗе°ұжҸҗеҮәй—®йўҳпјҡвҖңиҖҒеёҲ пјҢ еҗ¬дәәиҜҙиҝҮеҺ»зҡҮеёқи®©дәәз§°дёҮеІҒ пјҢ жҖҺд№ҲжҜӣдё»еёӯд№ҹз§°дёҮеІҒпјҹвҖқеӯҰеҲ°гҖҠеҚҠеӨңйёЎеҸ«гҖӢйӮЈиҜҫ пјҢ еҶҷең°дё»е‘Ёжү’зҡ®еҚҠеӨңиө·жқҘеӯҰйёЎеҸ«и®©й•ҝе·Ҙ们еҚҠеӨңиө·жқҘеҲ°з”°йҮҢе№Іжҙ» гҖӮ еҳҺеӯҗеҸҲжҸҗеҮәй—®йўҳпјҡвҖңиҖҒеёҲ пјҢ еҚҠеӨңйҮҢй»‘еҸӨйҡҶеҶ¬ пјҢ дјёжүӢдёҚи§Ғдә”жҢҮ пјҢ е‘Ёжү’зҡ®и®©й•ҝе·ҘеҲ°ең°йҮҢе№Іжҙ» пјҢ йӮЈдёҚжҠҠз”°йҮҢзҡ„秧иӢ—йғҪй“ІжҺүдәҶеҗ—пјҹвҖқиҖҒеёҲиҜҙ пјҢ иҝҷе°Ҹеӯҗе°ҶжқҘиӮҜе®ҡжғ№дәӢз”ҹйқһ гҖӮ жһң然 пјҢ еңЁ1971е№ҙжҳҘиҠӮ пјҢ еҳҺеӯҗеңЁд»–家жҲҝй—ЁдёҠеҶҷеүҜеҜ№иҒ” пјҢ дёҠиҒ”жҳҜвҖңдәҢеӣӣе…ӯе…«вҖқ пјҢ дёӢиҒ”жҳҜвҖңдёүдә”дёғд№қвҖқжЁӘжү№жҳҜвҖңеҚ—еҢ—вҖқ гҖӮ иҝҷеүҜеҜ№иҒ”пјҲе…¶е®һжҳҜд»–дёҚзҹҘд»Һе“ӘйҮҢжҠ„жқҘзҡ„пјү пјҢ жқ‘йҮҢдәәеҖ’зңӢдёҚеҮәд»Җд№Ҳ пјҢ дёҖж—Ҙ пјҢ еҺҝйҮҢе·ҘдҪңйҳҹи·ҜиҝҮ他家и§ҒиҝҷеүҜеҸӨжҖӘзҡ„еҜ№иҒ” пјҢ еҸҚеӨҚзҗўзЈЁе…¶ж„Ҹ пјҢ зҗўзЈЁжқҘзҗўзЈЁеҺ» пјҢ з»ҲдәҺзҗўзЈЁеҮәе…¶дёӯзҡ„еҘҘз§ҳ пјҢ еҺҹжқҘжҳҜпјҡзјәиЎЈе°‘йЈҹ пјҢ жІЎжңүдёңиҘҝе‘ҖпјҒиҝҷжҳҜжұЎи”‘еӨ§еҘҪеҪўеҠҝ пјҢ дәҺжҳҜеҳҺеӯҗиў«жү“жҲҗеқҸеҲҶеӯҗ гҖӮ еӨҡе№ҙд»ҘеҗҺ пјҢ жҲ‘и§ҒеҲ°еҳҺеӯҗе·ұжІЎжңүе…ҲеүҚзҡ„иҒӘж…§дј¶дҝҗдәҶ пјҢ еӨҙеҸ‘иҠұзҷҪ пјҢ зәөжЁӘзҡ„и„ёдёҠеҲ»зқҖиӢҰйҡҫ гҖӮ дёҙеҲ«д»–йҖҒжҲ‘дёҖеүҜеҜ№иҒ”пјҡвҖңжғ№зҘёзҡҶеӣ дёӨзүҮе”Ү пјҢ д»ҺжӯӨй—ӯеҸЈпјӣзҪ№йҡҫеҸӘжҖЁдёҖж”Ҝ笔 пјҢ иҖҢд»ҠзҪўжүӢ гҖӮ вҖқжҲ‘жөҒжіӘдәҶ пјҢ иҝҷе°ұжҳҜжҖқжғіж”№йҖ зҡ„еҠӣйҮҸпјҒ еҘҪеңЁдёҖеҲҮйғҪиҝҮеҺ»дәҶ гҖӮ жҲ‘еңЁ1976е№ҙи°ғеҫҖй•ҮдёӯеӯҰж•ҷд№Ұ пјҢ 1981е№ҙи°ғе…ҘеҺҝжңәе…іе·ҘдҪң пјҢ д»ҺжӯӨејҖе§ӢдәҶж–°зҡ„з”ҹжҙ» 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зүӣжіү#зүӣжіүй•ҮжҢҒз»ӯејҖеұ•ж®ӢеһЈж–ӯеЈҒж•ҙжІ» ж”№е–„еҶңжқ‘дәәеұ…зҺҜеўғ
- [жҲҸдёӯдәәи‘өиҠұе®қе…ё]вҖңж–°еһӢдј й”ҖвҖқе·ІжӮ„然иҝӣе…ҘеҶңжқ‘пјҢж”№еҗҚжҚўж–°жӢӣпјҢеҶңж°‘жңӢеҸӢеҸҜеҲ«дёҠеҪ“
- гҖҗеҶңдёҡеҶңжқ‘йғЁгҖ‘еҶңдёҡеҶңжқ‘йғЁпјҡжұҹиӢҸзңҒжІӯйҳіеҺҝеңЁжҹҘиҺ·зҡ„еӨ–зңҒиҝқ规и°ғе…Ҙз”ҹзҢӘдёӯжҺ’жҹҘеҮәйқһжҙІзҢӘзҳҹз–«жғ…
- [жңЁйҮҢеҺҝ]жңЁйҮҢз”ҹжҖҒзҺҜеўғеұҖз»„з»ҮеҶңжқ‘зҺҜеўғз»јеҗҲж•ҙжІ»иЎҢж”ҝжқ‘д»»еҠЎеҜ№жҺҘе·ҘдҪң
- [еҶңдёҡеҶңжқ‘]еј•еҜјзӨҫдјҡиө„жң¬жңүеәҸжҠ•е…ҘеҶңдёҡеҶңжқ‘
- гҖҺеӣӣе·қеҶңжқ‘ж—ҘжҠҘгҖҸжҸҗеүҚйғЁзҪІеҒҡеҘҪеәҰжұӣеҮҶеӨҮ
- гҖҢеҶңдёҡеҶңжқ‘йғЁгҖҚеҶңдёҡеҶңжқ‘йғЁжҙҫеҮәзқЈеҜјз»„ж·ұе…ҘйҮҚзӮ№зңҒд»ҪзқЈдҝғйқһжҙІзҢӘзҳҹйҳІжҺ§
- гҖҺиүҜеҘҪж°ӣеӣҙгҖҸгҖҗеҶңжқ‘дәәеұ…зҺҜеўғж•ҙжІ»гҖ‘иҒҡз„Ұдәәеұ…зҺҜеўғж•ҙжІ»пјҢжҸҗеҚҮе…«йҮҢд№Ўжқ‘вҖңйўңеҖјвҖқ
- гҖҢдҝЎжҒҜе…¬ејҖиЎЁгҖҚеҝ«зңӢ | ж·ұеңіеҶңжқ‘е•Ҷдёҡ银иЎҢеӨҡйЎ№иҝқ规пјҢ银дҝқзӣ‘дјҡејҖеҮә260дёҮе…ғзҪҡеҚ•
- гҖҺеҶңжқ‘з”өзҪ‘гҖҸж–°з–Ҷд»Ҡе№ҙе®үжҺ’йҖҫ75дәҝе…ғеҜ№еҶңжқ‘з”өзҪ‘еҚҮзә§ж”№й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