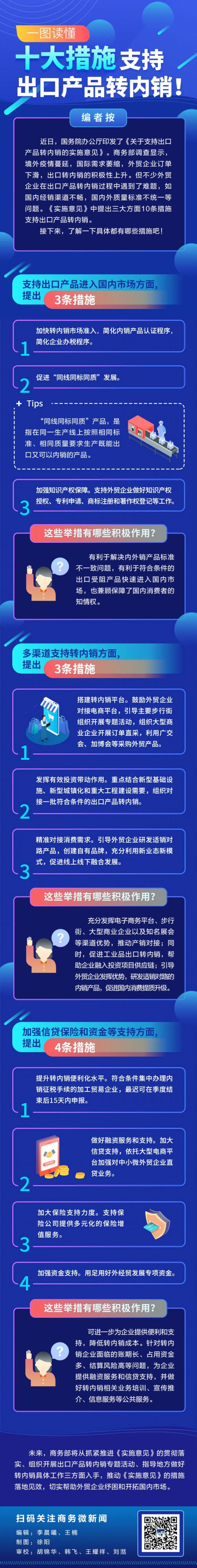为什么疫情期间很多情侣会分手 ?
因为你发现了即使他很闲也不会来找你聊天。
■来自的网友回复
原答已删
祝所有情侣永远甜甜蜜蜜,这种狗粮我还挺爱吃。
别人:

我:

■来自的网友回复
说一个当年「非典」我采访过的真实故事吧。失去一段感情肯定会难过,但这或许正是成长的契机。
「非典」时期的爱情
这个标题乍一看,好像有点矫情,如今任何故事如果不跟爱情沾点边,好像就不是故事。因此,写「非典」的故事也要硬扯上一点关于爱情的故事。
可是,你再往深处想一想,「非典」感染的是人,而人是一个有感情的动物,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就造了一男一女,而且这一男一女总想跑到一起去,男人和女人都会感染「非典」,而救治「非典」病人的医护人员也是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因此他(她)们当中不会有爱情问题?这样一想,就不会觉得矫情了。
说的这个爱情故事,还完全是一个柏拉图式的爱情,可是正是这种爱情最感人。
当时,被挑选进入市一医院临时病区的有一个小护士。真的是个小护士,一个年纪很轻,个子也不高,还戴着无边眼镜的「小」护士。也许是她太「小」,以致不能引人注意,我在张积慧那本记述市一医院「非典」隔离病区的《护士长日记》中,没有见到她的名字。但是,小人物的故事更真实,小人物的故事也感人。这个小护士叫小春。
小春是个清秀的湖北荆州姑娘,个性内秀,情感细腻。当时她在市一医院神经外科 ICU 室当护士,第一批进临时病区的 12 名护士中就有她。那天,神经外科的护士长通知她说:「小春,护理部通知抽调你到新组建的临时病区去。」当时,小春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因为「非典」属于呼吸内科疾病,从专科上与神经外科没有什么联系,她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抽她到临时病区,因此,当时第一反应只说了一个字:「啊?」护士长就解释说:「因为你是『ICU』护士。」意思是「ICU」是重症监护室,临时病区最需要的就是重症监护室的工作人员。小春似乎明白了,表达的方法仍然是一个字:「哦。」再也没说什么,一个人悄悄地走了。
当天小春变得格外的沉默,只是机械地干活,很少说话。晚上下班回到宿舍,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干什么都心不在焉,满屋子转,却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最后索性什么也不干了,把灯关了,开着电视,可眼睛盯着电视画面,心里却不知道在演什么内容,充满脑海的只是:害怕,莫名的害怕。
当小春含着眼泪跟我谈到这些时,我想像得出那种画面,我体会得到那种感觉,因为这是一种真实的叙述,感人的真实。那么多的医护人员进入了「非典」一线,这时,都已经知道这种传染病的凶险,不害怕的人,确实有。而且小春还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她有一个女同事,也叫晓春,只是拂晓的晓,是个重症监护室的医生,虽然是个女同志,但她在得知自己被抽调到临时病区后,回到科里一点也没有表现出害怕,而是有一种勇士即将要上战场的兴奋。后来在临时病区的日日夜夜里,在所有参加临时病区工作的医护人员中,始终表现出色,让小春敬佩不已。
但绝大部分人心里还是害怕的。天天听到的都是「非典」的凶险,中山二院、中山三院遭受「非典」重创,那么多的医务人员被「非典」感染倒下,特别是本院护士梁健,平时在医院里活蹦乱跳的一个人,说倒就倒了,而且此时已有医务人员死亡,这不仅仅是耳濡目染的危险,而是一种近在身边实实在在的危险。这种明明白白的害怕,更煎熬人。
那天晚上,小春想着,想着,一种无助的眼泪就下来了。因为她是一个外地人,只身一人在广州,不像本地的同事还可以回家,得到身边亲人的安慰和鼓励,她只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个人把一切都承担下来。因此,感到格外的孤独。
她后来对我说,从心里并不想去,但她明白不去是不行的。在当前抗击「非典」已经变成压倒一切的大形势下,自己作为一个医护人员,如果不去,就是临阵脱逃?临阵脱逃,一辈子都会抬不起头来。现在只有一条路,去。
想着,想着,一种无助,一种没有任何亲人可以倾诉的孤单,使小春泪水禁不住地往下流。小春生自己的气,为什么这种无奈的泪水就总也流不完呢?
小春自小生长在农村,父亲在她 14 岁的时候,跟母亲离婚了,然后在离家不远的一个村子里,跟另一位女人结了婚。那时在农村离婚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家里的孩子也抬不起头来,而 14 岁的少女也是最敏感的时候,那种遭人背后指点的耻辱深深地烙在她的心里,她的敏感和细腻,也是在那时,在逆境中逐渐养成的。今天她已经长大成人,仍然不能原谅自己的父亲,尽管她知道自己最需要的就是父爱。
那时在小春的心里只有一个愿望,好好学习,考上大学,离开让自己总不能顺畅呼吸的老家。后来,她考上了湖北职工医学院,再后来以优秀的成绩被选派到广州实习,又被市一医院留下,先后在好几个科室做过护士。
在这间小小的单身宿舍里,在只有电视光亮的背景下,只有小春一个孤身弱影,此时的她最迫切的愿望就是找一个最亲的人,叙说心中的孤单。最亲的人首先是自己的母亲,她目前也在广东打工,可是小春知道不能跟母亲说,因为这只会增加了一分担心,现在全中国有几个人不知道「非典」的危险,让更不明白的母亲知道自己的女儿进了临时病区,那母亲的担心反而变成了自己的负担。不能说,绝对不能跟母亲说。
除了母亲,最亲的人就是他了。虽然他们还没有把一切都说得那么透彻,目前所处的关系也不是十分的明确,但,在小春的心目中,最亲的人就是他。
这个人是小春初恋的情人,也是她一直在深爱着的人。他在北京,一位在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
性格内向,但情感丰富的小春,没想到爱情来得是那样的让她措手不及。
2000 年 5 月,当时小春大学二年级,由于成绩好,学校要送她到广州去实习,她利用「五一」假期回家探望母亲。那天,她乘中巴回家。一上车,就看见一个戴着眼镜很文静的青年坐在车上,他那与众不同的文雅气质一下就把她吸引了,好像整个车上只有他一个人似的。当时,小春感到有一股强大的引力,吸引着她想坐到他身边去,而他坐的位子旁边正好没有人坐。当小春朝他走来,他立即站了起来,很有礼貌地将自己靠车窗的座位让给了小春。这让小春更感动,因为小春晕车,一般坐车都尽量找有车窗的位子坐。这样两人就坐在了一起。当车子开动的时候,小春感到两个人都产生了强烈的想交谈的欲望。小春首先想猜他的身份,她认为他一定是个大学生,就试探着问:「你是大几的?」(大学几年级)小伙说:「你猜。」小春说:「大不了大四。」(大学四年级)小伙笑着说:「我已经读完硕士研究生,马上就要交论文了。」「啊?!」一种崇敬之情油然而起。于是,两个人的话题就谈不完了,以至于车到家门口了,小春还不觉得,今天车怎么开得这么快?
分手的时候,两人都相互留了电话。
「五一」节结束回到学校,小春给他打电话,小伙立即邀请她去他的学校玩。小春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才到小伙的学校。小伙已经在学校门口等她。于是,两人就在学校操场边散步边交谈。
至今,小春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已近黄昏,两人在操场上遇到一个同学,这位同学向小伙打听考研究生的事,小伙耐心地向他介绍,一点一滴讲得特别仔细。小春侧脸望着他,这时,夕阳西下,阳光照在小伙的脸上,使从未恋爱过的小春心弦怦然拨动。小春突然产生一种强烈地想了解小伙内心世界的愿望。后来,小春跟我谈到这一段时,她坦白地说:「我被他深深地吸引了。」
没过几天,两人相约再次会面,到小春学校附近的一所公园见面。这一次是小伙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
那天,约好下午 3 点见面。小春早早地来到公园,她不愿意迟到,当然也希望小伙也别迟到。特别,对于一个敏感的又是第一次恋爱的姑娘,是非常在意约会迟到的事的。
可是,小春坐在公园里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小伙的身影,当时,公园旁边就是有一座大厦,楼顶上有一个大钟,小春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个大钟,数着钟上的时间。5 分钟,10 分钟,15 分钟过去了,就是不见小伙的影子。可是,此时的小春心里却是出奇地宁静,她甚至都不焦急。后来她告诉我说:「当时公园里没有一丝风,我坐在湖边的一个小亭子里,湖水平静得像一面镜子,我的心也像湖水一样的平静,因为我确信他一定会来。」
20 分钟过去了,果然小伙一头大汗地跑来了。他一脸歉意地说:「我迟到了,宁愿受罚。」说着伸出自己的手:「随便你打多少下都行。」
小春握住了他的手,一脸庄重地说:「我不打你,我相信你一定会来。」
那天从下午 3 点多,两人在公园里一直呆到晚上 9 点,中间没有吃东西,却一点也不觉得饿。天色暗下来的时候,小伙轻轻地将小春揽进怀中,小春就静静地躺在小伙的怀里,一句话也没有了,一切尽在不言中,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一直坐到那讨厌的大钟敲了九下,小春知道时间太晚了,再晚,小伙就没有交通车回去了。
后来小伙是这样表达自己的感觉的,他对小春说:「我从见到你的那一刻起,就觉得我们认识很久了。」
2000 年 7 月,小春到广州实习,接着,小伙也考取了北京的博士研究生。于是,两人天各一方,全靠鸿雁传书了。再后来,小春有了手机,「鸿雁」不需要了,手机传书,发短信息,既经济也快捷。
这是小春的初恋,对于小伙来说,是不是初恋,小春没有说,但这种纯朴的爱情,生活中好像已经久违了。如果,不是小春娓娓道来,在生活中我们恐怕很少再听到这种爱情故事了。
不用我说,在无助的害怕之中流着眼泪的小春,此时,最想通话的是谁了。
在采访中,小春告诉我:「当时哪怕得到他一句话的鼓励,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力量。」
这时,已经是凌晨 2 点了,小春知道现在他肯定睡了,不能再打电话去打扰他了,于是,就给他发了一个短信:我要去非典病区了,我心里很害怕,我坚信一定能挺过去。请你为我祝福,给我力量。
发完短信,小春想,明天就要去临时病区了,我一定要睡着,不能第一天就无精打采的。小春强迫自己睡下了。
第二天就去参加会议,正在这时,小伙回了一个短信,真的很短,只有一句话:保护好自己。很平实。两个原因,小伙本身就是一个平实的人,还有就是当时北京「非典」疫情还没有起来,小伙对「非典」的认识还处于模糊之中,恐怕根本没有想到,小春所面临的危险。
就这样一句话,小春就感到满足了。她当时就回了一个短信:正在开会,好像要上战场一样。」
2 月 17 日上午,第一批「非典」病人送到了,八个人都是护士。她们神情憔悴,面色苍白,情绪低落,下救护车的时候,有的是用担架抬着,有的在别人的搀扶下坚持自己走,有的还插着氧气管。前来接收她们的市一医院临时病区的医护人员,除了个别曾到广州八院支援过的医生,其他都是第一次接触真正的「非典」病人,那种气氛既紧张又凝重。一切都顾不上了,小春和大家一道,赶紧上前把自己的姐妹们搀扶进病房。
安顿好她们以后,病房里的气氛特别的沉闷,来的病人心情都不好,有的很消沉,有的甚至有些绝望,一个个都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不说话,病房里掉一根针的声音都能听见,空气也仿佛凝固了。
隔离病区的医护人员,特别是那些护士,看着这些原本是自己的同行,心情非常的复杂。她们都是因为救治别人而倒下的。同时,几乎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这样一个担心:明天躺在这儿的会不会是我呢?
小春当然也一样。
一连几天,都在收治「非典」病人,都是自己的同行,护士比医生多。病人的那种无望,那种痛苦,甚至产生绝望的情绪,深深地影响着临时病区里的医护人员,当然也严重地影响着小春的心情。
那天晚上下班回到医院宿舍,小春累得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当时只有一个想法,赶快睡下。除了工作的繁重,还有院领导、科室领导都一再强调,所有临时病区的医护人员,都必须保证充分的休息,保持较好的体质,是最好防御「非典」的保证。所以,一下班回到宿舍,小春倒下就睡。不但睡下,还要盖好被子,担心着凉。
南国的广州,2 月下旬的气温已经是 20 多度了。
睡着以后的小春突然醒了,醒来后发现自己一身汗,吓得立即跳了起来,不禁脱口而出:「不好,我中招了。」赶紧满屋里找体温表,平时就放在眼前的体温表,这时就是找不着,越是找不着,心里越是发急,越是发急,就更感到心里发烧。终于找到体温表,一量体温:36.9 度。不对,小春再量,还是 36.9。小春仍然不相信,她想,是不是刚才自己找体温表时,身上凉了。钻到被子里捂一会儿,再量,还是 36.9。这才知道,自己是被子捂出汗来的,虚惊了一场。小春对我说,当时躺在床就像中了六合彩一样,自言自语地说:「我太高兴了,我没有中招啊!」
推荐阅读
- 「环球健身中心」每天坚持练两小时,孕后没有小肚子,何雯娜怀孕期间仍不忘瑜伽
- 面包蛋糕@为什么同样的面粉,在中国是包子馒头,在西方人却是面包蛋糕?
- 南方孩子的北方妈妈:越能培养出自理能力强的孩子,为什么越“懒”的妈妈
- 『果果妈咪谈育儿』看完你就懂了,为什么护士要报新生儿的“体重”?这2个作用
- 『疫情』疫情下的至暗欧美,老人清除计划正在进行
- 健身减脂期间,早餐喝啥酸奶较好
- 健康零距离▲为什么?,发现癌症就是晚期
- 「传染病」张文宏:疫情期间如果发烧了,有两件事情特别重要
- 许栗木变美记@不要再想歪了,超模走秀为什么不穿“内衣”?原因其实是这4点
- [贵阳正畸医生周新莹]五点原因让你明白牙齿为什么变黄,牙齿不白都是这些“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