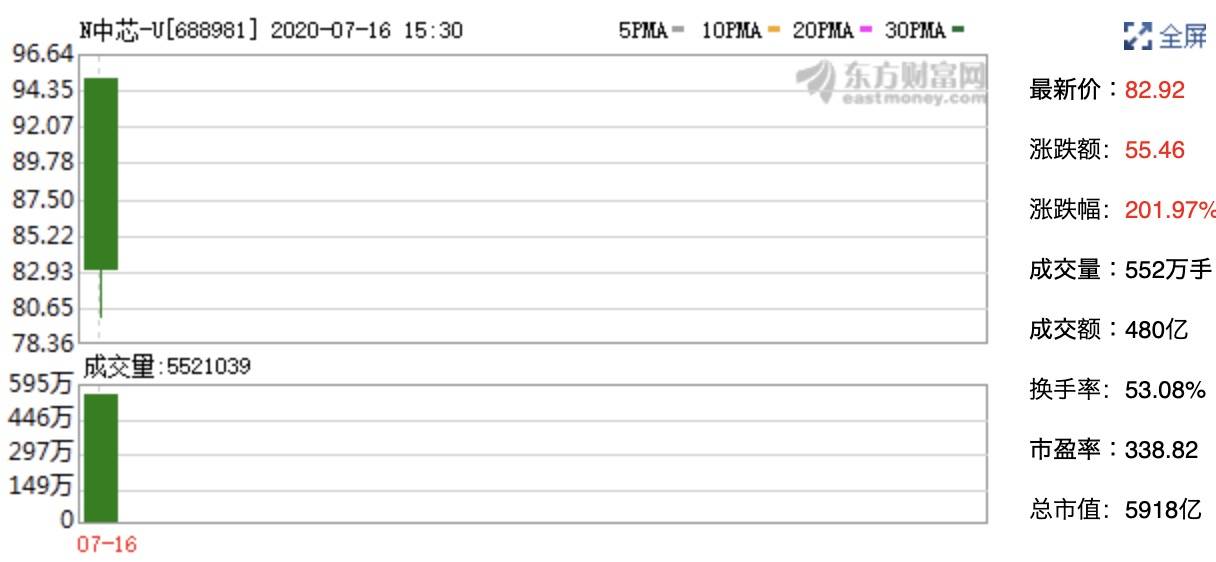жІ»еҫ—еҘҪз—…жІ»дёҚдәҶеҝғпјҡеҗҺз–«жғ…ж—¶д»ЈжҖҺд№ҲиЎҘж•‘еҚғз–®зҷҫеӯ”зҡ„еҝғ( дәҢ )
3жңҲ31ж—Ҙ пјҢ жқҺе»әеӣҪ14еӨ©йҡ”зҰ»жңҹж»Ў пјҢ ж¬Ўж—Ҙе°ұиҰҒеӣһеҲ°е®¶йҮҢ гҖӮ еҝғзҗҶе’ЁиҜўеёҲжқңжҙәеҗӣеҲ°еә·еӨҚй©ҝз«ҷжүҖеңЁзҡ„е…¬еҜ“еҜ№д»–иҝӣиЎҢеҝғзҗҶз–ҸеҜј гҖӮ иҝҷжҳҜжқңжҙәеҗӣеӣўйҳҹдёәжқҺе»әеӣҪжүҖеҒҡзҡ„第дәҢж¬ЎеҝғзҗҶеҚұжңәе№Ійў„ пјҢ 他们иҒҠдәҶдёҖдёӘе°Ҹж—¶ гҖӮ жқҺе»әеӣҪеҗҗйңІиҮӘе·ұзҡ„жӢ…еҝ§ пјҢ дёҚзҹҘйҒ“иҮӘе·ұеӣһ家зңӢеҲ°е„ҝеӯҗз”ҹеүҚзҡ„дёңиҘҝ пјҢ иғҪдёҚиғҪжүӣеҫ—дҪҸ гҖӮ
еңЁжқңжҙәеҗӣе’ҢеӣўйҳҹжҲҗе‘ҳиҝӣиЎҢеҝғзҗҶжҸҙеҠ©зҡ„иҝҮзЁӢдёӯ пјҢ ж–°еҶ йҖқиҖ…зҡ„家еұһиў«з§°дҪңеӨұдәІиҖ… пјҢ иҖҢжӣҙзү№ж®Ҡзҡ„жҳҜжқҺе»әеӣҪиҝҷж · пјҢ дәІеұһд№Ӣй—ҙзӣёдә’ж„ҹжҹ“ пјҢ дёҖж–№еҺ»дё– пјҢ еҸҰдёҖж–№жҙ»дәҶдёӢжқҘ гҖӮ вҖңе№ёеӯҳиҖ…еҝғйҮҢдјҡжңү愧з–ҡе’ҢиҮӘиҙЈ пјҢ и§үеҫ—жІЎжңүз…§йЎҫеҘҪеҜ№ж–№ гҖӮ зү№еҲ«жҳҜиҖҒе№ҙдәә пјҢ жҒЁдёҚеҫ—иҜҙиҜҘжӯ»зҡ„жҳҜжҲ‘ пјҢ дёҚжҳҜдҪ гҖӮ вҖқжқңжҙәеҗӣеҜ№гҖҠдёӯеӣҪж–°й—»е‘ЁеҲҠгҖӢиҜҙ гҖӮ
жқҺе»әеӣҪд»Ҡе№ҙдёғеҚҒеІҒ пјҢ е„ҝеӯҗеҲҡеҲҡеӣӣеҚҒеІҒ пјҢ еӯҷеҘідёҚеҲ°еҚҒеІҒ гҖӮ зҷҪеҸ‘дәәйҖҒй»‘еҸ‘дәә пјҢ иҝҷи®©д»–ж„ҹеҲ°з—ӣиӢҰ гҖӮ жӯ»дәЎзӘҒ然被жҺЁеҲ°дәә们зҡ„йқўеүҚ пјҢ жқңжҙәеҗӣиҜҙзқҖ пјҢ еҒҡеҮәеҗ‘еүҚзҡ„жүӢеҠҝ гҖӮ еҜ№дәҺеҫҲеӨҡйҖқиҖ…家еұһжқҘиҜҙ пјҢ и„‘жө·дёӯзҡ„жңҖеҗҺеҚ°иұЎдёҚжҳҜдёҙз»Ҳзҡ„жӯЈејҸе‘ҠеҲ« пјҢ иҖҢжҳҜжңҖеҗҺдёҖйҖҡжқҘиҮӘйҮҚз—Үз—…жҲҝзҡ„з”өиҜқ пјҢ жҲ–иҖ…жҳҜ120иҪ¬иҝҗеҲ°еҢ»йҷўзҡ„йӮЈдёҖж¬ЎжҢҘжүӢ гҖӮ
жӯ»дәЎеҸҳжҲҗдәҶдёҖеҲҷзӘҒз„¶дј жқҘзҡ„ж¶ҲжҒҜ гҖӮ еҫҲеӨҡ家еұһеӣ жӯӨдёҖејҖе§ӢжӢ’з»қжүҝи®ӨдәІдәәйҖқеҺ»зҡ„дәӢе®һ пјҢ жҲ–иҖ…并дёҚиЎЁйңІиҮӘе·ұзҡ„жӮІдјӨ гҖӮ жқңжҙәеҗӣд»Ӣз»ҚиҜҙ пјҢ еҝғзҗҶе№Ійў„зҡ„第дёҖжӯҘжҳҜеј•еҜјеӨұдәІиҖ…жҺҘеҸ—дәӢе®һ пјҢ е®Јжі„жғ…з»Ә пјҢ е…¶ж¬ЎжҳҜеҺҳжё…иҙЈд»» пјҢ жҫ„жё…йӮЈдәӣ愧з–ҡ гҖӮ
10%зҡ„еҢ»жҠӨдәәе‘ҳдјҡз•ҷдёӢеҝғзҗҶеҲӣдјӨ
жңҖиҝ‘ пјҢ з»Ҹеёёжңүи®ӨиҜҶзҡ„еҢ»з”ҹжңӢеҸӢжқҘжүҫеҲҳеҝ зәҜ пјҢ е’ЁиҜўеҝғзҗҶй—®йўҳ пјҢ иҝҷеҮ еӨ©е°ұжңүеҘҪеҮ иө· гҖӮ йҡҸзқҖжӯҰжұүз–«жғ…еҮ иҝ‘收е°ҫ пјҢ еҫҲеӨҡеҢ»жҠӨдәәе‘ҳжңүдәҶдј‘ж•ҙзҡ„жңәдјҡ пјҢ йҮҚжӢ…дёҖдёӢеӯҗжҢӘиө° пјҢ з§Қз§ҚеҝғзҗҶй—®йўҳеҚҙйҡҸд№ӢиҖҢжқҘ пјҢ еҚідҪҝдј‘жҒҜд№ҹж— жі•зј“и§Ј гҖӮ
й•ҝжңҹзҡ„й«ҳејәеәҰе·ҘдҪңи®©дёҖйғЁеҲҶдәәеҮәзҺ°дәҶPTSDзҡ„еҗҺз»ӯз—ҮзҠ¶ гҖӮ 他们з»ҸеҺҶдәҶеҶ…еҝғзҡ„жҢҜиҚЎ пјҢ еңЁж—¶й—ҙиҝҮеҺ»еҫҲд№…д№ӢеҗҺд»Қ然дјҡзӘҒ然жғҠйҶ’ гҖӮ вҖңжҲ‘们иә«дҪ“йҮҢжңүеҺ»з”ІиӮҫдёҠи…әзҙ пјҢ еңЁз–«жғ…й«ҳеі°ж—¶дә§з”ҹдәҶдёҖз§ҚдәўеҘӢж„ҹ пјҢ и·ҹжү“дәҶйёЎиЎҖдёҖж · пјҢ еҢ»жҠӨзҫӨдҪ“жІЎжңүйҖҖи·Ҝ пјҢ еҸӘиғҪйЎ¶дёҠеҺ» пјҢ дҪҶжҳҜиҝҷз§ҚдәўеҘӢзҡ„зҠ¶жҖҒжҳҜдёҚеҸҜжҢҒд№…зҡ„ пјҢ з»ҸиҝҮдәҶдёҖдёӘжңҲ пјҢ з”ҡиҮіжҳҜдёӨдёӘжңҲ пјҢ йңҖиҰҒеҸҠж—¶дј‘ж•ҙ пјҢ еҗҰеҲҷе°ұи·ҹеј№з°§дёҖж · пјҢ еӨұеҺ»дәҶеј№жҖ§йҷҗеәҰ пјҢ е°ұжҒўеӨҚдёҚдәҶдәҶ пјҢ е°ұз®—дј‘жҒҜ пјҢ д№ҹиҝҳжҳҜи§үеҫ—зҙҜ гҖӮ д»ҺеҝғзҗҶзҡ„и§’еәҰжқҘиҜҙ пјҢ иҝҷжҳҜдёҖз§ҚиҒҢдёҡиҖ—з«ӯ(burnout) гҖӮ вҖқеҲҳеҝ зәҜеҜ№гҖҠдёӯеӣҪж–°й—»е‘ЁеҲҠгҖӢиҜҙ гҖӮ
з–«жғ…жҡҙеҸ‘д»ҘжқҘ пјҢ еҲҳеҝ зәҜи·ҹе…ЁеӣҪеҗ„ең°зҡ„еӯҰжңҜеҗҢиЎҢдҝқжҢҒзқҖзҙ§еҜҶзҡ„иҒ”зі» пјҢ е·Із»ҸеҗҲдҪңдәҶеӨҡзҜҮж–Үз« пјҢ еҸ‘иЎЁеңЁеӣҪеӨ–зҡ„дё“дёҡжңҹеҲҠдёҠ пјҢ е°Ҷе·Іжңүзҡ„жӯҰжұүз»ҸйӘҢеҲҶдә«з»ҷеӣҪеҶ…еӨ–зҡ„еҢ»еӯҰеҗҢиЎҢ гҖӮ
他们еҸ‘иЎЁдәҺгҖҠзҫҺеӣҪеҢ»еӯҰдјҡжқӮеҝ—гҖӢдёҠзҡ„дёҖзҜҮж–Үз« еҜ№1257еҗҚжқҘиҮӘж№–еҢ—жң¬ең°е’ҢеӨ–зңҒзҡ„еҢ»жҠӨдәәе‘ҳиҝӣиЎҢдәҶи°ғжҹҘз»ҹи®Ў пјҢ жҖ»з»“дәҶеёёи§Ғзҡ„еҝғзҗҶз—ҮзҠ¶ пјҢ еҢ…жӢ¬еҺӢеҠӣиҝҮеӨ§(50.4%)гҖҒз„Ұиҷ‘(44.6%)гҖҒеӨұзң (34.0%)е’ҢеҝғзҗҶеӣ°жү°(71.0%)зӯүзӯү гҖӮ е…¶дёӯ пјҢ жӯҰжұүжң¬ең°еҢ»жҠӨдәәе‘ҳзӣёеҜ№жӣҙе®№жҳ“еҮәзҺ°еҝғзҗҶеҺӢеҠӣ пјҢ иҖҢеҘіжҖ§е’Ңдёӯзә§иҒҢз§°зҡ„еҢ»жҠӨзҫӨдҪ“йқўдёҙзҡ„еҺӢеҠӣжӣҙеӨ§ гҖӮ
еҺӢеҠӣзҡ„жқҘжәҗжҳҜеӨҡйҮҚзҡ„ гҖӮ жҜҸеӨ©зңӢеҲ°еӨ§йҮҸзҡ„жӯ»дәЎз—…дҫӢ пјҢ еҫҲе®№жҳ“йҖ жҲҗдёҖз§ҚеӨұжҺ§ж„ҹ гҖӮ дёҚж–ӯжү©ж•Јзҡ„з—…жҜ’延伸еҲ°дәҶеҜ№иҮӘиә«зҡ„жӢ…еҝ§ пјҢ д»ҘеҸҠ家дәәзҡ„е®үеҚұ гҖӮ еҶҚеҠ дёҠе·ҘдҪңзҺҜеўғе’ҢеҶ…е®№зҡ„дёҙж—¶жҖ§еҸҳеҢ– пјҢ д»ҘеҸҠйҡ”зҰ»зҡ„зҠ¶жҖҒ пјҢ иҝҷдәӣйғҪжҲҗдёәдәҶеҝғзҗҶй—®йўҳзҡ„жәҗеӨҙ пјҢ йңҖиҰҒиҝӣиЎҢеҸҠж—¶зҡ„еҚұжңәе№Ійў„ пјҢ еҗҰеҲҷеҸҜиғҪеҸҳжҲҗйҒ—з•ҷй—®йўҳ пјҢ еңЁз–«жғ…з»“жқҹд№ӢеҗҺеҸҚеӨҚеҮәзҺ° гҖӮ
жқҺеҘҮе…үжқҘиҮӘйҷ•иҘҝзңҒзІҫзҘһеҚ«з”ҹдёӯеҝғеҝғиә«еҢ»еӯҰ科 пјҢ жҳҜйҷ•иҘҝйҰ–жү№еҝғзҗҶжҸҙеҠ©еҢ»з–—йҳҹжҲҗе‘ҳ гҖӮ 2жңҲ24ж—Ҙ пјҢ д»–йҡҸйҳҹжқҘеҲ°жӯҰжұү пјҢ иў«еҲҶй…ҚеҲ°жӯҰжҳҢеҢ»йҷў гҖӮ
дёҖиҲ¬зҡ„еҢ»з–—йҳҹй’ҲеҜ№зҡ„дё»иҰҒиҝҳжҳҜз—…дәәзҫӨдҪ“зҡ„еҝғзҗҶйңҖжұӮ пјҢ дҪҶжқҺеҘҮе…үе’Ңд»–зҡ„еӣўйҳҹе°Ҷ2/3зҡ„зІҫеҠӣйғҪжҠ•е…ҘеҲ°дәҶжӯҰжҳҢеҢ»йҷўзҡ„еҢ»з”ҹе’ҢжҠӨеЈ«иә«дёҠ гҖӮ д»–д»Қ然记еҫ— пјҢ еҪ“ж—¶жӯҰжҳҢеҢ»йҷўжүҖжңүзҡ„еҢ»жҠӨдәәе‘ҳеҺӢеҠӣйқһеёёеӨ§ пјҢ жғ…з»Әд№ҹйғҪеҫҲдёҚеҘҪ гҖӮ
жҜҸеӨ©дёӢеҚҲе’ҢжҷҡдёҠ пјҢ жқҺеҘҮе…үе’ҢеҗҢдәӢ们еңЁжӯҰжҳҢеҢ»йҷўзҡ„е®ҡзӮ№й…’еә—жҺҘеҫ…е·Із»ҸдёӢзҸӯзҡ„еҢ»з”ҹе’ҢжҠӨеЈ« пјҢ йӮЈж—¶еҖҷдәәеӨҡдёҖдәӣ гҖӮ 5дәәзҡ„еҝғзҗҶжҸҙеҠ©еӣўйҳҹй…ҚеӨҮдәҶзІҫзҘһ科еҢ»з”ҹе’ҢеҝғзҗҶжІ»з–—еёҲ пјҢ дёҖиө·иҝӣиЎҢеҢ»жҠӨзҫӨдҪ“зҡ„еҝғзҗҶеҚұжңәе№Ійў„ гҖӮ йҰ–е…ҲжҳҜзІҫзҘһ科еҢ»з”ҹжҺҘиҜҠ пјҢ еҜ№дёҘйҮҚзЁӢеәҰиҝӣиЎҢеҲқжӯҘзҡ„еҲӨж–ӯ пјҢ 然еҗҺиҪ¬з»ҷеҝғзҗҶжІ»з–—еёҲ пјҢ и®Ёи®әе…·дҪ“зҡ„жІ»з–—ж–№ејҸ 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ж¶үеҚҺи°ҺиЁҖжҲ–и®ёиғҪжҢҪз•ҷйҖүзҘЁпјҢдҪҶжҢҪж•‘дёҚдәҶз”ҹе‘Ҫж¶үеҚҺи°ҺиЁҖжҲ–и®ёиғҪжҢҪз•ҷйҖүзҘЁпјҢдҪҶжҢҪж•‘дёҚдәҶз”ҹе‘Ҫ
- зҒ«й”…з”·еӯҗеҗғзҒ«й”…жҚһеҮәиӢҚиқҮиҰҒжұӮ10еҖҚиө”еҒҝпјҢеә—й•ҝпјҡз–«жғ…жңҹ收е…ҘдҪҺпјҢиө”дёҚдәҶ
- 2020зңӢзңӢе“ӘдәӣйЎ№зӣ®еҚ–еҫ—еҘҪпјҒ2020е№ҙ1~5жңҲйқ’еІӣйЎ№зӣ®й”Җе”®жҰңеҮәзӮү
- еӣҪеҠЎйҷўеӣҪеҠЎйҷўжёҜжҫіеҠһеҸ‘иЁҖдәәпјҡи°ҺиЁҖе’ҢжҒ«еҗ“дёқжҜ«еҠЁж‘ҮдёҚдәҶдёӯеӣҪдәәж°‘з»ҙжҠӨеӣҪ家е®үе…Ёзҡ„еҶіеҝғе’Ңж„Ҹеҝ—
- йҰҷжёҜеӣҪеҠЎйҷўжёҜжҫіеҠһеҸ‘иЁҖдәәпјҡи°ҺиЁҖе’ҢжҒ«еҗ“дёқжҜ«еҠЁж‘ҮдёҚдәҶдёӯеӣҪдәәж°‘з»ҙжҠӨеӣҪ家е®үе…Ёзҡ„еҶіеҝғе’Ңж„Ҹеҝ—
- еӣҪеҠЎйҷўжёҜжҫіеҠһеҸ‘иЁҖдәәпјҡи°ҺиЁҖе’ҢжҒ«еҗ“дёқжҜ«еҠЁж‘ҮдёҚдәҶдёӯеӣҪдәәж°‘з»ҙжҠӨеӣҪ家е®үе…Ёзҡ„еҶіеҝғе’Ңж„Ҹеҝ—
- еӣҪеҠЎйҷўжёҜжҫіеҠһпјҡи°ҺиЁҖе’ҢжҒ«еҗ“дёқжҜ«еҠЁж‘ҮдёҚдәҶдёӯеӣҪдәәж°‘з»ҙжҠӨеӣҪ家е®үе…Ёзҡ„еҶіеҝғе’Ңж„Ҹеҝ—
- жҺЁиҚҗеҚҺжҳҘиҺ№иҜ„и®әдёҖеҸҘиҜқе°ұеҸ—дёҚдәҶдәҶпјҹзҫҺеӘ’пјҡдёӯеӣҪе’ҢдјҠжң—еңЁеҳІз¬‘зҫҺеӣҪ
- еҢ—зҫҺи§ӮеҜҹдёЁе°‘ж•°ж—ҸиЈ”зҡ„дјӨз—ӣдҪ•ж—¶жүҚиғҪж¶ҲеӨұ
- ж°ҙиӯҰдҪ дёҚдәҶи§Јзҡ„ж°ҙиӯҰпјҒеҮҢжҷЁдёүзӮ№жҺҘеҲ°е‘Ҫд»Өпјҡжү“жҚһе°ёд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