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庭院
居住在钢筋、水泥的小城里几十年 , 更想念儿时的庭院 , 那时的庭院里 , 一年四季景色迷人、瓜果飘香、蝶飞蜂鸣 , 灵动自然 , 就像一个美丽的小花园 , 也是我儿时的乐园 , 载满了我童年的欢乐 , 装满了我少年的烂漫 , 庭院里的一枝一叶总关情 , 那是我与庭院的感情;一景一物都系心 , 那是我对庭院的神往 。 那里 , 留下了我重重叠叠的脚印 , 留下了我五彩斑斓的梦想 , 儿时的庭院成了我心中永恒的记忆 。庭院的右侧是一个偏于一隅的厢屋 , 底座是用石头垒的 , 墙体是用土墼垒的 , 屋顶是尖的 , 厢屋门留在屋山上 , 这样 , 进出方便 。 乡村百姓居家过日子 , 有了这么个厢屋 , 就觉得便利多了 , 也就平添了我现时的记忆 。 我的思维在细嚼慢想:噢 , 想起了厢屋里的摆设 , 正中间安置着一盘石磨 , 石磨的上方吊挂着生活用的麦秸草之类的 , 南面养着一头用来拉磨的毛驴 , 其余的墙旮旯放着锨鐝锄 , 墙缝里挂满了柴镰、草镰 , 这才叫充实的农家生活 。 就说这盘磨吧 , 那是我舅老爷(也就是我父亲的舅)用凿子精心凿出来的 , 用过它的人都说很好用 , 不好用的磨用起来可就麻烦了 , 不是磨的粮食不均匀 , 就是堵磨眼 。 那时 , 虽说村子里有磨坊 , 但有些粮食不能磨 , 再说了 , 磨坊离家一里多 , 来回倒腾两次 , 到了那里还要排号 , 不知哪天才能磨完 , 空里还要一趟趟地跑 , 有时还真不如用自家的石磨磨起来方便 , 想什么时候磨都很随心 , 自己磨出来的粮食还好吃 , 特别香甜 。 现在 , 有些会享受的人 , 宁肯多花钱 , 也打听着买用石磨磨出来的小麦、小米、玉米面等 , 就是这个道理 , 如此看来 , 石磨的影响还是深远的 。家里的石磨一般都是女主人打理的 , 母亲有时间就招呼着推磨 , 母亲在村里忙的时候 , 祖母就招呼着推磨 , 祖母可是居家过日子的一把好手 , 样样都会 。 别看她裹着脚 , 干起活来却很利索 。 儿时看到祖母推磨的场景偶尔还在眼前晃动 , 祖母把粮食放到磨盘上 , 就给毛驴子蒙上眼睛 , 拴到磨棍上 , 蒙上眼的毛驴子就很听话似的 , 专心地、不紧不慢地拉着磨 , 祖母就跟在毛驴子后面 , 一边吆喝着毛驴 , 一边迈着“三寸金莲” , 间或用笤帚往里扫着蹦远的碎米 , 节奏很和谐 , 就这样一圈一圈地推磨 , 不知走过了多少岁月 , 这一圈一圈也不知在我脑海里转了多少遍 。 现在想来 , 有了石磨 , 更再现了那时乡村百姓的真实生活 , 街坊邻里有端着笸箩来碾玉米面吃的 , 有提着袋子来碾地瓜干喂猪的 , 笸箩、筛子什么的就摆满了庭院 , 热闹起来 , 欢声笑语也笑遍了庭院 , 整个庭院都随之灵动起来 。我家那不大不小的庭院里 , 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果树 , 庭院的左侧 , 有一棵老葡萄树 , 这是新中国刚成立时就栽下的 , 树苗也很有意义 , 1983年《人民日报》刊登过我老家乔家村一棵120年树龄的葡萄树 , 我家的这棵龙眼葡萄树苗 , 就是从这棵百年葡萄树上培育的 , 至今也有65个年头了 , 伴随着共和国成长 , 富有时代的纪念意义 。 这棵葡萄树一直横着疯长 , 占据着大半个庭院 。 儿时 , 看着葡萄树的生长 , 熟知它的成长过程 , 从葡萄树的滴水、生芽、长须、结粒到果实累累 , 觉得很有意思 , 到了每年的八、九月份 , 就更有情趣了 , 全家大人孩子围坐在葡萄架下 , 乘凉、喝茶、赏月 , 看着月光斜照下约明约暗的熟透了的葡萄 , 一嘟噜一嘟噜 , 像珍珠 , 似红玛瑙 , 特别招人喜欢 , 细心的父亲端详着剪下一嘟噜既大又整齐的葡萄 , 慢慢品尝 , 酸甜可口 , 沁人心脾 , 感觉味道好极了 , 心情自然好极了 , 油然萌生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 这棵老葡萄树曾给我的童年、少年带来几多欢乐、几多收获 , 现在想来 , 虽离家多年了 , 还总有那么一点让人回味无穷的感觉 , 那棵葡萄树让我产生美好的回忆 , 给我带来一种精神享受 。我家在葡萄架下打了一眼旱井 , 很浅 , 用来储存萝卜、芹菜、葱之类的 , 用起来很方便 。 这口浅井冬暖夏凉 , 感觉很舒适 , 儿时到了夏天的时候 , 就愿意和一两个小伙伴到浅井里乘凉、看看闲书、玩玩牌 , 感觉特别有意趣 。在庭院的东墙跟下并排栽着两棵石榴树 , 在儿时的印象中 , 石榴树上开的一朵朵小红花特别鲜艳 , 鲜艳的花朵散发出浓浓的芳香 , 小小的蜜蜂闻着芳香“嗡嗡”地叫着来了 , 美丽的蝴蝶看着鲜艳的花朵翩翩飞来了 , 就连那黑色的大蜂子也飞来了 , 围绕着石榴花转来转去 , 耳听蜂鸣 , 眼观蝶飞 , 特有情趣 , 到了八、九月份 , 石榴熟了 , 张开了鲜红的笑脸 , 儿时真感到垂涎欲滴 , 祖母见我对石榴注目的样子 , 就顺手揪下那个“喜笑颜开”的石榴 , 用手掰下几粒品尝了一下 , 就递给了我 , 我就和兄弟、姊妹们分着吃了 , 那种甜甜的、酸酸的味道一直留在我的心里 。在厢屋的前面 , 挺拔着一棵苹果树 , 名叫花皮苹果 , 枝繁叶茂 , 果实累累 , 虽说跟现今的红富士苹果苹果比起来不算好吃 , 还有点皮硬 , 但在那时 , 却成了那时解馋的重要果实 。 到了收获苹果的时候 , 我常常爬到苹果树上 , 踏着四周的侧枝 , 摘着一个个鲜艳的苹果 , 家中收获了苹果 , 我也收获了感受 ,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紧挨着粗壮的苹果树的是一棵高大的梨树 , 祖母说这棵梨树叫车头梨 , 我却吃起来像“谢花甜”梨 , 因它谢了花 , 结了果实不长时间就好吃 , 因之 , 我一直把它当成谢花甜梨 。 也因为它在庭院里的果实中熟的最早 , 也就“先入为主”占据在我心中 , 这棵梨吃起来很甜 , 不过 , 我有个习惯 , 即使果实熟了的时候 , 我也一般不动手去摘 。 我只是捡着被风雨摔打下来的 , 用水冲洗干净 , 往往这种果实都是快熟了的 , 吃起来更好吃 。 每次来了暴风雨 , 我都把木棱子小窗帘卷起来 , 盯望着被狂风暴雨摔打的梨树 , 因梨树最不抗摔打 , 看着那左摇右摆的梨树 , 听着梨“啪、啪”落地的响声 , 跑到庭院 , 弯腰捡拾着一个个摔打的皮开肉绽的梨 , 真觉心痛 , 这是我那时不希望看到的 , 这种感受已深
推荐阅读
- 70后80后“童年动画片”收藏!满满的儿时回忆
- 影院要开门了,《唐人街探案 3》们为何不上映
- 物业管理费|住在铜陵嘉华国际的问题
- 保险|一个都不能少!10多分钟走20米,岳阳消防摸黑“喊”出住在积水最深处的五保户
- 加装|住在一层!却带头签字加装电梯,是因为…
- 舞琉喵喵|你居住在“美好生活城市”吗?
- 蚩尤大帝
- 蚩尤,华夏第一人
- 枣庄女性|滕州市召开“美丽庭院”现场观摩暨巩固提升会议
- 染疫男发文说后悔参加烤肉派对 隔日不治身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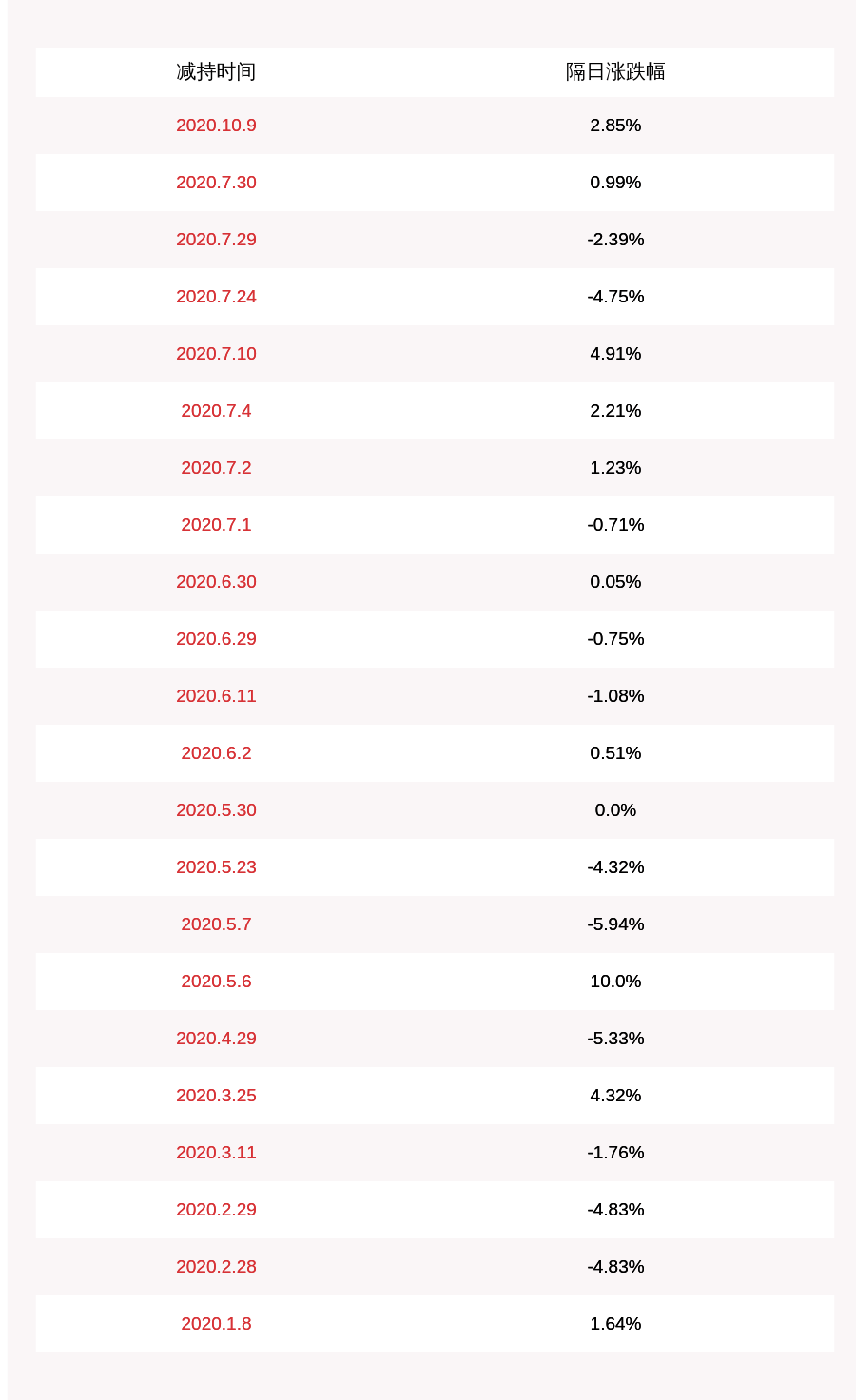









![[河北]我国“退步”最快的省份:用了15年时间,人均GDP从11跌到26](http://img88.010lm.com/img.php?https://image.uc.cn/s/wemedia/s/2020/fbe0e0d48ea3828657c15b92de135824.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