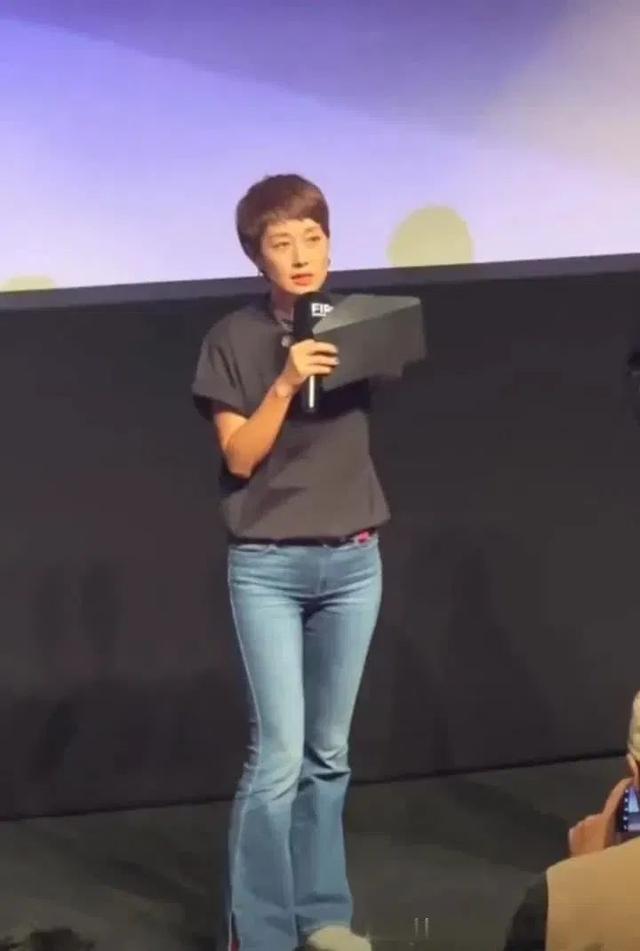医院|9.1,只有一个国家敢拍这真人真事( 二 )

文章图片
那,丈夫真的是优秀的那个,妻子真的是劣质的那个吗?剧情从另一个角度给出答案。丈夫在做医生的同时,还在偏远医院做着儿童学研究。表面看,是预防儿童疾病的伟大研究。实际。这些儿童,都是弃儿,甚至是患有疾病的儿童。讽刺的是,他们名为“国家的弃儿”。
文章图片
意思是:在以国为家的时代,当国家以集体的名义将你抛弃,你就是个弃儿,哪怕父母双全都还是孤儿。瓦德豪森医生再三确认患儿的身份,只说了两个字:很好
文章图片
毫无负罪感。基因优生学原理,也是他提出来的。决定一个人的基因价值是种族不是长相或健康状况
文章图片
造化弄人,他自己的女儿也成为了病儿。经过了多次治疗失败,他决定,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弃儿医院。
文章图片
为了自己能够顺利继承儿童医院院长的职位。优秀吗?在丈夫身上,我们能看到纳粹的第二层特征:抛弃爱与家庭的观念束缚,抛弃个人自主自由的追求。一切以集体利益至上。把人贬低为物,可用则用,不可用则弃。另一边,安妮似乎也不是个好女人。再想想她面对弟弟的那个犹豫眼神。她不坏。只是,被疯狂的统一思想裹夹的人,压根没有能力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她从不曾用自己的理性思考过问题。直到问题出现在她自己身边。自己(即将)被划到异端,女儿被送走,生死不明。为了让孩子免遭苦痛,她尤其绝望。趁孩子睡去,用一只手企图令孩子窒息。镜头定格在她的脸上。
文章图片
无声无息。这个画面让Sir脊背拔凉——妈妈的脸,魔鬼的脸,是同一张脸。人性,还有多少可以被拯救的余地。镜头一转,孩子安然无恙。
文章图片
她以为妈妈在和她玩,兴奋地抓住那双温暖的手。人性之光,又在恻隐中撕开了一道裂缝。杀子怜子,天堂地狱,只一念之间。一边是基因优秀的“优等人”,却优秀得,只有基因足为人道。一边是基因恶劣的“劣等人”。却屡屡一点点凿开冰山,冲破沉闷的社会空气。处处彰显人的尊严。
文章图片
要真正凿开纳粹,除了需要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军的努力,还需要第三台手术。一台德国人自己动的“手术”。手术主刀,是所有夏利特的德国人。他们中,有厌战而逃避上战场的,如安妮的弟弟欧图。
文章图片
有已经投诚给同盟军做间谍的,如绍尔布鲁医生的助手。
文章图片
更多的人,是像绍尔布鲁医生一样。他们崇拜希特勒,为希特勒宣誓效忠。批准在“死刑犯”身上试行实验的计划中,他并没有提出反对;甚至很多新计划送到他的桌上要他签处,也会出于盲目随便签名。理由是,不能限制科学自由。
文章图片
绍尔布鲁是罪大恶极的纳粹帮凶吗?不要轻易扣帽子。这就是《战火中的夏利特》的最后一场手术——它不仅剖开德国人沾上污名的表皮。更露出它们有呼吸感的肌理,深入骨髓的情感。他们并没有罪大恶极,一意孤行干坏事。只是一个个相信自己国家元首的人。对,重点是“人”。Sir想起一本书,概括二战时期德国人的心理非常精准,米尔顿·迈耶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作者访问过纳粹时期十个不同职业的德国人,得出了这样的描述:他们被统治着,他们的选择都是被动的,或者根据自己的利益相关。他们选择当初加入纳粹党,很大程度上,入党能让他们有一份工作。战后回顾过去,仍然认为纳粹时期是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期,他们有生活,有工作,有保障。纳粹战败也并不能让他们感到罪责,他们以为他们的罪已经通过战争来偿还,他们在战败中经历的苦难就是赎罪和补偿。《战火中的夏利特》为什么特别,正因为它近乎注脚般的,解释了一种独特视觉:德国人并不认为自己不正常,也不认为自己在从事一项多么伟大的工作。他们只是普通人,身处战争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剧集没有激烈的战斗,甚至没有强烈的正邪人性冲突,没有我们自以为是的人性黑暗的批判。有的只是对德国人日常生活态度的呈现。反思,如地下缓缓溪流。埋藏在医院的日常生活中,隐藏在每一个复杂的人的举手投足,最终造成人们对“纳粹”的颠覆。剧中有一场戏Sir印象深刻。来自法国(已被德国攻陷)的荣格医生,被邀请到绍尔布鲁医生家做客。荣格医生质疑绍尔布鲁,在对国家元首的誓言(奉旨杀人),和当初对医学的誓言(致力救人)中。哪一种才是他心中主要的价值?
推荐阅读
- 海报视频|仍在救援!山西临汾一饭店坍塌|海报视频|仍在救援!山西临汾一饭店坍塌 已致5人遇难 医院目击者:救护车就没停过
- 常视界|17岁小伙被拘看守所死亡,身上多处伤痕,在医院时禁止家人探望!
- 市属医院|北京市属医院“十四五”如何规划?请您提意见
- 隆福医院|北京市隆福医院挂牌成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临床实验室
- |诸城华元医院重要公告:所有新住院患者及陪护人员须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 医疗|5G智慧医疗快速融合 业内认为未来医院或可轻资产运营
- the|美国科技股市值达9.1万亿美元 首次超过整个欧洲股市市值
- "原"健康杭州|官宣!杭州市第九人民医院今天正式揭牌
- 李沧区|市内三区首家社区医院在李沧区永清路揭牌启用创新构建紧密型医联体
- 国际社会|吉尔吉斯斯坦新冠肺炎疫情缓和 部分医院已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