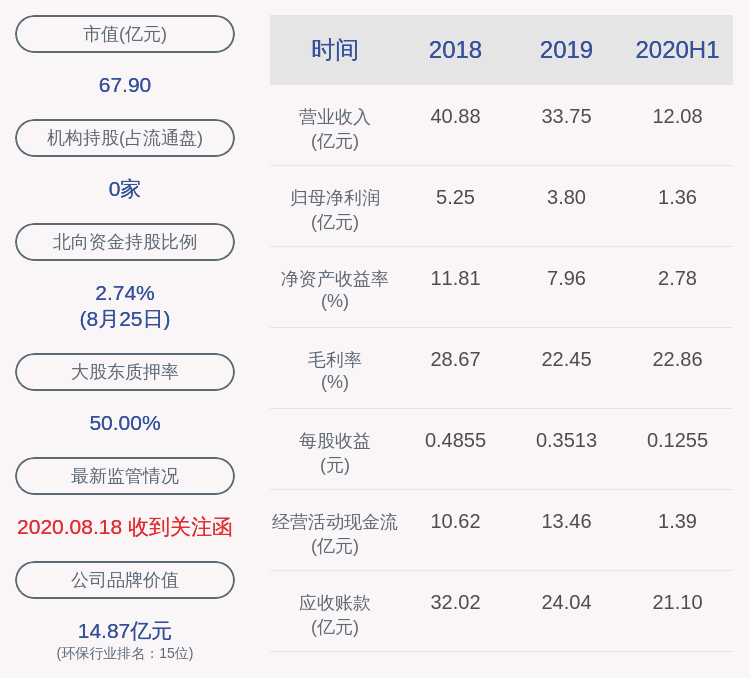дёӯеӣҪж–°й—»е‘ЁеҲҠ|йӘҶд»ҘеҶӣпјҡжҲ‘жҳҜвҖңеӨ–жҳҹдәәеҗҺд»ЈвҖқ( дёү )
йӘҶд»ҘеҶӣжҖ»з»“еҮә пјҢ е°ҸиҜҙ家жҳҜжңҖжңүи§’иүІж„ҸиҜҶзҡ„дёҖзҫӨдәә пјҢ 他们具жңүеҲҮжҚўи§’иүІзҡ„иҮӘи§ү гҖӮ д»–еј•з”Ёзұіе…°В·жҳҶеҫ·жӢүзҡ„иҜқиҜҙ пјҢ е°ҸиҜҙжҳҜвҖңеҹәдәҺеҜ№дәҺи§ӮжөӢдәәзұ»еӯҳеңЁеҪўжҖҒзҡ„дёҖз§ҚзӢӮзғӯвҖқ гҖӮ жүҖд»Ҙ пјҢ йӘҶд»ҘеҶӣж— и®әжҳҜзңӢйӮЈдәӣеҸЈж°ҙиҠӮзӣ® пјҢ иҝҳжҳҜиҜ»йҮҸеӯҗеҠӣеӯҰеҸҲжҲ–иҖ…зңӢдәәе–қй…’еҗ№зүӣ пјҢ д»–ж„ҹе…ҙи¶Јзҡ„ж— йқһйғҪжҳҜйӮЈд»ӨдәәжғҠеҸ№зҡ„еӨҚжқӮдё–з•Ңдёӯзҡ„дәә гҖӮ
е°ҸиҜҙжІЎжӯ» пјҢ еёқеӣҪд»ҚеңЁ
й«ҳдёӯж—¶йӘҶд»ҘеҶӣзҡ„и§’иүІжҳҜвҖңе°ҸжөҒж°“вҖқвҖңеқҸдәәвҖқ пјҢ жІЎдәәи®Өдёәд»–дјҡжҲҗдёәе°ҸиҜҙ家 пјҢ иҜ»еӨ§еӯҰеҗҺ пјҢ вҖңеқҸдәәвҖқеҸҳжҲҗдәҶйҶүеҝғдәҺж–ҮеӯҰзҡ„дё–з•Ңзҡ„вҖңжҖӘдәәвҖқ гҖӮ 20дё–зәӘ90е№ҙд»ЈзЎ•еЈ«жҜ•дёҡеҗҺ пјҢ йӘҶд»ҘеҶӣеұ…然жҲҗдёәдәҶе°‘ж•°йӮЈз§ҚжІЎжҖҺд№ҲдёҠиҝҮзҸӯ пјҢ е°ұзӣҙжҺҘеҪ“дёҠиҒҢдёҡдҪң家зҡ„дәә гҖӮ
вҖңеқҸдәәвҖқдёҖж—ҰдёӢе®ҡеҶіеҝғ пјҢ е°ұжңүзқҖеҘҪеӯҰз”ҹдёҖиҲ¬зҡ„з”ЁеҠҹ пјҢ д»–з”ЁжүӢжҠ„зҡ„еҠһжі•е°Ҷз»Ҹе…ёдҪңе“Ғе’ҢиҜҚеҸҘзЎ¬з”ҹз”ҹеҲ»е…ҘиҮӘе·ұзҡ„еӨ§и„‘д№ӢдёӯвҖ”вҖ”д»–иҜҙжҠ„д№ҰжҳҜдёәдәҶе…ӢжңҚиҮӘе·ұзҡ„йҳ…иҜ»йҡңзўҚ гҖӮ д»–д№ҹдёҖзӣҙеқҡжҢҒжүӢеҶҷзЁҝ件 гҖӮ ж—¶иҮід»Ҡж—Ҙ пјҢ д»–иҝҳиғҪи„ұеҸЈеј•з”Ёз»Ҹе…ёдҪңе“Ғдёӯзҡ„еҶ…е®№ гҖӮ д»–жҠҠ20еІҒдёӢе®ҡеҶіеҝғиҝӣе…ҘиҝҷдёҖиЎҢ пјҢ иӢҰз»ғ10е№ҙжүҚиҝӣе…Ҙзҡ„йӮЈз§ҚзІҫзҘһ пјҢ еҪўе®№дёәвҖңж®үйҒ“вҖқ гҖӮ
еҰӮд»ҠеңЁеҸ°ж№ҫ пјҢ иҒҢдёҡдҪң家зҡ„з”ҹеӯҳжҜ”иҫғиү°йҡҫ пјҢ еҮәзүҲеёӮеңәеҮ д№Һе…»дёҚиө·дёҖдёӘзәҜж–ҮеӯҰдҪң家 гҖӮ еңЁйӘҶд»ҘеҶӣиә«иҫ№зҡ„еҗҢиҫҲжҲ–е№ҙиҪ»дёҖиҫҲдҪң家жңӢеҸӢдёӯй—ҙ пјҢ жңүдәәеҮәиҝҮдёҖдёӨжң¬д№Ұе°ұй”ҖеЈ°еҢҝиҝ№пјӣжңүдәәиҠұи®ёеӨҡе№ҙеҚҮеҲ°жӯЈж•ҷжҺҲд№ӢеҗҺжүҚжңүж—¶й—ҙеҶҷдҪңпјӣеҫҲеӨҡдәәжІЎжҲҗ家 пјҢ жҲ–иҖ…з»“е©ҡдәҶиҝ«дәҺеҺӢеҠӣдёҚиҰҒеӯ©еӯҗ гҖӮ иҖҢд»–зҡ„дёҠдёҖиҫҲдҪң家еҜ№иҮӘе·ұзҡ„иҒҢдёҡдјјд№ҺжӣҙжңүзЎ®е®ҡжҖ§ пјҢ д№ҹжӣҙжІЎжңүз”ҹеӯҳзҡ„еҺӢеҠӣ гҖӮ д»–еҖҹз”ЁдәҶеӨ§жұҹеҒҘдёүйғҺзҡ„иҜҙжі•иЎЁзӨә пјҢ иҜҙеҲ°еә• пјҢ еҰӮд»ҠдҪң家已дёҚеҶҚжҳҜж•ҙдёӘзӨҫдјҡзІҫзҘһжҖ§зҡ„д»ЈиЁҖдәәвҖ”вҖ”иҜёеҰӮеҠЁз”»зүҮеҜјжј”жҲ–иҖ…Lady GaGaд№Ӣзұ»зҡ„дәәзү©жүҚжҳҜ гҖӮ
йӘҶд»ҘеҶӣеңЁеӨ§еӯҰе…јиҒҢж—¶жҺҘи§ҰеҲ°зҡ„дёҖдәӣе№ҙиҪ»дәә пјҢ иҰҒиҠұеӨ§еҠӣж°”еҺ»е“„ пјҢ 他们жүҚж„ҝж„ҸеҺ»зңӢзңӢд№Ұ гҖӮ дҪҶд»–еҜ№иҝҷз§ҚзҠ¶еҶөеҚҒеҲҶзҗҶи§Ј пјҢ еңЁд»–зңӢжқҘ пјҢ е°ҸиҜҙжҳҜеёқеӣҪзҡ„дә§зү© пјҢ иҖҢж•ҙдёӘеҚҺж–Үдё–з•Ң пјҢ ж— и®әеӨ§йҷҶгҖҒеҸ°ж№ҫгҖҒйҰҷжёҜгҖҒ马жқҘиҘҝдәҡ пјҢ з”ҡиҮідёҚиҜҙдёӯж–Үзҡ„еҚ°еәҰ пјҢ ж—©е°ұеңЁеҮ зҷҫе№ҙеүҚе°ұиў«иҘҝж–№жҺ еӨәдәҶ гҖӮ вҖңдәә们еҝ…йЎ»иҰҒеҠӘеҠӣи¶…ж—¶е·ҘдҪң пјҢ е·Із»ҸжІЎжңүи¶іеӨҹзҡ„ж–ҮжҳҺпјҲеҹәзЎҖпјү пјҢ еҺ»жү©еј 他们еҝғйҮҢзҡ„з©әй—ҙ гҖӮ вҖқ
е“ҲдҪӣеӨ§еӯҰдёңдәҡзі»жҡЁжҜ”иҫғж–ҮеӯҰзі»и®Іеә§ж•ҷжҺҲзҺӢеҫ·еЁҒжӣҫе®ҡд№үиҝҮвҖңеҚҺиҜӯж–ҮеӯҰвҖқзҡ„еҗ«д№ү пјҢ еҚід»ҘдёӯеӣҪж–ҮеӯҰдёәеқҗж Ү пјҢ еңЁдёҚеҗҢзҡ„ең°еҢәгҖҒеӣҪ家з”ҡиҮідёҚеҗҢж–ҮеҢ–зҡ„еңәеҹҹйҮҢйқў пјҢ д»ҘеҚҺиҜӯдҪңдёәжІҹйҖҡзҡ„ж–№ејҸ пјҢ д»ҘеҚҺиҜӯдҪңдёәеҲӣдҪңзҡ„еӘ’д»Ӣзҡ„ж–ҮеӯҰ гҖӮ иҖҢеңЁи‘—дҪңгҖҠеҪ“д»Је°ҸиҜҙдәҢеҚҒ家гҖӢдёӯ пјҢ зҺӢеҫ·еЁҒж—ўи®әиҝ°дәҶзҺӢе®үеҝҶгҖҒиҺ«иЁҖгҖҒеҸ¶е…ҶиЁҖзӯүеӨ§йҷҶдҪң家 пјҢ жңұеӨ©ж–ҮгҖҒйӘҶд»ҘеҶӣзӯүеҸ°ж№ҫдҪң家 пјҢ д№ҹи®әиҝ°дәҶжқҘиҮӘ马жқҘиҘҝдәҡзҡ„й»„й”Ұж ‘гҖҒжқҺж°ёе№ізӯүдәә гҖӮ
йӘҶд»ҘеҶӣе°ұеңЁиҝҷдёӘеҚҺиҜӯж–ҮеӯҰзҡ„еӨ§жЎҶжһ¶д№ӢдёӢеұ•ејҖеҶҷдҪң пјҢ ж—©е№ҙиӢҰз»ғеҶ…еҠҹ пјҢ еҰӮд»ҠеҚҙйқўдёҙж–ҮеӯҰд№Ҹдәәй—®жҙҘзҡ„зӘҳеўғ гҖӮ дҪҶиҝҷдәӣвҖңе°ҸиҜҙдј дәәвҖқдҫқж—§жғіиҰҒйҖҸиҝҮж–Үеӯ—е»әйҖ еұһдәҺеҚҺдәәзҡ„ж–Үеӯ—еёқеӣҪ гҖӮ вҖңеёҢжңӣиғҪеӨҹиҝӣе…ҘеҲ°еҚЎеӨ«еҚЎзҡ„еңәжҷҜдёӯ пјҢ иҝӣе…ҘеҲ°еЎһдёҮжҸҗж–Ҝзҡ„ж•…дәӢдёӯ пјҢ д№ҹеёҢжңӣиғҪи·ҹйҷҖжҖқеҰҘиҖ¶еӨ«ж–ҜеҹәгҖҒ马尔е…Ӣж–Ҝе№іиө·е№іеқҗ гҖӮ вҖқйӘҶд»ҘеҶӣеҜ№гҖҠдёӯеӣҪж–°й—»е‘ЁеҲҠгҖӢиҜҙ гҖӮ
жӣҫз»Ҹ пјҢ еҸ°ж№ҫеӨ§еӯҰйҷ„иҝ‘зҡ„йӮЈдәӣзІҫзҫҺгҖҒж–Үиүәж°”жҒҜжө“еҺҡзҡ„е°Ҹе’–е•ЎйҰҶжҳҜйӘҶд»ҘеҶӣжҜҸеӨ©зҡ„е·ҘдҪңе®Ө пјҢ еҰӮд»Ҡ пјҢ д»–зҡ„дҪ“еҠӣе·Із»Ҹж— жі•ж”Ҝж’‘еңЁе’–е•ЎйҰҶд№…еқҗ пјҢ еҸӘиғҪеңЁжҜҸеӨ©зҡ„еӣәе®ҡж—¶й—ҙ пјҢ еңЁж—…йҰҶејҖдёӘй’ҹзӮ№жҲҝеҶҷдҪң гҖӮ дҪҶд»–е’Ңд»–дёәж•°дёҚеӨҡзҡ„еҗҢдҫӘ пјҢ д»Қ然ж—ҘеӨҚдёҖж—Ҙ пјҢ еңЁиў«зҪ‘з»ңе’ҢжҠҖжңҜжү“зўҺзҡ„дё–з•ҢйҮҢдёҖзӮ№дёҖзӮ№жӢјеҮ‘зқҖе°ҸиҜҙзҡ„ж„Ҹд№ү гҖӮ жӯЈеҰӮеҗҢгҖҠеҢЎи¶…дәәгҖӢе°Ғеә•дёҠеҶҷзҡ„йӮЈж®өиҜқпјҡвҖңжҲ‘еёҢжңӣиҮӘе·ұиғҪиөҺеҒҝеӣһе№ҙиҪ»дәәеҜ№ж–ҮеӯҰзҡ„еёҢжңӣ пјҢ жҲ‘еёҢжңӣдәә们еңЁиҝҷзӣёжҝЎд»ҘжІ« гҖӮ вҖқ
жҺЁиҚҗйҳ…иҜ»
- зҺӢиҺҪ|еңЁиҝҷдёӘй—®йўҳдёҠпјҢжӯҰеҲҷеӨ©дёҺзҺӢиҺҪзҡ„зӯ”жЎҲдёәдҪ•е®Ңе…ЁдёҖиҮҙ
- жұҹиҜ—дё№йЎҝ|жұҹиҜ—дё№йЎҝеҸ‘еёғMalte马иҖід»–зі»еҲ—зғҹйқ’иүІдёӯеӣҪйҷҗйҮҸж¬ҫи…•иЎЁ йҷҗйҮҸеҸ‘иЎҢ100жһҡ
- иұӘе®…|100е№ҙеүҚзҡ„дёӯеӣҪ第дёҖиұӘе®…пјҢйҖ д»·дёүеҚғдёҮдёӨзҷҪ银пјҢйҮҚе»әиҠұиҙ№6дёӘдәҝ
- з»Ҹи§ӮжұҪиҪҰ|дёӯеӣҪиұӘеҚҺиҪҰ10е№ҙд№ӢеҸҳпјҡBBAзҡ„дәүйңёеҸҳиҝҒеҸІдёҺж„Ҹж–ҷеӨ–зҡ„вҖңж–°й»„йҮ‘ж—¶д»ЈвҖқ | з»Ҹи§ӮжұҪиҪҰ
- зҺӢйҳҝе§Ё|дёӯеӣҪ60еҗҺеҘіжҖ§пјҡз”ҹжҙ»жңҖиӢҰдёҖд»ЈдәәпјҢе№ҙиҪ»ж—¶дёҚй—ІзқҖпјҢжҷҡе№ҙеӯҗеҘідёҚж¶ҲеҒң
- йҷҲжҙӘж–Ң|жЈ®жһ—иүҮй•ҝ
- еҚҒе °еёӮ|ж№–еҢ—10ең°иҺ·вҖңдёӯеӣҪжңҖзҫҺвҖқпјҢзңӢе®Ңжғіжү“еҚЎпјҒ
- йҷ¶з“·|第дәҢеҚҒеұҠдёӯеӣҪпјҲж·„еҚҡпјүеӣҪйҷ…йҷ¶з“·еҚҡи§Ҳдјҡ9жңҲ6ж—ҘвҖ”13ж—ҘдёҫиЎҢ
- йҳҝе°”еұұ|дёӯеӣҪзүҲе°Ҹз‘һеЈ«зҒ«дәҶпјҢжј«еұұйҒҚйҮҺйҮ‘й»„пјҢ9жңҲиө·е°ҶеҲ·зҲҶжңӢеҸӢеңҲпјҒ
- е…ғжңқ|ж»Ўж—ҸдәәеҸЈиҝңе°‘дәҺжұүж—ҸпјҢдёәд»Җд№ҲиғҪе»әз«Ӣжё…жңқпјҢз»ҹжІ»дёӯеӣҪдёӨзҷҫеӨҡе№ҙпј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