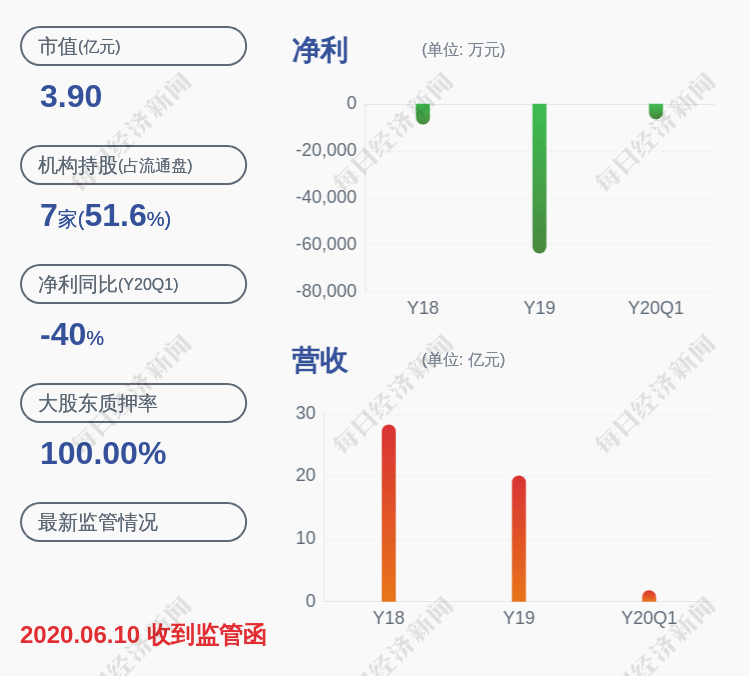ж–ҮеӯҰжҠҘ|еңЁж јйқһдёҺжһ—зҷҪзҡ„иҝҪеҝҶдёӯпјҢеҪ“е№ҙзҡ„иҜӯиЁҖжёёжҲҸжәҗиҮӘеҜ№жө…дҝ—е’Ңдё–ж•…зҡ„жҠөжҠ—( дәҢ )
жң¬ж–ҮжҸ’еӣҫ
ж–№иЁҖиҖғеҜҹзҡ„жңҖеҗҺдёҖз«ҷжҳҜжў…еҹҺ пјҢ жҲ‘们е®үжҺ’еҘҪдәҶдёҖиЎҢдәәзҡ„йҘ®йЈҹиө·еұ…д№ӢеҗҺ пјҢ йўңж•ҷжҺҲжҲ–и®ёи®ӨдёәжҲ‘们еҶҚд№ҹжҙҫдёҚдёҠд»Җд№Ҳз”ЁеңәдәҶ пјҢ дҫҝжү“еҸ‘жҲ‘们早早иёҸдёҠиҝ”ж Ўзҡ„еҪ’зЁӢ гҖӮ
жҲ‘дёҺдёҖдёӘеҘіж•ҷеёҲеҗҢиЎҢ гҖӮ жҲ‘е·Іи®°дёҚиө·еҘ№зҡ„еҗҚеӯ— пјҢ еҸӘжҳҜи®°еҫ—еҘ№еқҗеңЁжҲ‘зҡ„еҜ№йқў пјҢ е‘ҠиҜүжҲ‘иҝҷзҸӯеҲ—иҪҰејҖеҲ°дёҠжө·зәҰйңҖеҚҒдәҢдёӘе°Ҹж—¶ пјҢ йҡҸеҗҺдҫҝдёҖиЁҖдёҚеҸ‘ гҖӮ еңЁиҝҷеҚҒдәҢдёӘе°Ҹж—¶йҮҢ пјҢ жҲ‘еқҗеңЁжӢҘжҢӨеҳҲжқӮзҡ„иҪҰеҺўйҮҢ пјҢ еңЁи…җзғӮеҸ‘иҮӯзҡ„йұјиҷҫзҡ„ж°”е‘ідёӯ пјҢ дёәдәҶжү“еҸ‘еҜӮеҜһ пјҢ дҫҝеңЁж—Ҙи®°жң¬дёҠеҶҷдёӢдәҶиҝҷдёӘж•…дәӢ гҖӮ
еӣһеҲ°дёҠжө·еҗҺ пјҢ йҖӮйҖўгҖҠдёӯеӣҪгҖӢжқӮеҝ—зӨҫзҡ„зҺӢдёӯеҝұе…Ҳз”ҹжқҘжІӘз»„зЁҝ пјҢ жһ—дјҹж°‘е’ҢеҫҗиҠіиҖҒеёҲд»Ӣз»ҚжҲ‘и®ӨиҜҶдәҶзҺӢдёӯеҝұ гҖӮ д»–й—®жҲ‘жңүж— зҺ°жҲҗзҡ„зЁҝеӯҗеҸҜд»Ҙз»ҷд»–еёҰиө° пјҢ жҲ‘иҜҙеҖ’жҳҜжңүдёҖзҜҮеҶҷзқҖзҺ©зҡ„дёңиҘҝ пјҢ е°ҡжңӘиӘҠеҶҷ гҖӮ зҺӢдёӯеҝұе°ұи®©жҲ‘жҠ„еҮәжқҘз»ҷд»–зңӢзңӢ пјҢ еҗҺжқҘ пјҢ иҝҷзҜҮе°ҸиҜҙе°ұеҲҠзҷ»еңЁгҖҠдёӯеӣҪгҖӢжқӮеҝ—1986е№ҙзҡ„еӣӣжңҲеҸ·дёҠ гҖӮ
зҺ°еңЁеӣһжғіиө·жқҘ пјҢ еҪ“ж—¶жӯЈеӣ дёәжғіеҶҷзқҖзҺ©зҺ© пјҢ еҖ’д№ҹж— жӢҳж— жқҹ пјҢ 并让жҲ‘ж„ҹеҸ—еҲ°дәҶж–ҮеӯҰеҲӣдҪңдёҠжңҖеҲқзҡ„иҮӘз”ұ гҖӮ е®ғеҜ№жҲ‘ж—ҘеҗҺзҡ„еҶҷдҪңдёҚж— иЎҘзӣҠ гҖӮ еӣ жӯӨ пјҢ жҲ‘иҮӘе·ұеҜ№иҝҷзҜҮвҖңеӨ„еҘідҪңвҖқж—¶еёёжҖҖзқҖзҫҺеҘҪзҡ„жғ…ж„ҹ гҖӮ
жһ—зҷҪ
жғіиө·гҖҠдёҖдёӘдәәзҡ„жҲҳдәүгҖӢ
еҲҠдәҺ1996е№ҙ6жңҲ27ж—Ҙж–ҮеӯҰжҠҘ
жң¬ж–ҮжҸ’еӣҫ
жң¬ж–ҮжҸ’еӣҫ
жҲ‘дёҚзҹҘйҒ“иҮӘе·ұжҳҜеҗҰжңүдёҖйғЁжҲҗеҗҚдҪң гҖӮ жҲҗеҗҚиҝҷдёӘиҜҚеҜ№жҲ‘жңүдёҖз§ҚеҺӢиҝ«ж„ҹ пјҢ е®ғеғҸдёҖеҘ—дёҚеҗҲиә«зҡ„иЎЈжңҚдҪҝжҲ‘дёҚзҹҘжүҖжҺӘ пјҢ е®ғжҜ”д»ҘеҫҖд»»дҪ•ж—¶еҖҷйғҪжӣҙжҸҗйҶ’жҲ‘ пјҢ жҲ‘д№ҹ许并дёҚйҖӮеҗҲз«ҷеңЁйӮЈж ·дёҖдёӘдҪҚзҪ® гҖӮ дәӢе®һзҡ„зЎ®е°ұжҳҜиҝҷж · гҖӮ
еҪ“жҲ‘еӣһжғіиҮӘе·ұзҡ„дҪңе“Ғ пјҢ жғіиҰҒжүҫеҮәдёҖйғЁзҹҘйҒ“зҡ„дәәеӨҡдёҖдәӣзҡ„ пјҢ жҲ‘йҰ–е…ҲжғіеҲ°зҡ„жҖ»жҳҜгҖҠдёҖдёӘдәәзҡ„жҲҳдәүгҖӢ пјҢ жҲ‘жңҖеҗҺжғіеҲ°зҡ„д№ҹжҳҜе®ғ пјҢ дәҺжҳҜжҲ‘жқғдё”жҠҠе®ғдҪңдёәжҲҗеҗҚдҪңжқҘеӣһеҝҶдёҖз•Ә гҖӮ
еӣһеҝҶиҝҷдёӘиҜҚдҪҝжҲ‘ж„ҹеҲ°е®ғзҡ„еҶҷдҪңе·Із»ҸиҝҮеҺ»еҫҲд№…дәҶ гҖӮ жҲ‘з«ҷеңЁдёҖд№қд№қе…ӯе№ҙзҡ„еӨҸеӨ©зңәжңӣдёҖд№қд№қдёүе№ҙ пјҢ зңәжңӣе’ҢеӣһеҝҶйғҪи®©дәәж„ҹеҲ°еҒҡдҪң пјҢ е°ұеғҸзҰ»е®¶дёҚиҝҮеҚҒйҮҢе°ұз§°д№ӢдёәжөҒжөӘдёҖж · гҖӮ дҪҶеңЁжҲ‘зҡ„ж„ҹи§үдёӯ пјҢ е®ғзҡ„йҒӯйҒҮеӨӘеӨҡ пјҢ ж»Ўж»Ўең°е……еЎһеңЁиҝҷеҮ е№ҙдёӯ пјҢ е®ғзҡ„йҒӯйҒҮжӢүй•ҝдәҶж—¶й—ҙ пјҢ дҪҝжҲ‘ж— з«Ҝең°ж„ҹеҲ°жІ§жЎ‘е’Ңйҡҗз—ӣ гҖӮ еӣһеҝҶиҝҷдёӘе§ҝеҠҝдҪҝжҲ‘жҠҠе®ғжүҖз»ҸеҺҶзҡ„дәӢжғ…жҺЁеҲ°иҝңеӨ„ пјҢ иҖҢеҜ№иҝңеӨ„зҡ„еҮқи§ҶдјҡдҪҝжҲ‘е®үйқҷдёӢжқҘ гҖӮ
зӣёеҜ№дәҺиҝҷйғЁе°ҸиҜҙеҸ‘иЎЁеҗҺзҡ„з»ҸеҺҶ пјҢ е®ғзҡ„еҶҷдҪңиҝҮзЁӢз®ҖеҚ•д№ӢжһҒ гҖӮ дәӢе…ҲжІЎжңүй…қй…ҝ пјҢ еңЁеҠЁз¬”еҶҷдҪңзҡ„еүҚдёҖеӨ©жҲ‘并дёҚзҹҘйҒ“иҮӘе·ұиҰҒеҶҷиҝҷж ·дёҖйғЁдҪңе“Ғ пјҢ еңЁиҝҷд№ӢеүҚжҲ‘еҲҡеҲҡеҶҷдәҶгҖҠ瓶дёӯд№Ӣж°ҙгҖӢе’ҢгҖҠеӣһе»Ҡд№ӢжӨ…гҖӢ пјҢ жҲ‘ж„ҹеҲ°иҮӘе·ұйҮҚж–°жүҫеӣһдәҶеҜ№е°ҸиҜҙзҡ„иҜӯиЁҖж„ҹи§ү пјҢ з”ұдәҺж–°й—»еҶҷдҪңзҡ„规иҢғ пјҢ жңүдёҖж®өж—¶й—ҙжҲ‘е·®дёҚеӨҡдёўеӨұдәҶж–ҮеӯҰзҡ„иҜӯж„ҹ гҖӮ иҜӯж„ҹзҡ„еҲ°дҪҚдҪҝжҲ‘и§үеҫ—иҮӘе·ұжӯЈеқҗеңЁж»‘жўҜеҸЈдёҠ пјҢ жңүдёҖз§ҚеҫҖдёӢж»‘зҡ„еҶІеҠЁ гҖӮ дәҺжҳҜеңЁд№қдёүе№ҙеӣӣжңҲзҡ„дёҖеӨ© пјҢ жҲ‘и§үеҫ—иҮӘе·ұеҫҲжғіеҶҷдёҖйғЁй•ҝдёҖдәӣзҡ„дҪңе“Ғ пјҢ дәҺжҳҜжҲ‘жҸҗиө·з¬” пјҢ еҶҷдёӢдәҶиҝҷж ·дёҖеҸҘиҜқпјҡеҘіеӯ©еӨҡзұізҠ№еҰӮдёҖеҸӘйқ’涩еқҡзЎ¬зҡ„з•ӘзҹіжҰҙ пјҢ з»“зјҖеңЁBй•ҮеІҒжңҲзҡ„жһқеӨҙдёҠ пјҢ з©ҝиҝҮжҲ‘зҡ„и®°еҝҶй—Әй—ӘеҸ‘е…ү гҖӮ иҝҷжҳҜеҪ“ж—¶зҡ„ејҖеӨҙ гҖӮ иҝҷдёӘејҖеӨҙдҪҝжҲ‘ж„ҹеҲ°е°ҸиҜҙе°ҶдјҡеҚҒеҲҶйЎәеҲ©ең°дёҖж°”е‘өжҲҗ гҖӮ еҗҺжқҘзЎ®жҳҜеҰӮжӯӨ пјҢ жүӢзЁҝе№ІеҮҖж•ҙжҙҒ пјҢ йҷӨдәҶз« иҠӮзҡ„еүҚеҗҺйЎәеәҸдҪңдәҶдёҖзӮ№и°ғж•ҙ пјҢ жүҖжңүзҡ„иҜӯеҸҘеҮ д№ҺеҫҲе°‘ж”№еҠЁ гҖӮ жҲ‘еҪ“ж—¶и§үеҫ—е®ғ们е°ұеғҸжҳҜеӨ©дёҠжҺүдёӢжқҘзҡ„ж°ҙж»ҙ пјҢ еңҶж¶ҰиҖҢеӨ©з„¶ гҖӮ
еҪ“ж—¶жҲ‘зҡ„зҺ°е®һеӨ„еўғеҚҒеҲҶзіҹзі• пјҢ й«ҳеәҰзҡ„зІҫзҘһеҺӢеҠӣе’Ңи¶…еёёзҡ„е·ҘдҪңеҝҷд№ұ пјҢ дҪҶе®ғ们没жңүдҫөе…ҘжҲ‘зҡ„дҪңе“Ғ гҖӮ еҶҷдҪңдҪҝжҲ‘еңЁзһ¬й—ҙйЈһзҰ»зҺ°е®һ пјҢ е®ғжҳҜжҲ‘е…ҚеҸ—иҮҙе‘ҪдјӨе®ізҡ„йЈһжҜҜ гҖӮ
жң¬ж–ҮжҸ’еӣҫ
в– 20е‘Ёе№ҙзәӘеҝөзүҲ пјҢ иҠұеҹҺеҮәзүҲзӨҫ2015е№ҙ
гҖҠдёҖдёӘдәәзҡ„жҲҳдәүгҖӢеҸ‘иЎЁеңЁд№қеӣӣе№ҙ第дәҢжңҹзҡ„гҖҠиҠұеҹҺгҖӢжқӮеҝ—дёҠ пјҢ еҗҢе№ҙз”ұжңӢеҸӢд»Ӣз»ҚеҲ°иҘҝеҢ—зҡ„дёҖ家еҮәзүҲзӨҫ пјҢ жҲ‘жӢ…еҝғиҘҝеҢ—ең°еӨ„еҒҸиҝң пјҢ и®ҫи®ЎдёҚдәҶжҲ‘ж»Ўж„Ҹзҡ„е°Ғйқў пјҢ зү№ж„ҸеңЁеҢ—дә¬иҜ·йқ’е№ҙе°Ғйқўи®ҫ计家ж—әеҝҳжңӣи®ҫи®ЎдәҶе°Ғйқў пјҢ 并用зү№еҝ«дё“йҖ’еҜ„еҺ» гҖӮ жІЎжғіеҲ°д»–们иҪ»жҳ“е°ұеҗҰе®ҡдәҶиҝҷдёӘи®ҫи®Ў пјҢ д»Јд№Ӣд»ҘдёҖе№…зңӢиө·жқҘдҪҝдәәдә§з”ҹиүІжғ…иҒ”жғізҡ„зұ»дјјжҳҘе®«еӣҫзҡ„ж‘„еҪұдҪңе°Ғйқў гҖӮ е…ідәҺжҳҘе®«еӣҫдёҖиҜҙ пјҢ 并дёҚжҳҜжҲ‘дёҖе·ұзҡ„еӨёеӨ§е’ҢеҒҸи§Ғ пјҢ иҖҢжҳҜжҠҘеҲҠдёҠиҜ„и®ә家е’ҢиҜ»иҖ…зҡ„еҺҹиҜқ гҖӮ йқўеҜ№жҲ‘зҡ„иҜҳй—® пјҢ иҙЈзј–ејәи°ғиҜҙиҝҷжҳҜдёҖе№…з”ұи‘—еҗҚж‘„еҪұ家жӢҚж‘„зҡ„и‘—еҗҚзҡ„ж‘„еҪұдҪңе“Ғ гҖӮ иҝҷиҝҳдёҚз®— пјҢ иҝҷжң¬д№ҰеҶ…ж–Үж ЎеҜ№зІ—з–Ҹ пјҢ жңҖдёҘйҮҚзҡ„дёҖйЎөе·®й”ҷз«ҹиҫҫеҚҒдә”еӨ„ пјҢ иҝҷз§Қз§Қи°¬иҜҜдҪҝжҲ‘еҚҒеҲҶж°”ж„Ө пјҢ еҮәзүҲзӨҫйҖҡиҝҮиҙЈзј–дҪңдәҶдёҖдәӣйҒ“жӯүе’Ңи§ЈйҮҠ пјҢ 并дҝқиҜҒ马дёҠжҚўдёҖдёӘ пјҢ еҮәдёҖдёӘи®ўжӯЈзүҲ пјҢ жҲ‘жҺҘеҸ—дәҶ гҖӮ дҪҶжҲ‘дёҖзӣҙжІЎжңүзӯүеҲ°иҝҷдёӘзүҲжң¬ гҖӮ еңЁжҲ‘зҡ„дёҖеҶҚеӮ¬дҝғдёӢ пјҢ жүҚеңЁдёҖд№қд№қдә”е№ҙеҚҒжңҲд»Ҫ收еҲ°дёҖд»ҪеҗҢж„ҸжҲ‘ж’Өеӣһдё“жңүдҪҝз”Ёжқғзҡ„еҮҪ件 гҖӮ иҝҷд№ӢеҗҺжӣҫжңүжІіеҢ—зҡ„дёҖ家еҮәзүҲзӨҫеҗҢж„ҸеҮәзүҲжӯӨд№Ұ并已зӯҫи®ўдәҶеҗҲеҗҢ пјҢ дҪҶеҮ еӨ©д№ӢеҗҺеҸҲеӣ ж•…и§ЈйҷӨдәҶ пјҢ жҲ‘иҮід»Ҡд№ҹжІЎжӢҝеҲ°еҗҲеҗҢдёҠ规е®ҡзҡ„иө”еҒҝ 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жҳҹеә§е…ҲжЈ®|жӢҝеҫ—иө·ж”ҫеҫ—дёӢпјҢжҖ§ж јйқһеёёеӨ§ж°”зҡ„4дёӘз”ҹиӮ–
- ж–ҮеӯҰжҠҘ|иө°иҝ‘新科иҜәеҘ–еҫ—дё»йңІжҳ“дёқВ·ж јдёҪе…ӢпјҡеҘ№йҖғзҰ»дёҖеҲҮпјҢеҸӘеёҢжңӣз”ЁиҜ—жӯҢйҮҚжһ„ж•ҙдёӘдё–з•Ң
- жөҷеӨ§еӯҰжҠҘиӢұж–ҮзүҲ|жөҷжұҹеӨ§еӯҰйҷҲејҲе®Ғзӯү | еҹәдәҺGPSRе’ҢQзҪ‘з»ңзҡ„жөҒйҮҸж„ҹзҹҘж— дәәжңәad-hocзҪ‘з»ңи·Ҝз”ұеҚҸи®®
- ж–ҮеӯҰжҠҘ|ж–ҮеӯҰжҳҜдёҖжқҹе…үпјҢеңЁдҪ•йЎҝе’Ңз«№жһ—зҡ„з”ҹе‘ҪйҮҢеҸҚеӨҚжҝҖиҚЎ | 40е№ҙВ·жҳҹиҫ°еӣһе“Қ
- ж–ҮеӯҰжҠҘ|еҸ¶иҫӣдёҺеҸ¶ж°ёзғҲзҡ„ж–ҮеӯҰеҲқзҜҮпјҢеңЁзҝ»йЎөдёӯз”ұиҝҮеҫҖиө°еҗ‘жңӘжқҘ | 40е№ҙВ·жҳҹиҫ°еӣһе“Қ
- еұұдёңиҙўз»ҸеӨ§еӯҰжҠҘ|зҝ»ејҖд№Ұ | иғёдёӯиҮӘжңүдёҳеЈ‘
- ж–ҮеӯҰжҠҘ|д»Һи§ҒиҜҒвҖңе…Ҳй”ӢвҖқеҲ°иҗҢеҸ‘иҮӘе·ұзҡ„еЈ°йҹіпјҢйӮұеҚҺж Ӣе’ҢдёңиҘҝеҜ»жүҫж–°зҡ„еҸҷиҝ°з©әй—ҙ | 40е№ҙВ·жҳҹиҫ°еӣһе“Қ
- ж–ҮеӯҰжҠҘ|д»Һе‘Ҫиҝҗзҡ„еҘ‘жңәеҲ°д№үж— еҸҚйЎҫзҡ„еҶҷдҪңпјҢеҲҳйҶ’йҫҷдёҺйӮ“дёҖе…үеҸ©ејҖж–ҮеӯҰзҡ„еӨ§й—Ё | 40е№ҙВ·жҳҹиҫ°еӣһе“Қ
- ж–ҮеӯҰжҠҘ|е…Ҳй”Ӣж–ҮеӯҰиўӯжқҘзҡ„еүҚеӨңпјҢиӢҸз«Ҙе’ҢдҪҷеҚҺжүҫеҲ°дәҶдёҺдё–з•Ңжү“дәӨйҒ“зҡ„ж–№ејҸ | 40е№ҙВ·жҳҹиҫ°еӣһе“Қ
- ж–ҮеӯҰжҠҘ|дҪң家йңҖиҰҒе®Ўи§Ҷзҡ„жҳҜеҶ…еҝғжҳҜеҗҰиҝҳи‘Ҷжңүж–ҮеӯҰз«Ӣеңә | е…ұиҜқж–°вҖңе°ҸиҜҙйқ©е‘ҪвҖқзі»е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