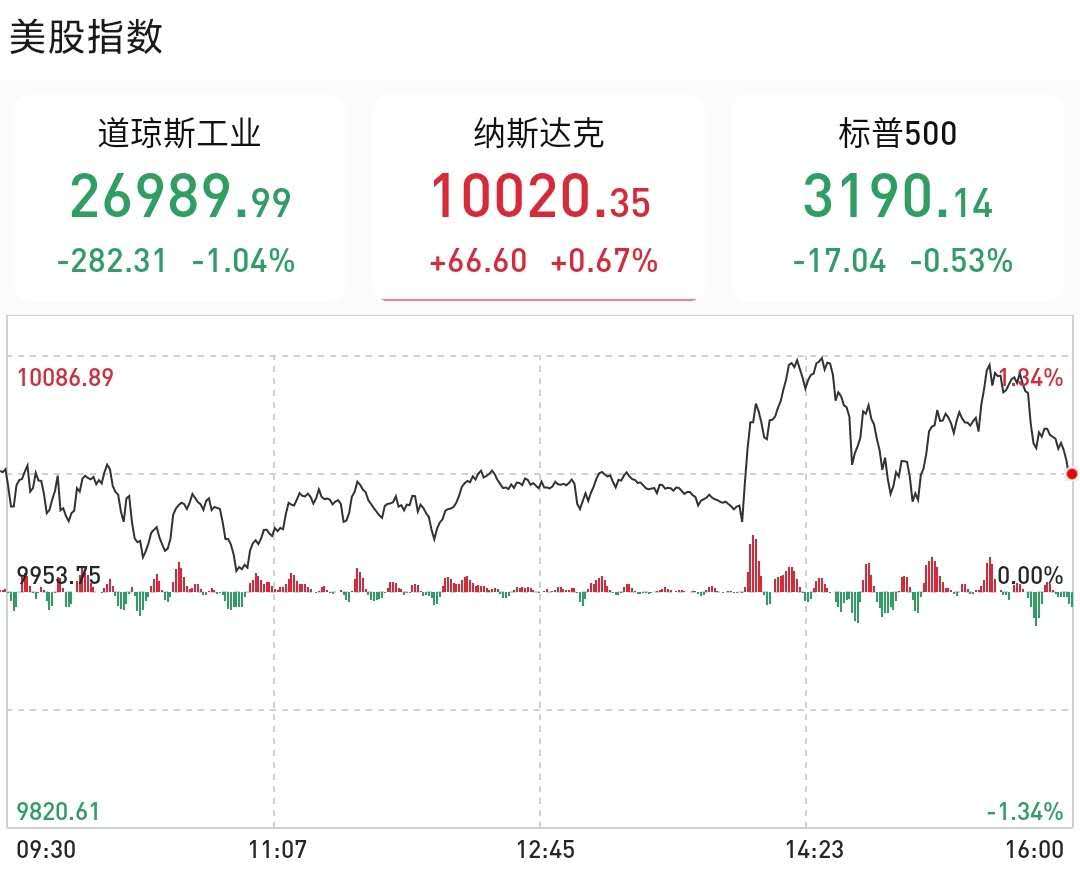原子智库原子智库| Uber在美遇法律风波,会否形成共享经济平台用工蝴蝶效应?( 三 )
按照一些平台的说法 , B模式是基础运力 , C模式是补充运力 , 只有维持稳定的基础运力 , 才能确保完成每日订单量 。 那么 , 真正意义的平台用工就是C模式 。 而这种模式与现有劳动组织体系有何区别呢?
平台用工在世界范围内早期的代表是Uber平台打车 , 以共享经济的名义开启了社会车辆进入客运的通道 。 国内平台用工大规模兴起是2014年 , 网约车、外卖送餐、城市快递、代驾等蓬勃发展 。 这一现象的形成 , 主要来自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智能手机、定位服务与平台算法 , 共同塑造了平台用工;城市的服务需求和相对宽松的法律环境 , 为平台用工提供了疯狂生长的养分 。
而从时间轴来看 , 平台用工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灵活用工发展的结果 , 背景是服务业兴起 , 社会需求多元化 。 全日制用工契合工业化生产 , 却无法满足服务业需要 , 灵活用工成为一种趋势 。 到了网络时代 , 平台用工仍是主要针对服务业 , 创新性体现在将立体的组织化用工 , 转变为平面的平台化用工 。
就我国的平台用工而言 , 其在结构上是组织化与平台化的混合物 。 平台通过代理商实现组织化 , 同时通过众包劳动实现平台化 , 以便兼顾效率与灵活 。 那么 , 众包劳动的C模式主要充当了现有劳动组织体系的补充 , 也可以说是在已有就业模式之外开辟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劳务给付方式 。
如果说A和B模式是平台牵头搭建起了用工组织 , C模式则是平台利用网络技术将原本分散、小额的民事劳务活动聚拢到平台上 , 通过开放准入、快速匹配 , 实现了服务的社会化 。 依据各主要平台的参与人数来评估 , C模式下的网约工是几百万人的量级 , 在全国7.7亿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低 。 因此 , 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劳动关系过时了 , 也不足以得出“平台用工将颠覆现有劳动组织体系”的结论 。
需要澄清的第三个误解:平台用工是对劳动法的挑战 , 起到了规避劳动法的作用 。 对此有两个基本回答:一是平台用工和劳动法各有各的问题;二是平台用工如同任何一种用工形式 , 都存在不规范之处 , 但应区分定性问题与执行问题 。
就第一点而言 , A和B两种模式均存在劳动合同 , 当然适用劳动法 , 问题在于C模式 , 其法律关系定性存有争论 。 而劳动法的问题是对各类用工主体采取了“一刀切”的调整机制 , 不区分行业、规模等特点 , 没有小企业豁免的规则 。 因此 , 劳动法需要针对组织化用工设计更弹性的制度 , 而平台用工则需要针对C模式构建专门的制度 , 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
就第二点而言 , “以非劳动关系之名行劳动关系之实”的“隐蔽雇佣”早已存在 , 一些试图不正当降低成本的企业 , 打起了平台用工的主意 , 实际上是既不想承担劳动关系的成本 , 又想获得劳动关系的好处 。 “隐蔽雇佣”是劳动法的老问题 , 属于确认劳动关系争议 。 平台用工亦不乏此类案件 , 法院有丰富的审判经验 , 耍小聪明是行不通的 。
而C模式作为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平台用工 , 对企业是有很高要求的 , 企业基本上要放弃对劳动力的直接管理和支配 。 试问:有多少企业在此条件下能实现有效的劳动力组织 , 完成业务目标?
中国该如何选择
美国围绕Uber、Lyft的法律风波 , 归根到底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规范平台用工 。 从当前纷争来看 , 加州不想改变“劳动二分法” , 而是将平台用工纳入到劳动法中 。
我国也面对同样的问题 , 现行法律也是“劳动二分法” , 由《劳动法》和《民法》分别调整的“从属性劳动—独立性劳动”构成 。 在此框架下 , C模式难以被认定为劳动关系 , 而作为民事关系调整 , 又无法给予网约工有效的保障 。 需要强调的是 , 网约工不是《劳动法》上的劳动者 , 不意味着网约工不是弱者 。 网约工在工资、工作时间、职业伤害保障等多方面 , 有现实的社会保护需求 。
推荐阅读
- 搜狐智库|上市公司大亚圣象董事长陈晓龙突发脑溢血去世,时年44岁
- 界面新闻|Uber收购外卖Grubhub最新进展:正就大额分手费谈判
- |中国科协发布科技创业数字地图,打造公共数字智库平台
- 深网|深网 | 今日头条高级副总裁柳甄离职,曾任Uber中国战略负责人
- 不凡智库|被误认为是“国产”的洋品牌?其实早已是外资,你猜中几个?
- 美联储@美联储可还记得双重使命?著名智库批评:“All in”极端措施大错特错
- 安期智库期权周报 |期价整体下行,隐含波动率稳中有降
- 太阳界智库解析丨中广欧特斯快速发展的硬核“实招”
- 佩琪小为Uber拟收购外卖平台GrubHub 消息称双方未达成协议
- 搜狐智库黄奇帆: 18亿亩耕地红线必须守住,新《土地管理法》将带来几十万亿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