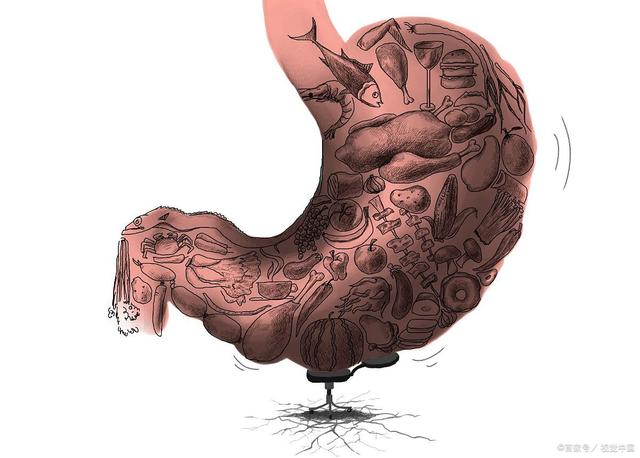单读|张悦然:是“情感的支点”捍卫着作家的真诚丨单读( 二 )
此外 , “情感的支点”可以帮我们解决一个重要的困难 , 那就是我们不必只写我们熟悉的人了 。 事实上 , 所谓的“熟悉”是很可疑的 。 表面看起来 , 朋友、恋人和家人离我们最近 , 我们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 了解他们的背景 , 知道他们的追求 ,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真的同他们之间具有“情感的支点” 。 恰恰相反 , 陌生、遥远的人 , 有可能因为一个“情感的支点” , 和我们产生更加深厚和坚固的缔结 。
我们的生活里有很多简单粗暴的对人的分类 , 比如身份、社会阶层 。 一个人属于什么阶层 , 他就应该具有这个阶层的行为特征、价值追求 。 有人希望作者更多地关注底层 , 因为他们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 , 但是有的评论者又会站在另一边批评这样的写作 , 认为不了解底层的人 , 写出来的底层是居高临下的 , 始终带有优越感 。 作者本人也会受到暗示 , 下意识地把笔下的人物归入某个类别 , 好像获得了一个抓手 。 有时候这个抓手会有帮助 , 让你的人物看起来更真实 。 比如一个保姆独自在家 , 忽然有访客 , 还是一个外国人 , 冲着她说英语 。 没错 , 根据她的背景 , 她多半不会英语 , 所以你写道:“她不好意思地冲着外国人笑了笑 。 ”这可能听起来很真实 , 但同时它也是陈词滥调 。 你并没有揭露任何属于这个保姆的个人特质 , 到现在为止 , 她仍是一张纸片、一个符号 。 如果她是并不重要的角色 , 也许你可以这样蒙混过去 , 但如果她是一个主要角色 , 你就必须把她从你对阶层、身份的固化认知里解放出来 。
当然 , 这并不是说 , 涉入一个完全不熟悉的人物的时候 , 那些对他身份、处境的调查研究是不必要的 。 它们非常重要 。 它们带给我们信心 , 为写作赋以血肉 。 对于一些写作者来说 , 用一种写论文似的方法来收集资料 , 好像有违写作理念 , 也有失艺术的神秘性 。 另一些写作者则试图把创作里科学性的部分和艺术性的部分分开对待 。 比如麦克尤恩 , 他写外科医生 , 要去观摩人体解剖;他写大法官 , 要深入地研究英国的法律;他决定写人工智能——这时他已经 70 岁了 , 他了解这个领域的难度远大于年轻作家 , 但他依然通过收集大量资料 , 以及对相应领域人士的采访 , 成功地完成了这次书写 。 关于资料收集 , 我认为当事人的口述优于影像、优于文字资料 。 在所有获取资料的途径中 , 采访可能是最有效的 。 见面会营造一个开放的场域 , 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会被召唤进来 。 而且在见面的情况下 , 对方的讲述像一种重现 , 能够使你更多地浸入你的故事之中 。 其次是影像 。 我觉得影像比文字要好 , 因为影像有很多留白 , 大多数时候 , 影像本身是中立的 , 没有更多的立场 , 这都会留给创作者充裕的想象空间 。 但是很多时候 , 我们无法通过前面两种途径获得所需要的素材 , 还是要诉诸于文字资料 。 有些时候 , 写作者会淹没在文字资料里 , 因为真实的力量总是具有某种催眠作用 , 催眠掉了虚构的雄心 。 张爱玲早年生活经验非常苍白 , 依然可以写出如《倾城之恋》《金锁记》这样揭示复杂人性的作品 。 然而到了《秧歌》 , 张爱玲在序言里大声呼喊:“这个故事是真的!”因为它是真的 , 所以它获得了逻辑的庇护 , 在挑剔真实的读者那里得到了赦免 。 可是为什么真实事件按照原样安置在小说里 , 就会显得失真呢?我们必须明白 , 小说有其内在逻辑 , 就像另外一个太阳系 , 它有自己的运行规律 , 致使小说的逻辑已经偏离了真实事件的逻辑 。 它们不再是同心圆了 , 你甚至不能根据真实事件的公式 , 推导出适用于小说的公式 。 小说的内在逻辑由什么决定呢?在我看来 , 就是作者的情感支点 。 情感支点有点像船锚 , 义无反顾地扎进水里 , 它决定了一个小说的向心力 。
推荐阅读
- 单读|试着赞美这遭毁损的世界丨单读
- 文学报|张悦然的创意写作课:为经典小说重新搭起脚手架,甚至攀登路线 | 此刻夜读
- 单读|谁在歌唱这个贬值与失败的世界丨Editor’s Pick
- 单读|没有爱情的婚姻当然持久
- 吴越|?班宇:故事给我自由丨单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