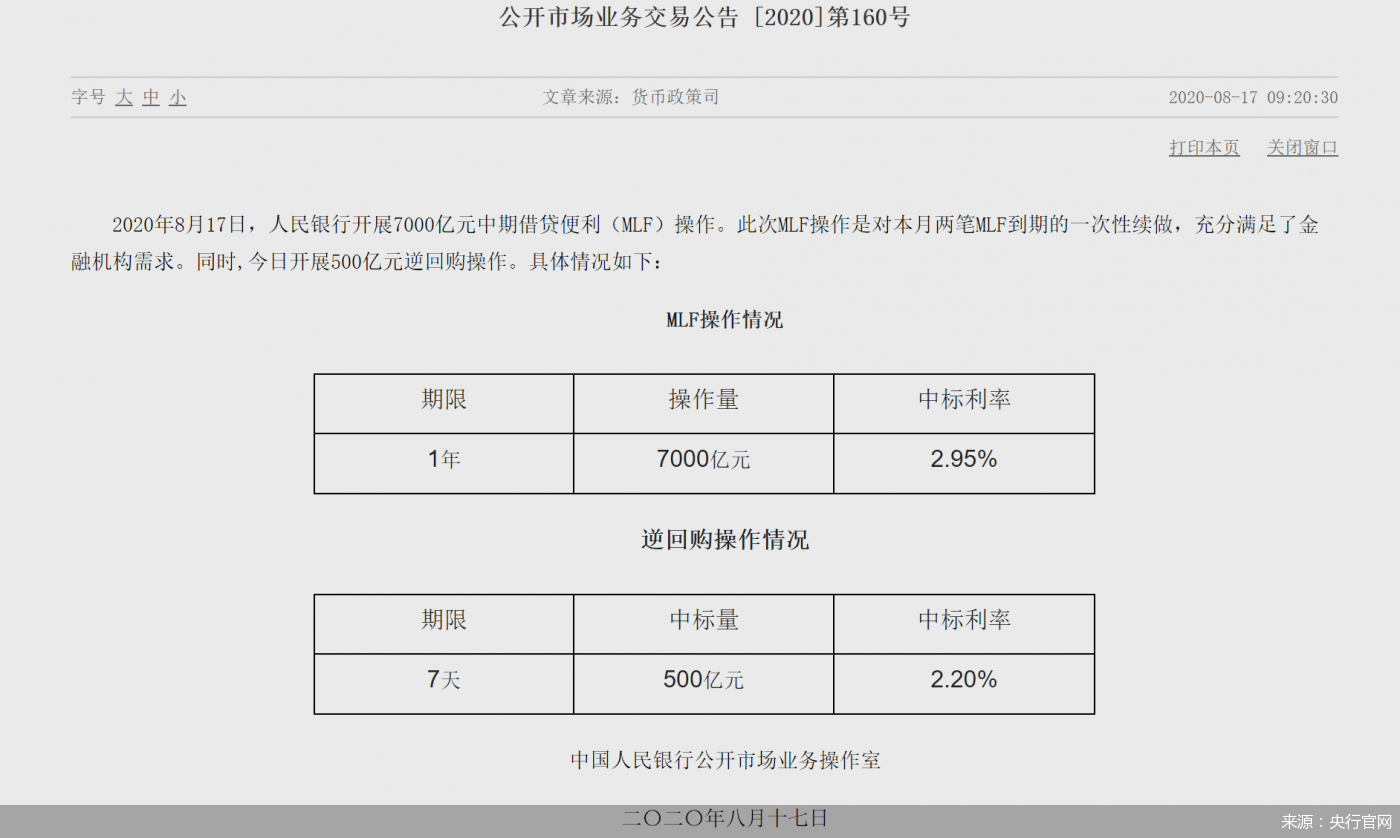从甘肃农村到北京后,家政阿姨也有了自己的梦
《大国小民》第1121期本文系网易“大国小民”栏目出品

14月刚刚开始 , 梦云就在老家待不住了 , 心里像有一股隐隐的火灼烤着 , 她从堂屋走到柴房 , 又从院坝回到灶头 , 走走停停 , 坐立不安 。其实过完年她就想回北京 , 但那时疫情形势还不明朗 , 她担心进不了雇主的小区 。 3月份 , 雇主委婉地告诉她 , 他们夫妻俩现在都在家办公 , 工资减半 , 孩子马上也能上幼儿园了 。 她一听就明白 , 这份做了3年的住家保姆工作 , 没有了 。从过年回老家算起 , 两个多月过去了 , 她觉得自己在家坐吃山空 。 这些年她已经习惯了不停干活、攒钱的节奏 。 在家待了一段时间 , 右手臂的骨头反而开始麻麻地疼 , 这是长期抱孩子造成的劳损 , 左腿膝盖也隐隐不舒服 , 就连右边的槽牙也掉落了一颗 。 工厂里鸣转的机器一旦停下来就容易出问题 , 人也是这样 。更让她受不了的是周围的气氛 。 年前 , 她拖了个塞得满满的箱子回到家 , 婆婆和丈夫凑过来看是什么好东西 , 谁知大半个箱子都是书 。 婆婆“唉”一声走开了 , 仿佛是刮开彩票后看到“谢谢” 。 丈夫则从鼻孔里放出嗤笑的粗气:“你说你把这些没用的玩意儿带回来干啥?不嫌沉吗?”梦云试图跟他解释:她在北京参加了一个专门由打工者组成的文学小组 , 每周都有大学老师、作家、编辑来给他们做讲座 , 还有北大的老师呢!你知道北大吗?咱们市每年高考能有几个考上北大?在他们的鼓励下 , 梦云也开始提起笔写自己的故事 , 有的还在文学小组的公众号上发表了 。 这些书都是老师们送给她的 , 她平时太累了 , 时时刻刻要顾着孩子和家务 , 没有时间看 , 但她一定要把它们带回来 , 她相信自己老了以后会在家把这些书看完的 。丈夫咂摸着“北大”两个字 , 他当然知道北大 , 但这两个字从妻子嘴里说出来 , 就觉得像是赝品 。 梦云有时候在家无事 , 拿出稿纸想写几个字 , 家里亲戚们看了就笑:“哟 , 你真的要当作家了?”丈夫便跟着他们一起笑 , 笑得更夸张 , 和众人站在一起 , 增加了他嘲笑梦云的底气 。3月末 , 儿子带回来一个好消息:交了几年的女友终于同意年底结婚了 。 两边谈了几次 , 女方家的最低条件是男方要拿出20万 , 用作在市里买房的首付 。梦云一家人默默垂首 。 儿子今年30岁 , 是村里年纪最大的单身汉 。 这些年 , 甘肃农村里结婚单是彩礼都得20多万 , 买房的钱另算 。 梦云觉得未来的亲家已经足够仁厚 , 思来想去 , 事不宜迟 , 她应该尽快回北京找工作 。丈夫劝她现在不要出门 , 说这些年她给家里攒了些钱 , 实在凑不够 , 去亲戚朋友家四处借借 。 梦云摇摇头 , 结婚是终身大事 , 钱不能一分一分地掰着算 , 不得给人家闺女买点首饰衣裳?疫情搞得各家现在都很难 , 谁愿意一下子拿出几万块钱借给穷亲戚呢?再说了 , 借来的终归是要还的 。丈夫叹了一口气 , 他坐在春天温热的阳光里 , 把假肢取下来 , 好让那已经磨破的腿透透气 , 稀疏的头发有气无力地搭在他的前额上 。 他年纪大了 , 即使有时候对梦云骂骂咧咧几句 , 也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气势汹汹 , 动作和声音里都透出衰颓的意味 。2“梦云”是她给自己取的笔名 , 她原来的名字有些土气 , 年轻的时候看琼瑶小说 , 里面的女主人公都有一个浪漫的名字 。 名字像一道护身符 , 得到这种名字的女人好像就拥有了幻想和爱情的特权 。 她羡慕这样的名字 , 想自己从小就爱做梦 , 就叫梦云吧 。她生来个子高 , 上初中时个子就长到了1米7 , 像田地里一株发育异常的稗草 , 不是女孩子该有的样子 。 村里人在背后议论她的高个儿、男人婆、丑 , 仿佛她得了某种怪病 , 或者她的个头是从哪里偷来的 。 她不愿意被人指指点点 , 走路的时候便故意弓着身子 , 似乎这样就能把自己往身体里塞回一截 。梦云有些文艺天赋 。 她爱看书 , 村里能捡到的故事书她看了个遍;她去村里看坝坝电影(露天电影) , 主题歌听一遍就学会了 , 看完回家时都是一路唱着主题歌回去的;她也喜欢跳舞 , 电视里有什么舞蹈动作 , 她只要抬抬腿、动动手就能学个八九分像 。 有时候她会一个人偷偷对着家里的镜子唱歌跳舞 , 只有在那时候 , 她才惊异地发现 , 自己挺着脖子的样子其实蛮漂亮 。结婚时 , 婆家给娘家送了1600元的彩礼 , 是当时全村最高的 。 既然人家花了钱 , 梦云觉得自己就是婆家的人了 。 她一天到晚在田地里挣不到什么钱 , 吃喝用度都要看丈夫脸色 , 哪怕来月经了 , 花5分钱买卫生纸都要丈夫心情好才能要到 , 她就愈发唯唯诺诺起来 。 丈夫说 , 你长得那么丑 , 又唱又跳的更难看 , 或者骂她 , 是不是想勾引哪家的男人?她便再也不去碰了 。有一年丈夫去镇上市集卖苹果 , 托人带口信回来说生意不错 , 怕是不够卖 , 让她赶紧再送两筐去 。 梦云不敢怠慢 , 装了七八十斤苹果 , 骑着大摩托朝镇上奔去 。 越着急就越要出事 , 村里的土路本来就坑洼不平 , 半道上忽然从田里钻出一个小孩 , 直直从她跟前跑过去 。 梦云心一慌 , 车头猛地往旁边拐 , 一下子连人带车倒在路边 , 好些苹果从筐里滚了出来 。 还好骑得不快 , 人车都没事 , 她翻个滚从地上爬起来 , 担心丈夫等急了 , 顾不得检查自己 , 装上苹果又继续朝前走 。到了镇上 , 丈夫便劈头盖脸地骂她怎么来得这样晚 。 她嗫嚅着说自己摔了一跤 , 丈夫像被点着的鞭炮一下子跳了起来:“那苹果摔坏了还怎么卖?败家的臭娘们儿 , 你怎么不去死?”旁人看不下去了 , 过来劝架:“别骂了 , 她脚上都流血了 。 ”梦云这才低头发现 , 右腿膝盖上磕破了皮 , 血沿着小腿流下来 , 把她的米色裤子沾红了 。回到家 , 丈夫还不解气 , 骂她不长眼睛 , 骂她在市集上给自己丢了人 , 骂摔坏的苹果没有卖出好价钱 , 丈夫好像恶魔附体 , 他的脸抽搐变形 , 眼睛露出灼热的凶光 。 最后恶魔在丈夫的身体里站起来 , 扬起手给了梦云一巴掌 。丈夫出够了气 , 躺在床上睡觉 。 梦云去做饭 , 等她觉得恶魔从丈夫身体里蛰伏下来 , 她再去小心翼翼地叫醒丈夫吃饭 。那些年梦云挨过很多次打 , 最凶的一次导致她右耳耳膜穿孔 , 现在她右耳听力都有点问题 , 在人多嘈杂的地方会突然听不见 。 梦云当时觉得丈夫挺过分的 , 但如果离开丈夫 , 她又能去哪里呢?而且村里那么多女人都挨打 , 经常被打得头破血流 , 相比之下 , 丈夫下手还算是轻的 , 何况 , 他还养活着这个家 , 总的来说 , 他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32007年 , 正当盛年的丈夫因车祸导致左腿截肢 , 从此无法再干重活 。梦云要跟着村里的人外出打工 , 丈夫起先不同意 , 他骂梦云“眼见他残废了 , 就要去城里找野男人” , 嘴里就一直没干净过 。 直到婆婆都听不下去了 , 问他“儿女上学的钱怎么办”、有没有“给我养老送终的棺材钱”时 , 丈夫才不说话了 。那几年 , 梦云辗转兰州、银川、呼和浩特等地 。 第一次到兰州的时候 , 她跟在老乡后头随着人流等红绿灯 , 汽车从她跟前开过去 , 她站在斑马线上两腿发抖 , 路上的一切都让她心惊胆战 。 但她知道自己没有退路 , 天已经塌下来了 , 只有自己个子高顶着 。在黄河边上的一个啤酒厂 , 一箱啤酒曾从货架上掉下来砸到她脚上 , 右脚大拇指盖整个被砸掉了 , 鲜血往外涌 , 她也不敢声张 。 她不知道有工伤这回事 , 看医生要花钱 , 第二天要是不能来继续上班就不是全勤了 , 又要扣好多工资 , 想到这儿 , 她心里比脚趾还疼 , 就用卫生纸包了包 , 继续上班 。慢慢地 , 她对疼痛的忍耐力越来越高 。 手上的茧子越来越厚 , 也就不觉得拎的东西有多沉重 , 有个头疼脑热也从来不去医院 , 最后都能化险为夷地“捱过去” 。 她觉得身体就像弹簧 , 不断地用疼痛加压 , 才能激发它克服疼痛的能力 。从那时候起 , 梦云开始梦见一个男人 , 他面容模糊 , 但她相信他一定很帅 , 眉目的样子总是看不清 , 却能看见他眼角带着一抹温柔的笑 , 像黄昏时的余霞那样温暖动人 。 有时候是一个月一次 , 有时候是两三个月一次 , 她就像等待神秘的连续剧一样 , 等着他毫无规律的来临 , 有时候她还会在梦里问他 , 你怎么好久都没来了呢?他也不说话 , 就是笑笑 。两人离得最近的一次 , 是梦云坐在公交车上 , 一阵狂风袭来 , 似乎要把她卷上天 , 他笑着朝她走过来 , 伸出手帮她关窗户 。 她呆呆地坐在公交车上 , 在他的手臂下感觉到了他的体温 , 她意识到了自己正在做梦 , 便对那个人说 , 我们一起回到现实中去吧 。 那人却不回答她 , 公交车开进了一座森林 , 她醒来后 , 后面的记忆被森林淹没了 。丈夫的脾气越来越差 , 每次她回家 , 丈夫都要厉声质问她“是不是在外面和别的男人好了” 。 看到她委屈流泪 , 他又会过来给她捏肩膀、捏背 。 其实她知道 , 丈夫出事后内心郁闷憋屈 , 像一头失去牙齿、被关在笼子里的猛兽 , 既想继续保持往日的威严 , 心底又害怕自己会被抛弃 , 才会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试探她的反应 。 有一次 , 丈夫抽着烟闷闷地对梦云说 , 他在中央电视台上看到一个人把别人打耳膜穿孔了 , 判了3年刑 , 他才知道这是犯法的 , 以前不应该打她 。 她听到这话就放声大哭起来 。2017年 , 梦云托熟人给丈夫找了份在县城看大门的活儿 , 自己则坐了18个小时的大巴来到北京 , 成为一名住家保姆 。来北京的目的只有一个:这里的工资是原来的两到三倍 。 那一年 , 她已经49岁了 。4原来的中介还没复工 , 但家政群里三天两头会弹出“北京阿姨急招”的消息 。 一个姐妹向梦云推荐了另一家在东边的中介 , 她想 , 疫情之后好多阿姨在外地没法回京 , 需求量肯定大 , 自己又有经验 , 天无绝人之路 , 心一横 , 拖着箱子就从家里走了 。她先去之前的雇主家收拾东西 。 那个小男孩开门一看见她 , 就扑到她身上:“阿姨 , 你怎么这么久都不来看我呀?”孩子从出生起 , 她一直带到3岁 , 有感情了 。收拾完留在家里的东西 , 孩子看她又要走 , 迷惑不解地问:“你要到哪里去呀?”她忍住眼泪 , 笑着跟孩子说:“阿姨要出去工作 。 ”孩子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 , 睫毛扑扑的:“那你工作完了就回来哦 。 ”她冲他点了点头 。做家政的姐妹们经常劝她 , 不要对雇主的孩子全身心投入 , 孩子太黏阿姨了 , 以后离开的时候就揪心 。 但她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喜欢这个孩子 。雇主夫妻是一对小年轻 , 言语之间对她很客气 , 她就更觉得自己该知恩图报 。 白天夫妻俩都去上班了 , 就她和孩子在家 。 孩子看小猪佩奇她也看 , 孩子满地滚她也陪他一起滚 。 她觉得带孩子就像在农村的时候种庄稼 , 看着一棵苗子渐渐长高长大 , 动作、样子、眼神也跟着变化 , 每当这种变化悄然发生 , 怎么能忍住欢欣鼓舞呢?她的普通话不太标准 , 有时候就让孩子摊开识字绘本教她念 , 这时她觉得自己也变回了孩子 。正是在这个孩子身上 , 她才明白原来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如此精心的呵护 , 要一点一滴地给他们自信 , 想想自己的一双儿女 , 她都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把他们拉扯大的了 , 小时候满地散养 , 就知道给饭吃给衣穿 , 完全不知道什么“精神成长” 。 等到他们懂事 , 自己又漂在外面到处打工 , 几乎没怎么关心过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 女儿性格活泼一点 , 儿子就内向很多 , 人前总是笨嘴拙舌 。 她有时候会突发奇想 , 如果时光倒流 , 她一定会按照现在带雇主孩子的方法来带自己的孩子 。下电梯的时候 , 她心里有些愧疚 , 刚刚自己说要回来 , 其实是骗了孩子 。 她一向觉得 , 孩子虽然小 , 但实际上特别聪明 , 他们能明白 , 也能记得所有事情 , 不能骗他们 。那天晚上梦云就梦见了雇主的孩子 , 抱在自己手里 , 孩子忽然哭着对她说 , 肚子痛痛 。 她急得四处找药 , 抓起一个棕色的小瓶子 , 回头一看 , 那孩子却变成了自己儿子小时候的样子 , 再仔细一看那个瓶子却是空的 。梦云吓醒了 , 发现自己正和十多个人一起 , 横七竖八地躺在地铺上 。 她像一片落叶在湍急的水流中旋转 , 一下子时空倒置 , 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过了好一会儿 , 她才想起自己几个小时前拖着行李四处找新中介的情景:当时她迷了路 , 手机又没电了 , 走在天桥上 , 四面八方的车水马龙向她涌来又急忙散去 , 自己就像一只随时会被洪水淹没的蚂蚁 。 最后 , 她定了定神 , 凭着记忆里姐妹告诉她的那几个字 , 一边走一边问路 , 终于在晚上10点过找到了地方 。 新中介把十多个她这样的家政女工临时安置在这间房子 。月光透过窗帘 , 几个小时前发生的事恍如隔世 。 她睡不着了 , 忽然想起年前和公益组织“鸿雁之家”的姐妹们在一起写歌 , 有一段歌词是这样的:我是鸿雁妈妈 ,我有两个娃娃;一个叫我阿姨 ,一个十月怀胎 。当时大家要录这首歌 , 她专门录了雇主的孩子叫她“阿姨”的声音 , 请公益组织的人剪进姐妹们的合唱里 。 那个孩子真的很聪明 , 叫“阿姨”的时候声音清清脆脆的 , 像一粒透明的雨滴落下来 。此刻她又听见那个声音了 , 阿姨 , 阿姨 , 在她太阳穴上突突地跳 。5疫情的影响远远超乎预料 。不少原来在酒店做活儿的阿姨们没了工作 , 也纷纷转向家政 。 雇主的需求量却在萎缩 , 写着“急招”的招聘信息 , 一问过去都要先交好几千的培训费 。 姐妹们都陆续遇到了这种情况 , 大家在群里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些人就是想骗咱们农村人的钱 。 ”“知道咱们着急找工作趁火打劫” 。梦云在新中介的住处睡了半个月地铺也没遇到合适的活儿 。 一个姐妹问她 , 愿不愿意先去一家养老院干着 。 工资只有先前做家政的一半 , 但有总比没有好 , 与其在中介这里干等 , 只出不进 , 有点钱挣总是好的 , 她来不及多想便跟着去了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 北京便显得格外坚硬冰冷 。 梦云对北京的感情是一直在变化:当她在这里攒了一笔积蓄时 , 她后悔自己没有早来;当她受了委屈、遭人白眼时 , 她又觉得过几年应该离开;但每当她回忆自己第一次去皮村时的情景 , 她都对北京充满温情 , 说自己就像一只在黑暗隧洞里误打误撞的蜜蜂 , 偶然找到一个光口 , 飞过去 , 发现了一片花海 。那时她刚到北京 , 每周六是休息日 , 可以离开雇主家到处去转转 。 然而真的走出家门后 , 她却一片茫然 , 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 北京太大了 , 没有一处是属于她的 。有一天 , 梦云拿出手机搜索“北京、打工、群体” , 意外看到了皮村的“工友之家” 。 她在上面读了好些文章 , 都是外出打工的工友写的 , 粗粝却真诚的文字就像从她自己心里流出来的一样 。 她决定去看看 , 周六便坐了两个多小时车 , 地铁倒公交 , 从西四环跑到东五环外 , 来到一个破破烂烂的城中村 。第一眼望去 , 她的心沉到了谷底:这是什么鬼地方?北京竟然还有这么破的地方 , 连老家县城都不如 。 但她想 , 花了这么长时间来一趟 , 进去瞧瞧吧 。 意外地 , 她在工友之家的院落里发现了工人图书馆、博物馆和剧场 , 一个志愿者小年轻告诉她 , 晚上7点这里会有文学小组的讲座 , “免费开放” 。 整整一个下午怎么度过呢?小年轻给她递了一本《活着》:“看看这个吧 。 ”那天晚上 , 她的眼睛因为看《活着》而有些不自然地红 , 她也把公众号上很多熟悉的名字和真人对上了 。 一群常年在外打工、衣着朴素甚至破旧的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 , 却依然被一种叫做“文学”的东西发出的幽微光芒照亮 , 那是一点火星被一簇火光包围的感觉 。 梦云觉得这里的人都懂自己 , 知道自己心里的酸甜苦辣 。 她走过去 , 主动跟一位经常在公号上发表文章的打工大哥说话:“我在公众号上看过你写的文章 , 写得特别好 。 ”那是她第一次在外面主动跟男人打招呼 。讲座放在周六晚上 , 是因为一些工友周末也要上班 , 开始太早了大家赶不过来 。 有一天晚上 , 一位北大的老师来讲 , 大家兴致高昂 , 结束后已经快10点了 。 老师知道梦云的雇主在海淀 , 说自己也回海淀 , 大姐你就搭我的车吧 。 梦云急忙摆手 , 在雇主家她一向时刻提醒自己不要逾越分寸 , 北大的老师 , 那应该级别跟县长差不多了吧 , 想想老家那些开车的有钱人 , 鼻孔都是朝天的 , 自己怎么能让老师开车送自己呢?老师笑了笑:“别客气 , 咱们都是朋友了 。 ”就这一句话 , 那天晚上她久久未能成眠 。 迷迷糊糊睡着了 , 她梦见自己在坐飞机 , 窗外霞光中升起一座辉煌的楼宇 , 她满心惊喜:这就是海市蜃楼 , 传说中的蓬莱仙境啊!光顾着高兴 , 忽然周围一切都消失了 , 座位、机舱统统一下子烟消云散 , 她在一片黑暗的大风中往下坠落 , 一边落一边想 , 这是要落到哪里去呢?再往下一看 , 这不就是我们村吗?那覆满尘土的房屋 , 那哆哆嗦嗦、早已无人供奉的小庙 。 继续下坠 , 越过陆地 , 下面就是万丈深渊了 , 更可怕的还有老鼠和蛇 , 她已经看见了它们尖利的眼睛……她吓得从梦里惊醒过来 。春节前夕 , 文学小组要颁发“劳动者文学奖” , 梦云因为个子高挑 , 形象姣好 , 说话又大方 , 便被大家推选当主持人 。 当大家的目光都打到她身上时 , 她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 , 自己真的是美丽的 。 她和家政姐妹们参加“鸿雁之家”文艺演出的事迹还被采访人员搬上了央视新闻 。 在生命的前50年 , 她的美丽被家乡的偏僻、丈夫的打骂、生活的窘迫死死压着 , 日益凋落苍老 , 只剩下最后一抹痕迹 。就在此时 , 北京承认了她的美丽 。6丈夫再不会对她动手了 , 他知道家暴也是犯法的 , 何况梦云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 , 腰板自然硬朗了起来 。丈夫在县城看大门 , 像一台默默无言的摄像仪器 , 记录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 有一次他慨然对梦云说:“城里的女人 , 可真不得了 , 个个都要穿名牌用名牌 , 女人买不起就破口大骂 , 把男人骂得跟丧家犬似的 。 ”他停顿了一会儿 , 又自言自语似的:“我就想啊 , 我媳妇这么漂亮 , 这么能干 , 我以前还打骂她 , 我可真不是个东西 。 ”但脾气一上来 , 他还是会把自己那些掏心窝的话抛在一边 , 忍不住冲梦云破口大骂 。 梦云却不再是以前那个唯唯诺诺的胆小鬼了 , 她的神经变得强壮 , 她已经完全自信 , 即使离开丈夫也能养活自己 , 心里便对他不再畏惧 , 反倒是丈夫害怕她会离婚 。 有了这样的底气 , 丈夫咒骂的时候她就像没听见 , 一边干着家务活儿 , 一边心里还唱着歌 , 而她越是表现得满不在乎 , 丈夫就越生气 , 这甚至会让她产生逗逗他的想法 。她也学会了反驳 。 丈夫说她举止“不像个大人” , 50多岁的人了 , 脑子里还成天想些不切实际的事 。 她就说:“不像大人也没什么不好 。 像小孩哪里不好?坏事都是大人干的 , 你看那些贪官污吏、强奸幼女 , 哪一个不是大人干的?”丈夫说不过她 , 只得恨恨地嘀咕一句:“神经病 。 ”然而北京在给予梦云信心和风光的同时 , 又会在她最跃跃欲试的时候给她当头一棒 。 在她当过主持人后 , 身边的人都纷纷对她说 , 凭她的条件 , 她可以去当老年模特 。 说的人多了 , 她便悄悄动了心 。 也是一个周六 , 她查到昌平一家公司要举行老年模特大赛初选 , 便交了几百块报名费去参加 。 平时 , 她连一个水果也舍不得买给自己吃 , 那几百块是这几年来她花在自己身上最大的一笔开销 。现场有不少和她年纪相仿的中老年妇女 , 不少人看起来条件并没有她好 。 但当她们打开自己手上的皮箱 , 从中拿出款式精致的旗袍、林林总总的化妆用品、7厘米的细高跟鞋 , 立刻便有一道光环从她们身上散发出来 。 一道无形的高墙在梦云和这些拿退休金的老太太之间竖起 , 她只是穿着5年前女儿给她买的一条白色绣花纱裙——她最拿得出手的一套衣服 , 当主持人的时候也穿的这套——脚上蹬着一双发旧的平底帆布鞋 , 但她还是硬着头皮 , 在评委异样的目光中 , 到T台上走了一遭 。在回去的地铁上 , 梦云挤在人群中间想 , 从事任何一项文艺活动都需要长期的金钱和精力投入 , 对她这种年纪和背景的人来说 , 这已经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了 。 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实 , 但她必须要承认啊 。 如果想写出好文章 , 就需要长期的阅读和练笔;如果想跳舞或成为模特 , 专业的配备和练习必不可少 。 或许作为一个阿姨 , 她能写文章、唱歌跳舞、当主持人便能够让一些人惊奇 , 但这些惊奇和赞许中都包含着别有意味的宽容 , 因为她是阿姨才有的宽容 。那年回家过完春节 , 走的时候 , 丈夫把她送到了西安 。 离火车开车还有大半天 , 丈夫说:“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去哪里玩过 , 去看看古城楼吧 。 ”买票的时候 , 丈夫听说两个人门票要100多 , 手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丈夫戴着假肢 , 走路不快 , 两个人在城楼上慢吞吞地挪着 , 不像来旅游 , 倒像是长途跋涉迷路了 。 丈夫说:“来西安好多次了 , 这还是第一次上城楼 。 ”梦云说:“我也知道 , 你花这么多钱 , 就是为了让我有个念想 。 ”丈夫又说:“你在外面 , 受苦受累了 。 ”梦云想 , 从这城楼修建起到现在 , 不知多少人生生死死 , 但自己现在就和丈夫在一起 , 这就是冥冥中的“缘分”吧 。 北京曾让自己见到希望和荣光 , 但那终究不属于自己;不管丈夫以前对自己怎样 , 他却是实实在在陪伴在自己身边的 , 他们这辈子已经裹在一起了 。从城楼上下来 , 他们便道别了 。 一个去火车站 , 一个回家 。 梦云回过头去看 , 丈夫慢慢挪着腿混入人来人往之中 , 一股热流在她心里涌动 。 她坐上火车 , 写了几句诗:看着你渐渐远去的背影稍微带着一点儿蹒跚泪水忍不住流下我的脸颊西安的古城楼真长啊长得我俩半天都走不到头……自己写的这些比不上专业作家 , 但梦云依然很珍视 。 她发给丈夫 , 丈夫破天荒地没有讽刺她“幼稚”“写些没用的东西” , 而是说“写得很好” 。7养老院里的老人大都瘫痪在床 , 无法自理 。 有的护理人员为了省事 , 能喂食的老人也打鼻饲 , 一针猛地打进去 , 扎得梦云的心也跟着疼 。 她受不了 , 轮到自己照料的老人 , 就一口一口地慢慢喂 , 喂一下擦一下嘴巴 。 别人都笑她给自己找事 , 劝过她几次 , 她不改 , 大家也就各行其是 。一种压抑的安静统摄着这里的空气 , 躺在床上的老人偶尔发出呻吟和叹息 , 护理人员也常常陷入沉默 , 整座养老院像一部慢慢流逝的黑白默片 。梦云想到自己的老家 , 年轻一代都想尽办法去城市里生活了 , 留下来的长辈接连去世 , 农村也陷入类似的寂静中 。 在养老院的日子 , 她常常做噩梦 , 自己回到了村里 , 远远一望 , 怎么人人都披麻戴孝 , 好像在办丧事呢?她猛然想起这几年相继故去的几个亲人 , 心里一阵怆痛 。 这时 , 死人却从棺材里跳出来 , 追问她要去哪里 , 她捂着惊恐的心口说要去北京 , 那站起来的死人就叹口气 , 北京太远了 , 太大了!说罢 , 又倒回棺材里 。在养老院做了大半个月 , 中介那边有消息了 。 新雇主家里面积比前雇主更大 , 人也更多 , 这意味着她会比以前更辛苦 。 但梦云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去做阿姨 。 工资更高当然是最重要的原因 , 她也确实没法长期忍受养老院的氛围 , 在这里 , 她觉得自己的生命力也分分秒秒在流失 。离开养老院那天 , 她走到自己照顾的那个瘫痪老人床边 , 跟她道别 。 老人说不出话来 , 只有手指还能动动 , 她就望着梦云 , 拉了拉她的衣角 。 梦云一下子鼻子酸了 , 她心里感到愧疚 , 每次离开家时 , 她也会有相似的愧疚:她自己跑去繁华大都市 , 把衰败留在了身后 。梦云现在更忙了 。 她早上6点起床做早饭 , 一直忙到晚上11点 , 除了雇主夫妇 , 爷爷奶奶再交代点活儿 , 一刻没有闲暇的时候 。 她白天几乎没有时间看手机 , 更别提写点文章和诗了 。 但她依然从心里感激雇主给了她这份工作 。何况 , 忙碌和辛苦其实也有好处 。 梦云暗地里也在观察真正的“北京人”:他们对疼痛的忍受度很低 , 有一点小病小痛就要上医院;他们更容易焦虑不安;他们的脑力过度发达而身体易于萎缩 。 城里人60多岁就退休 , 干不了什么重活儿了 , 而对她家乡的人来说 , “退休”是一个太遥不可及的词 , 她的母亲和婆婆80多岁了还在地里干活 , 或许只有当死亡来临时才能退休 。有时候她会感到不公平 , 但转念一想 , 农村人吃了太多苦 , 神经就粗壮些 , 生命力也更顽强 , 这也是另外一种公平吧 。 想到这里她便感到释然 , 心里的苦会泛出一丝甜 , 自己没有实现的梦也可以放下了 。 她甚至有些想念家乡的生活 , 到她干不动的那天 , 她会回家去 , 把老师们送她的书读完 。疫情好转后 , 有一天晚上梦云抱着孩子在闹市街头散步 。 街上车水马龙 , 流光溢彩 , 她恍惚觉得自己走在梦中某个似曾相识的场景 。 自己大半辈子吃了不少苦 , 但总归受到了眷顾 。 身边的人也有她所不知道的苦吧 。 人们习惯看到他人的幸福 , 羡慕别处的生活 , 而每个人的辛苦都只有自己去承受和接纳 。 她突发奇想——迎面走来的某个人或许会误以为她是孩子的亲生外婆或奶奶 , 他或许会在心底陡然羡慕自己:看啊 , 她是一个幸福的女人 。编辑:许智博题图:VCG
推荐阅读
- 陈勇军|悲恸!成都跳河救人的哥已遭遇不幸……
- 小罗|光天化日“蒙面大盗”把“加菲猫”给偷了
- 中国最早的中外合资汽车企业是?
- 周某|一模一样的行李被拿错了,茫茫人海中,能物归原主吗?
- 被领导长期骚扰“圈禁”3个月 中行回应了
- 老北京“吃,得应时当令”
- 空包|曝光!巨大黑幕
- 燕鸣|必须给“局处长走流程”点个赞
- 西直门立交桥|北京“最复杂”的立交桥,曾投资2.1亿建造,路况能让老司机崩溃
- 新风桥|三亚市消防救援支队救下一名跳桥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