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这里,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欧文·亚隆这样看待自己的盛誉,他写道:“最近几年,有些时候,我在开始演讲时会感激听众规模如此庞大,然后说道:‘我意识到,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听众数量越来越多。当然,这是对我极大的肯定。但如果我带上存在主义的眼镜,我就看到黑暗的一面,我在想,人们为什么这么着急来看我呢?’”
在读《弗兰克尔自传》时,我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事情,明白了弗兰克尔为什么对欧文·亚隆的眼镜感兴趣了。这一点,我觉得欧文·亚隆未必知道。
弗兰克尔在书中说:“镜框设计方面我可以算得上专家,由于我这方面造诣颇深,一个全球数一数二的镜框加工企业邀请我做顾问,这家企业会在它的产品大批量生产之前把产品样图给我,征求我的意见。”
好在,他在见面时,没有向欧文·亚隆炫耀这方面的能力。
尽管不喜欢弗兰克尔的自恋,但在阅读中,我心中的不舒服慢慢消失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又恢复了不少。因为,我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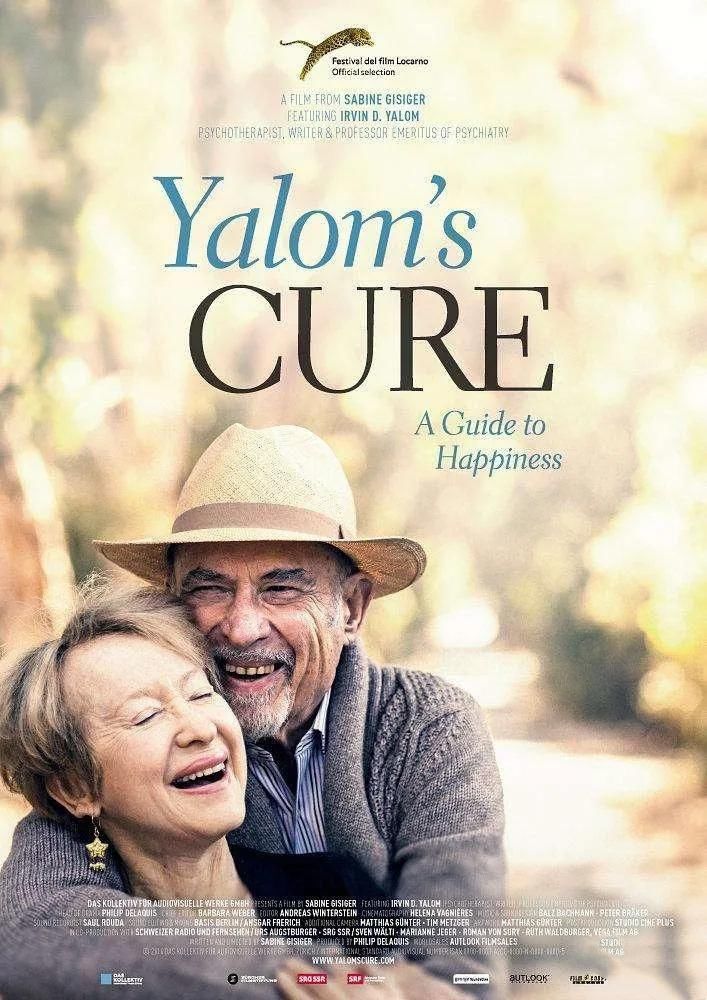
文章插图
欧文·亚隆与妻子玛丽莲03
人性的光辉
我看到的东西是,在纳粹集中营这样极其残酷的环境里,弗兰克尔散发出了人性的尊严与光辉。
他在自传中讲到这样一件事情。他被从泰雷津集中营转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新婚9个月的妻子蒂莉本来已获得免遣庇护,但她申请了自愿随迁。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男女要分开关押。在分别的那一刻,他对她说:“蒂莉,如论如何要活下去——明白吗,不惜一切代价!”
他写道:“我的语气是那么恳切,我想让她真正明白我要说的是什么。我想说的是,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需要她用身体去换取活下去的机会,希望她不要因为我而有所顾忌。这几乎算是我给她的一个提前赦免,我希望她不要因为顾忌我而走向死亡。”
作为集中营的幸存者,弗兰克尔坚定地反对“集体罪责”。他在集中营里得到过善良的纳粹分子的帮助,他不认为纳粹集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罪。
1946年,他还让一个同事躲在家里,那个人曾经获得某个希特勒青年荣誉奖章,当时国家警察正在搜捕他。如果他接受审判,而审判结果要么是无罪释放,要么是死刑。
有一次,他在法国占领区演讲时,还当着法军指挥官——一名将军的面,反对“集体罪责”的说法。第二天,一位大学教授过来找他,他曾经是一名党卫队军官。他含着泪问他,为什么他竟然这么有勇气,公开反对这样一种笼统的群体性指控。
“您不可以,”他在书中写道,“您如果这样说可能是在为自己辩护。可我是进过集中营的,是编号119104的囚犯,所以我可以这么做,因此我也就必须这么做。我没有您这样的嫌疑,这同时也意味着一种责任。”
欧文·亚隆也看到更多的东西。他读了斯坦福的同事和朋友,汉斯·斯坦纳(Hans Steiner)教授,写的20世纪60年代在维也纳医学院当学生时候的自传性描述,从而获得了看待弗兰克尔的另外一个视角。
作为一名学生,汉斯对弗兰克尔的印象极为正面,他将他描述为一位杰出的老师,他的创造性方法相比于维也纳其他精神病学教员的刻板,简直是一股清流。
有一次,欧文·亚隆和弗兰克尔一起都在一个大型的心理治疗会议上发言,他参加了他关于《活出生命的意义》的讲座。一如既往,他令听众着迷,并赢得了雷鸣般的喝彩。
所以,他赢得听众雷鸣般的喝彩并不是夸大。
欧文·亚隆还发现,当他写《存在主义心理治疗》(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的时候,又仔细地温习了弗兰克尔的著作,“越发意识到,他对我们这一领域的创新性和基础性贡献所具有的重要性。”
这些,都让我心中的那个缺口慢慢填满,弗兰克尔在我心目中,又重新成为一个圆满的形象,只是光辉少了一些。

推荐阅读
- 苏轼: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遇见的人,就是你的人生格局!
- 明天下午,《遇见淼城》正式发售!
- 在浙南产业集聚区:遇见非遗之美!
- 当设计思维遇见产品设计:如何培养产品的微观体感能力
- 吴柜贞|诚信,会让你在困难中遇见贵人
- 诗歌《遇见九陇山根据地》
- 溥仪|溥仪晚年买票重回故宫,途中遇见一位白发老人,愣了几秒脸色大变
- 《遇见馆藏·太空季》邀请航天文创(CASCI),共赴太空探索之旅
- 徐志摩前妻“感谢你,让我离开,让我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 秦朝|改变秦国的两个女人,当华阳夫人遇见芈月,她们俩是什么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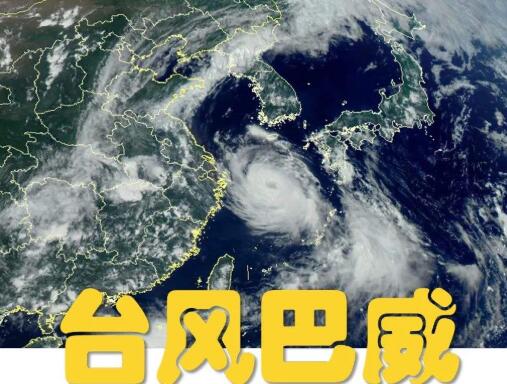






![[芬姨的故事会]国乒队在澳门进行混上循环对抗赛!王楚钦和孙颖莎排名第二!](https://imgcdn.toutiaoyule.com/20200418/20200418154109944806a_t.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