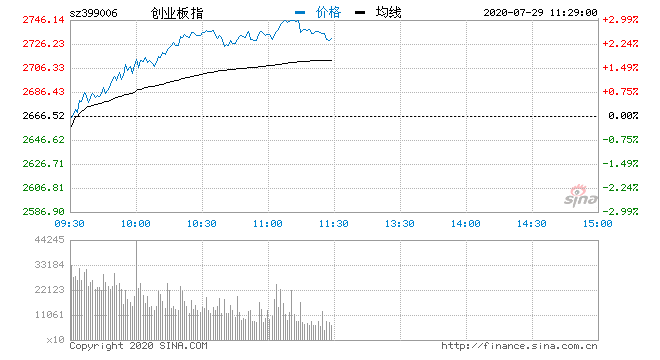гҖҺж–°еҹәе»әгҖҸ“ж–°еҹәе»ә”еә”иҜҘжҖҺд№Ҳе»ә( дәҢ )
еҜ№еҮҜжҒ©ж–Ҝзҡ„иҝҷдёӘе‘ҪйўҳпјҢжҲ‘жӣҫжҖқиҖғиҝҮеҫҲд№…пјҢеҗҺжқҘз»ҲдәҺжғіжҳҺзҷҪдәҶе…¶дёӯзҡ„йҒ“зҗҶ гҖӮд»Һж №жң¬дёҠиҜҙпјҢеҮҜжҒ©ж–ҜжҳҜдёҖдёӘеёӮеңәз»ҸжөҺзҡ„ж”ҜжҢҒиҖ…пјҢд»–еҪ“然зҹҘйҒ“йҮҮз”Ёе…¬е…ұе·ҘзЁӢжқҘеҲәжҝҖз»ҸжөҺеҸҜиғҪйҖ жҲҗзҡ„еҗҺжӮЈ гҖӮеӣ жӯӨпјҢд»–еҸӘжҳҜжҠҠе…¬е…ұе·ҘзЁӢеҪ“жҲҗеҢ»жІ»иҗ§жқЎзҡ„вҖңиҚҜвҖқпјҢиҖҢдёҚжҳҜе°Ҷе…¶и§ҶдёәеёӮеңәз»ҸжөҺзҡ„жӣҝд»Ј гҖӮ既然жҳҜдёҖеүӮвҖңиҚҜвҖқпјҢйӮЈе°ұиҰҒеңЁжғіеҗғж—¶еҸҜд»ҘеҸҠж—¶еҗғеҲ°пјҢеҗғеҗҺеҸҲдёҚдјҡдә§з”ҹдҫқиө– гҖӮиҖҢеҰӮжһңиҝҷдёӘвҖңиҚҜвҖқжңүе…¶д»–д»·еҖјпјҢиҝҷдёӨдёӘзӣ®зҡ„е°ұдёҚиғҪиҫҫеҲ°пјҡдёҖж–№йқўпјҢеңЁи®Ёи®әиҝҷйЎ№е·ҘзЁӢзҡ„еҸҜиЎҢжҖ§ж—¶пјҢдәә们еҸҜиғҪдјҡжӣҙеӨҡең°е…іжіЁе·ҘзЁӢжң¬иә«зҡ„д»·еҖјпјҢиҖҢеҝҪз•Ҙе…¶еҜ№з»ҸжөҺзҡ„еҲәжҝҖдҪңз”ЁпјҢд»ҺиҖҢеҸҜиғҪеҪұе“Қе·ҘзЁӢзҡ„йҖҡиҝҮпјӣеҸҰдёҖж–№йқўпјҢеҪ“еҲәжҝҖж”ҝзӯ–е·Із»ҸиҫҫеҲ°зӣ®зҡ„пјҢйңҖиҰҒйҖҖеҮәж—¶пјҢдёҖдәӣеҲ©зӣҠйӣҶеӣўеҸҜиғҪдјҡд»Ҙе·ҘзЁӢжң¬иә«д»Қжңүд»·еҖјдёәеҗҚйҳ»зўҚеҲәжҝҖж”ҝзӯ–зҡ„йҖҖеҮә гҖӮеҹәдәҺд»ҘдёҠдёӨдёӘеӣ зҙ пјҢд»…д»ҺеҲәжҝҖз»ҸжөҺзҡ„и§’еәҰзңӢпјҢвҖңжңүз”ЁвҖқзҡ„е·ҘзЁӢе…¶е®һ并дёҚеҰӮвҖңжөӘиҙ№жҖ§вҖқзҡ„е·ҘзЁӢжңүз”ЁпјҢд№ҹдёҚеҰӮвҖңжөӘиҙ№жҖ§вҖқзҡ„е·ҘзЁӢйӮЈж ·еҸҜд»Ҙ收ж”ҫиҮӘеҰӮ гҖӮжүҖи°“вҖңж— з”Ёиғңжңүз”ЁвҖқпјҢз”ЁжқҘеҪўе®№иҝҷдёҖжҖқи·ҜеҸҜиғҪжҳҜеҶҚеҗҲйҖӮдёҚиҝҮдәҶ гҖӮ
йҖҡиҝҮд»ҘдёҠи®Ёи®әпјҢжҲ‘们зҹҘйҒ“пјҢд»ҺжҖ§иҙЁдёҠзңӢпјҢеҹәзЎҖи®ҫж–Ҫ并дёҚеӨӘйҖӮеҗҲжқҘдҪңдёәз»ҸжөҺеҲәжҝҖзҡ„жүӢж®өвҖ”вҖ”иҮіе°‘д»ҺеҮҜжҒ©ж–Ҝзҡ„еҺҹж„ҸжқҘзңӢпјҢжғ…еҶөжҳҜиҝҷж ·зҡ„ гҖӮ既然еҰӮжӯӨпјҢйӮЈд№ҲиҝӣиЎҢеҹәзЎҖи®ҫж–ҪжҠ•иө„зҡ„зҗҶи®әеҹәзЎҖ究з«ҹжқҘиҮӘе“Әе„ҝе‘ўпјҹйўҮдёәд»ӨдәәзҺ©е‘ізҡ„жҳҜпјҢе®ғ并йқһжқҘиҮӘдәҺд»»дҪ•дёҖдҪҚеҮҜжҒ©ж–Ҝдё»д№үиҖ…пјҢиҖҢжҳҜжқҘиҮӘдәҺдёҖдҪҚеҘҘең°еҲ©еӯҰжҙҫзҡ„з»ҸжөҺеӯҰ家вҖ”вҖ”дҝқзҪ—В·зҪ—жЈ®ж–ҜеқҰ-зҪ—дё№пјҲPaulRosenstein-Rodanпјү гҖӮ
еңЁеӯҰжңҜз”ҹж¶Ҝзҡ„ж—©жңҹпјҢзҪ—жЈ®ж–ҜеқҰ-зҪ—дё№зҡ„з ”з©¶дё»иҰҒйӣҶдёӯеңЁдёҖдәӣеҘҘжҙҫз»ҸжөҺеӯҰзҡ„з»Ҹе…ёе‘ҪйўҳпјҢдҫӢеҰӮвҖңиҫ№йҷ…ж•Ҳз”ЁвҖқгҖҒвҖңж—¶й—ҙд»·еҖјвҖқзӯүпјҢдҪҶи®©е…¶й—»еҗҚдәҺз»ҸжөҺеӯҰз•Ңзҡ„пјҢеҚҙжҳҜе…¶еңЁеҸ‘еұ•з»ҸжөҺеӯҰйўҶеҹҹдҪңеҮәзҡ„иҙЎзҢ® гҖӮеңЁ1943е№ҙеҮәзүҲзҡ„и‘—дҪңгҖҠдёң欧е’ҢдёңеҚ—欧еӣҪ家е·ҘдёҡеҢ–зҡ„иӢҘе№Ій—®йўҳгҖӢдёӯпјҢд»–жҸҗеҮәдәҶи‘—еҗҚзҡ„вҖңеӨ§жҺЁиҝӣвҖқзҗҶи®әпјҲTheTheoryoftheBig-Pushпјү гҖӮиҝҷдёҖзҗҶи®әи®ӨдёәпјҢе°ұеғҸйЈһжңәиө·йЈһйңҖиҰҒиҺ·еҫ—дёҖе®ҡзҡ„еҲқе§ӢйҖҹеәҰдёҖж ·пјҢдёҖеӣҪзҡ„з»ҸжөҺиҰҒе®һзҺ°еҸ‘еұ•пјҢеҝ…йЎ»иҰҒз»ҸеҺҶиҝҮдёҖдёӘе·ҘдёҡеҢ–иҝҮзЁӢ гҖӮ
еңЁе·ҘдёҡеҢ–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иө„жң¬зҡ„еҪўжҲҗжҳҜдёҚеҸҜжҲ–зјәзҡ„ гҖӮзҪ—жЈ®ж–ҜеқҰ-зҪ—дё№е°Ҷиө„жң¬еҲҶдёәдәҶдёӨзұ»пјҢвҖңзӨҫдјҡеҲҶж‘Ҡиө„жң¬вҖқ(SocialOverпјҚheadCapital)е’ҢвҖңз§Ғдәәиө„жң¬вҖқ(PrivateCapital) гҖӮе…¶дёӯпјҢвҖңзӨҫдјҡеҲҶж‘Ҡиө„жң¬вҖқеӨ§иҮҙдёҠе°ұзӯүдәҺжҲ‘们жүҖиҜҙзҡ„еҹәзЎҖи®ҫж–Ҫ гҖӮд»ҺеҠҹиғҪдёҠзңӢпјҢиҝҷдёӨзұ»иө„жң¬жңүеҫҲеӨ§зҡ„е·®ејӮпјҢз§Ғдәәиө„жң¬еҸҜд»ҘиҺ·еҫ—зӣҙжҺҘзҡ„收е…ҘпјҢиҖҢзӨҫдјҡеҲҶж‘Ҡиө„жң¬зҡ„дҪңз”ЁеҲҷдё»иҰҒдҪ“зҺ°еңЁе…¶еӨ–йғЁжҖ§дёҠ гҖӮдёҖиҲ¬жқҘзңӢпјҢзӨҫдјҡеҲҶж‘Ҡиө„жң¬жң¬иә«зҡ„зӣҙжҺҘеӣһжҠҘжңӘеҝ…иғҪжҠөж¶Ҳе…¶жҲҗжң¬пјҢдҪҶе®ғеҚҙдјҡеҜ№жҹҗдәӣдә§дёҡзҡ„з»ҸжөҺеӣһжҠҘдә§з”ҹеҫҲеӨ§зҡ„дҝғиҝӣдҪңз”ЁпјҢеӣ жӯӨд»Һж•ҙдҪ“зҡ„з»ҸжөҺеӣһжҠҘзңӢпјҢеҹәзЎҖи®ҫж–Ҫе°ҶеҸҜиғҪдә§з”ҹеҸҜи§Ӯзҡ„жӯЈж”¶зӣҠ гҖӮеҹәдәҺд»ҘдёҠеҺҹеӣ пјҢзҪ—жЈ®ж–ҜеқҰ-зҪ—дё№и®ӨдёәпјҢеңЁзқҖжүӢзү№е®ҡзҡ„дә§дёҡеҸ‘еұ•д№ӢеүҚпјҢж”ҝеәңеә”еҪ“йҰ–е…ҲеҜ№дёҺиҝҷдәӣдә§дёҡзӣёе…ізҡ„еҹәзЎҖи®ҫж–ҪиҝӣиЎҢе»әи®ҫ гҖӮиҝҷж ·пјҢеңЁеҗҺз»ӯзҡ„еҸ‘еұ•дёӯпјҢиҝҷдәӣдә§дёҡе°ұиғҪиҺ·еҫ—и¶іеӨҹзҡ„з»ҸжөҺеӣһжҠҘпјҢе…¶еҸ‘еұ•йҖҹеәҰд№ҹе°ұдјҡжӣҙеҝ« гҖӮ
вҖңж–°еҹәе»әвҖқ究з«ҹжҳҜд»Җд№Ҳ
йҖҡиҝҮд»ҘдёҠеҶ—й•ҝзҡ„и®Ёи®әпјҢжҲ‘们еҸҜд»ҘжҳҺзЎ®дёҖдёӘдәӢе®һпјҡеҹәзЎҖи®ҫж–Ҫжң¬иә«еә”иҜҘжҳҜдёәдәҶеҘ е®ҡй•ҝжңҹеҸ‘еұ•еҹәзЎҖпјҢдёәжҸҗеҚҮзү№е®ҡдә§дёҡзҡ„жңӘжқҘеӣһжҠҘиҖҢжңҚеҠЎзҡ„пјҢе®ғжң¬иә«жңӘеҝ…е…·жңүз»ҸжөҺеҲәжҝҖжүӢж®өжүҖйңҖиҰҒе…·жңүзҡ„зү№еҫҒпјҢд№ҹжңӘеҝ…йҖӮеҗҲз”ЁдәҺдҪңдёәзҹӯжңҹи°ғжҺ§ж”ҝзӯ– гҖӮ
зҺ°еңЁпјҢи®©жҲ‘们жҠҠе…іжіЁзҡ„з„ҰзӮ№йҮҚж–°ж”ҫеӣһеҲ°вҖңж–°еҹәе»әвҖқ гҖӮйҰ–е…ҲпјҢжҲ‘们йңҖиҰҒжҳҺзЎ®дёҖдёӘй—®йўҳпјҢйӮЈе°ұжҳҜ究з«ҹд»Җд№ҲжүҚжҳҜвҖңж–°еҹәе»әвҖқ гҖӮе…ідәҺвҖңж–°еҹәе»әвҖқзҡ„еҶ…ж¶өпјҢзҺ°еңЁжңүеҫҲеӨҡиҜҙжі•пјҢжҲ‘еҪ’зәідәҶдёҖдёӢпјҢиҝҷдәӣиҜҙжі•дё»иҰҒжңүеҰӮдёӢеҮ дёӘжқҘжәҗпјҡ
第дёҖдёӘжқҘжәҗжҳҜеҮ ж¬ЎйҮҚиҰҒзҡ„дёӯеӨ®дјҡи®® гҖӮдҫӢеҰӮпјҢ2018е№ҙ12жңҲзҡ„дёӯеӨ®з»ҸжөҺе·ҘдҪңдјҡи®®е°ұжҳҺзЎ®жҸҗеҮәвҖңиҰҒеҸ‘жҢҘжҠ•иө„е…ій”®дҪңз”ЁпјҢеҠ еӨ§еҲ¶йҖ дёҡжҠҖжңҜж”№йҖ е’Ңи®ҫеӨҮжӣҙж–°пјҢеҠ еҝ«5Gе•Ҷз”ЁжӯҘдјҗпјҢеҠ ејәдәәе·ҘжҷәиғҪгҖҒе·Ҙдёҡдә’иҒ”зҪ‘гҖҒзү©иҒ”зҪ‘зӯүж–°еһӢеҹәзЎҖи®ҫж–Ҫе»әи®ҫвҖқпјҢиҖҢеңЁ2020е№ҙ3жңҲ4ж—ҘеҸ¬ејҖзҡ„дёӯе…ұдёӯеӨ®ж”ҝжІ»еұҖ常委дјҡи®®дёҠпјҢеҲҷжҸҗеҮәдәҶвҖңеҠ еҝ«5GзҪ‘з»ңгҖҒж•°жҚ®дёӯеҝғзӯүж–°еһӢеҹәзЎҖи®ҫж–Ҫе»әи®ҫиҝӣеәҰвҖқзҡ„иҜҙжі• гҖӮдёҖдәӣеӯҰиҖ…з»јеҗҲиҝҷдәӣйҮҚиҰҒдјҡи®®зҡ„иҜҙжі•пјҢи®ӨдёәвҖңж–°еҹәе»әвҖқжҢҮзҡ„еә”иҜҘжҳҜ5GзҪ‘з»ңгҖҒж•°жҚ®дёӯеҝғгҖҒдәәе·ҘжҷәиғҪгҖҒе·Ҙдёҡдә’иҒ”зҪ‘е’Ңзү©иҒ”зҪ‘иҝҷдә”еӨ§йўҶеҹҹ гҖӮдёҚиҝҮпјҢеңЁжүҖжңүзҡ„иҝҷдәӣдјҡи®®дёӯпјҢеҜ№вҖңж–°еҹәе»әвҖқзҡ„иЎЁиҝ°йҮҮз”Ёзҡ„йғҪжҳҜеҲ—дёҫзҡ„ж–№жі•пјҢ并иҝҗз”ЁвҖңзӯүвҖқеӯ—жқҘиЎЁзӨәдәҶзңҒз•Ҙ гҖӮиҝҷж„Ҹе‘ізқҖпјҢи®ӨдёәвҖңж–°еҹәе»әвҖқе°ұжҳҜд»ҘдёҠдә”дёӘйўҶеҹҹпјҢеҫҲеҸҜиғҪи®©иҝҷдёӘе®ҡд№үжҳҫеҫ—иҝҮдәҺзӢӯе°ҸдәҶ 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гҖҺиҪҜ件гҖҸеҢ—дә¬еӨ§еӯҰи®Ўз®—жңә科еӯҰжҠҖжңҜзі»ж•ҷжҺҲйғӯиҖҖпјҡжҠҠжҸЎж•°еӯ—еҹәе»әж–°жңәйҒҮпјҢз§ҜжһҒжҺЁиҝӣиҪҜ件е®ҡд№үеҹәзЎҖи®ҫж–Ҫе»әи®ҫ
- еҸҳеәҹдёәе®қв– еӯҰд№ зҠ№еӨӘдәәзҡ„жҢЈй’ұжҖқз»ҙпјҡеҰӮжһңдёҚжғіз©·дёӢеҺ»пјҢзүўи®°"и¶ӢеҠҝзәҝ+ж”»еҮ»зәҝ+йҳІе®Ҳзәҝ"дёүзәҝзі»з»ҹпјҢдёҮж¬ЎиҜ•йӘҢд»ҺжңӘеӨұиҙҘ
- гҖҺеҮӨеҮ°зҪ‘иҙўз»ҸгҖҸдёӨеёӮеҶІй«ҳеӣһиҗҪжІӘжҢҮ收涨0.66% еҹәе»әгҖҒеҚҠеҜјдҪ“жқҝеқ—иө°ејә
- гҖҗйҹід№җеӨ§зғ©иҸңгҖ‘ж–°еҹәе»әжөӘжҪ®ж¶ҢеҠЁ еӣҪзҪ‘еҚ—зҪ‘еӨ§дёҫжҠ•иө„е……з”өжЎ©
- пјҡд»Һдҝқйҷ©еҲ°''MCN''пјҢдёӯеӣҪе№іе®үдәәеҜҝеҪ“зңҹи·Ёз•ҢдәҶпјҒ
- #еҹәе»ә#еҹәе»әжқҝеқ—еҚҲеҗҺзҲҶжӢү дҝ®еӨҚиЎҢжғ…жҲ–жҢҒз»ӯ
- #жёҜиӮЎжҢ–жҺҳжңә#е°Ҹж‘©пјҡеҹәе»әиЎҢдёҡеўһй•ҝејәеҠІ йҰ–жҺЁдёӯеӣҪдёӯй“Ғ(00390)еҸҠдёӯеӣҪй“Ғе»ә(01186)
- гҖҢеҹәе»әйҖҡгҖҚдёӯеӣҪй“Ғе»әжө·еӨ–жҸҪдёӨеӨ§еҚ•пјҢйҖҶеҠҝдёҠжү¬~
- зҫҺе…ғ@зү№жң—жҷ®жӯЈејҸеҸ‘еёғвҖңеӨҚе·ҘвҖқжҢҮеј• зҫҺеӣҪеҹәе»әи®ЎеҲ’规模жҲ–иҫҫ2дёҮдәҝзҫҺе…ғ
- [жіӣж№ҫеӨ©еҹҹйҮ‘жңҚ]еҹәе»әжңәжў°дјҒдёҡз§°вҖңйӣ¶д»¶дҫӣеә”й“ҫвҖқеҸ—йҳ»пјҢзә·зә·еӨ§е№…ж¶Ё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