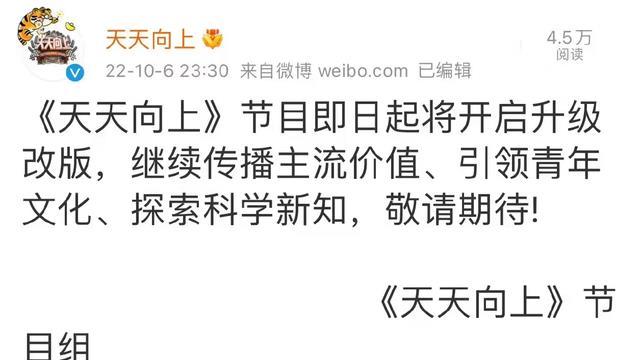еӨ«еӯҗв– жөҒеӨұзҡ„е·қжұҹйҒ—йҹөпјҲдёҠпјү еӨ§е®ҒжІі

еӣҫзүҮ
еӨ§жҳҢеҸӨй•Ү гҖӮ 
еӣҫзүҮ
е®ҒеҺӮеҸӨй•Үйҷ„иҝ‘зҡ„еіЎи°· гҖӮ 
еӣҫзүҮ
ж—§ж—¶е·қжёқдёҖеёҰзҡ„иҲ№е·ҘеҫҲиү°иҫӣ гҖӮ 
еӣҫзүҮ
1946е№ҙйҮҚеәҶдёҮе·һжұҹиҫ№дј‘жҒҜзҡ„ж»©еӨҙзәӨеӨ« гҖӮ
в–ЎжқҺиҙөе№іж–Ү/еӣҫ
зҰ»ејҖдёүеіЎиҖҒ家жқҘжҲҗйғҪе®ҡеұ…е·ІдәҢеҚҒеӨҡе№ҙ пјҢ жҜҸеӨ©е·қжөҒдёҚжҒҜзҡ„жұҪиҪҰгҖҒзҒ«иҪҰгҖҒй«ҳй“ҒгҖҒйЈһжңәгҖҒж‘©жүҳ пјҢ еңЁеҹҺеёӮд№җз« йҮҢж’©жӢЁзқҖиҝ·д№ұзҡ„йҹіз¬Ұ гҖӮ ж¬ЎеЈ°жіўзҲҶжЈҡзҡ„зҺ°д»ЈдәӨйҖҡе·Ҙе…· пјҢ иңҳиӣӣзҪ‘иҲ¬вҖңеҚЎвҖқдҪҸдәҶжҲ‘зҡ„зҒөйӯӮ пјҢ и®©жҲ‘еңЁзІҫзҘһеүҚиЎҢзҡ„и·ҜдёҠзЈ•зЈ•зў°зў° пјҢ дәҺжҳҜеёёеёёеӣһжңӣе…¶е®һж—©е·ІеӣһдёҚеҺ»зҡ„ж•…д№Ў пјҢ еҜ»и§…йӮЈж—©е·ІйҡҗеҺ»зҡ„иҲ№иҝҮжұҹжІігҖҒиҲ№е·ҘжӢүзәӨзҡ„иә«еҪұ гҖӮ дёҖзӣҙи§үеҫ— пјҢ жҲ‘жҳҜе—…зқҖеӨ§е®ҒжІіж°ҙзҡ„ж°”жҒҜй•ҝеӨ§зҡ„ гҖӮ
еЈ№
д»Ҙе‘ҪеҚҡз”ҹеӯҳзҡ„жЎЎеӨ«еӯҗ
еүҚдёҚд№…еӣһе·қдёңиҖҒ家 пјҢ еҫңеҫүеңЁеӨ§е®ҒжІіз•”зҡ„е®ҒеҺӮй•Ү пјҢ йҒҮеҲ°е„ҝж—¶дјҷдјҙзҡ„зҲ¶дәІйҷҲдјҜйҫ„ гҖӮ йҷҲ家зҡ„еҗҠи„ҡжҘјжҳҜиҙҙзқҖеұұй•ҝеңЁж°ҙйҮҢзҡ„ пјҢ зӢӯй•ҝзҡ„жҘјиә«еңЁж»”ж»”жІіж°ҙйҮҢиў«жҸүзўҺжҲҗжӯӘж–ңзҡ„еҖ’еҪұ пјҢ е®ӣиӢҘдёҖдёӘе–қйҶүй…’зҡ„иҺҪжұүйҡҸж—¶иҰҒиў«жІіж°ҙж·№жІЎ гҖӮ йҷҲеӨ§дјҜжү§ж„Ҹз•ҷжҲ‘дҪҸдёҖжҷҡеҶҚиө° гҖӮ иҖҒдәәе№ҙиҝ‘е…«ж—¬ пјҢ и„ёдёҠжІҹеЈ‘зәөжЁӘ пјҢ зҠ№еҰӮиў«еҚғе№ҙжәӘжөҒеҶІиҡҖиҝҮзҡ„еІ©еЈҒ пјҢ дҪҶзІҫзҘһзҹҚй“„ пјҢ зӣ®е…үж·ұйӮғ пјҢ еҸӨй“ңиүІи„ёеәһд»ҝдҪӣжү“дәҶжЎҗжІ№зҡ„жңЁиҲ№жіӣзқҖдә®е…ү гҖӮ йӮЈжҷҡ пјҢ жҲ‘е’ҢйҷҲдјҜзҲ¶еӯҗйғҪе–қдәҶдёҚе°‘й…’ пјҢ йҫҷй—ЁйҳөеғҸд»–еҳҙйҮҢзҡ„еҸ¶еӯҗзғҹиҲ¬иў…иў…еҚҮи…ҫ пјҢ иҮӘ然 пјҢ д№ҹж‘ҶеҲ°дәҶжҲ‘ж„ҹе…ҙи¶Јзҡ„еіЎжұҹиҲ№е·Ҙ гҖӮ
е®ҒеҺӮй•Ү пјҢ жҳҜеҸӨд»Је·қжёқең°еҢәи‘—еҗҚзҡ„еӨ§е®ҒзӣҗеңәжүҖеңЁең° гҖӮ й•ҮеӯҗдҫқеұұеӮҚж°ҙ пјҢ еҗҠи„ҡжҘјгҖҒиҝҮиЎ—жҘјеұӮеұӮеҸ еҸ еҗ‘еіЎи°·ж·ұеӨ„延伸 гҖӮ жҢӮеңЁеұұеҙ–иҫ№зҡ„йқ’зҹіжқҝи·Ҝж—©е·Ідәәиҝ№зҪ•иҮі пјҢ жңүдёҖжҗӯжІЎдёҖжҗӯеңЁиҢ…иҚүдёӯеҮәжІЎ пјҢ е®ӣиӢҘдёҖж®өж®өиў«ж–©еҫ—дёғйӣ¶е…«иҗҪзҡ„жӯ»иӣҮзҡ„йҒ—йӘё гҖӮ йў“еәҹеқҚеЎҢзҡ„ж—§еҺӮжҲҝгҖҒжӘҗе»ҠгҖҒзҙўжЎҘгҖҒзҘ е Ӯе°ҶиҖҒй•ҮеңЁж—¶й—ҙдёҠе®ҡж ј гҖӮ й—ЁеүҚзҹіж ҸдёҠ пјҢ дҪқеҒ»зқҖи…°зҡ„йҖҖдј‘зӣҗе·Ҙе’ҢиҲ№е·ҘеқҗеңЁз«№жӨ…дёҠжҷ’еӨӘйҳі пјҢ е®ҲзқҖи„ҡдёӢзҡ„зІјзІјжіўе…үжҚұиҝҮдәәз”ҹжҷҡжҷҜ гҖӮ дёҖеҸӘзӢ—е„ҝиӯҰжғ•ең°зһ…зһ…жҲ‘иҝҷйҷҢз”ҹдәә пјҢ еҸҲж‘ҮзқҖе°ҫе·ҙи·‘еҲ°жІіиҫ№жүҫеҗғзҡ„еҺ»дәҶ гҖӮ
йҷҲеӨ§дјҜзҡ„家 пјҢ е°ұеңЁе®ҒеҺӮй•ҮеӨ§е®ҒжІіиҫ№ пјҢ зҘ–дёҠеҮ д»ЈйғҪжҳҜжЎЎеӨ«еӯҗеҮәиә« гҖӮ
е…Ёй•ҝдёүзҷҫеӨҡе…¬йҮҢзҡ„еӨ§е®ҒжІі пјҢ еҸ‘жәҗдәҺйҷ•иҘҝз»ҲеҚ—еұұ пјҢ жөҒз»Ҹе·«жәӘгҖҒе·«еұұдёӨеҺҝжіЁе…Ҙжө©жө©й•ҝжұҹ гҖӮ жҳ”ж—ҘеӨ§е®ҒжІі пјҢ д№ұзҹідёӣз”ҹ пјҢ ж»©еӨҡж°ҙжҖҘ пјҢ жңҖйҷ©еӨ„жңү马иҝһжәӘгҖҒ马桑жІұгҖҒж°ҙеҸЈгҖҒеӨ©еқ‘ж№ҫгҖҒеҸ«еҢ–жҙһгҖҒзҷҪж°ҙжІігҖҒ银зӘқеӯҗзӯү гҖӮ жІҝйҖ”жңүеҫҲеӨҡйҷ©ж»© пјҢ еҜ№еҫҖжҳ”йӮЈдәӣиҝҮеҫҖзҡ„иҲ№еҸӘжқҘиҜҙ пјҢ дҝЁз„¶дёҖдёӘдёӘз”ҹе‘Ҫзҡ„й»‘жҙһ гҖӮ иҲ№иЎҢйҷ©ж»© пјҢ жЎЎеӨ«еӯҗжҖ»жҳҜз«ҷеңЁйЈҺеҸЈжөӘе°–жүҝжӢ…еҚғй’§еҺӢеҠӣ пјҢ иҲ№дёҠзҡ„ж—…е®ўиҙ§зү©д№ҹеңЁд»–жүӢеӨҙдёҖжӢЁдёҖжүідёӯи·Ңе®•иө·дјҸгҖҒжӯ»йҮҢйҖғз”ҹ гҖӮ
иҜҙеҲ°жЎЎеӨ«еӯҗ пјҢ еҸ¶еңЈйҷ¶е…Ҳз”ҹдёҖд№қеӣӣе…ӯе№ҙдёғжңҲеҲҠеҸ‘еңЁгҖҠж–ҮжұҮжҠҘгҖӢзҡ„ж–Үз« иҝҷж ·жҸҸиҝ°пјҡжЎЎеӨ«еӯҗ пјҢ жҳҜжҢҮжңЁиҲ№дёҠеҲ’иҲ№жҺЁжЎЎзҡ„дәә пјҢ еӣ е·қжұҹе’ҢеӨ§е®ҒжІійҮҢзҡ„иҲ№еҸӘеӨҡеҚҠз”ЁжЎЎеӯҗ пјҢ жЎЎеӯҗе®үеңЁиҲ№еӨҙдёҠ пјҢ е·ҰдёҖж”ҜеҸідёҖж”Ҝең°й—ҙйҡ”зқҖ гҖӮ е№іж°ҙйҮҢжҺЁиө·жқҘ пјҢ жЎЎеӯҗдёҚи§Ғеҫ—жҖҺд№ҲйҮҚ гҖӮ жҺЁжЎЎеӯҗзҡ„дәәеҫҖеҫҖж…ўжқЎж–ҜйҮҢең°жҺЁзқҖ пјҢ еүҚйқўи·Ҝй•ҝ пјҢ зҠҜдёҚзқҖд»–еӨӘдёҠеҠІ гҖӮ еҲ°дәҶйҖҶеҠҝзҡ„жҖҘж°ҙйҮҢ пјҢ жЎЎеӯҗе°ұйҮҚиө·жқҘ пјҢ жңүж—¶з«ҹиҰҒдёҠзҷҫж–Ө гҖӮ иҝҮж»©зҡ„ж—¶еҖҷ пјҢ жұ№ж¶Ңд№Ӣж°ҙзҡ„еҠӣйҮҸе…ЁеҺӢеңЁжЎЎеӯҗдёҠ пјҢ жҺЁжЎЎеӯҗзҡ„дәәи„ҡ蹬зқҖиҲ№жқҝ пјҢ еҳҙйҮҢе–ҠзқҖвҖңе’Ӣе’Ӣв”Җв”Җе‘өе‘өе‘өвҖқ гҖӮ еҫ…иҝҮдәҶж»© пјҢ жҺЁжЎЎеӯҗзҡ„зҙҜдәҶ пјҢ д»–еҸҲж…ўжқЎж–ҜзҗҶең°жҺЁдәҶ гҖӮ
иҙ°
д»ҘжңЁиҲ№дёә家зҡ„жЎЎеӨ«еӯҗ
йҷҲеӨ§дјҜзҡ„иҜҙжі•жңүдәӣдёҚеҗҢпјҡеңЁй•ҝжұҹдёүеіЎең°еҢә пјҢ вҖңжЎЎеӨ«еӯҗвҖқжҳҜеҜ№жүҖжңүиҲ№е·ҘзәӨеӨ«зҡ„з»ҹз§° пјҢ дёҚеҚ•жҢҮжҺЁжЎЎеӯҗзҡ„дәә гҖӮ
йҷҲеӨ§дјҜж—©е№ҙеңЁе·«жәӘгҖҒе·«еұұдёҖеёҰжҳҜжңүеҗҚзҡ„жЎЎеӨ«еӯҗ пјҢ д»–еҚҒеӣӣеІҒе°ұи·ҹзҲ¶дәІеңЁеӨ§е®ҒжІіиө°иҲ№жӢүзәӨ пјҢ дёҠдё–зәӘдёғеҚҒе№ҙд»ЈеҲқејҖе§ӢеҪ“иҲ№иҖҒеӨ§ гҖӮ йҷҲеӨ§дјҜеңЁжҝҖжөҒйҷ©ж»©йҮҢд»ҺжңӘеӨұжүӢ пјҢ д»–ж°ҙжҖ§жһҒеҘҪ пјҢ д»ҝдҪӣиә«дёҠжөҒж·ҢзқҖйұјзұ»зҡ„еҹәеӣ пјҢ жҲ‘е°Ҹж—¶еҖҷжңүдёҖеӨ© пјҢ жӣҫдәІзңји§Ғд»–д»ҺиҮӘ家еҗҠи„ҡжҘји·іиҝӣжІійҮҢ пјҢ жү‘и…ҫеҮ дёӢеҲ’еҲ°жІіеҝғ пјҢ е°ҶдёӨдёӘеҚЎеңЁзӨҒзҹізјқйҡҷе·®зӮ№иў«ж·№жӯ»зҡ„еЁғеЁғж•‘иө· гҖӮ
йҷҲеӨ§дјҜж—©е№ҙзҡ„жңЁиҲ№е°ұжҳҜ他们зҡ„家 пјҢ дёҖдёӘйҒ®йЈҺйҒҝйӣЁзҡ„жёҜж№ҫ гҖӮ иҲ№й•ҝдәҢеҚҒжқҘе°ә пјҢ е®Ҫеӣӣе°әеӨҡ пјҢ иҪҪйҮҚеӣӣдә”еҗЁ гҖӮ иҲ№дёҠй…Қе‘ҳдёүдәәпјҡдёҖй©ҫй•ҝгҖҒдәҢй©ҫй•ҝгҖҒеӨҙзәӨ гҖӮ жҢүж°ҙжөҒж–№еҗ‘дёҚеҗҢ пјҢ дёүдәәеҲҶе·ҘжңүејӮпјҡдёҠж°ҙж—¶ пјҢ дёҖй©ҫй•ҝз«ҷеңЁиҲ№е°ҫ пјҢ иҙҹиҙЈжҺҢиҲө пјҢ д»–иҰҒеҲ©з”ЁиҲ№е°ҫжӮ¬жҢӮзҡ„жңЁжЎЁе’ҢжүӢдёӯзҡ„зҜҷз«ҝи°ғеәҰиЎҢиҲ№ж–№еҗ‘пјӣдәҢй©ҫй•ҝе’ҢеӨҙзәӨз«ҷеңЁиҲ№еӨҙ пјҢ дёҖдәәдёҖжҠҠй•ҝзҜҷ пјҢ жүӢжҸЎзҜҷиә« пјҢ и„ҡ蹬иҲ№еӨҙ пјҢ д№ҳиҲ№ж—¶дёҖжҠҠдёҖжҠҠдҪҝеҠІе„ҝ пјҢ еҲ©з”ЁеҗҺжҢ«еҠӣжқҘжҺЁеҠЁжңЁиҲ№ гҖӮ еҰӮйҒҮж°ҙзҡ„еҶІеҠӣиҝҮејәжҲ–ж»©йҒ“иҫғй•ҝ пјҢ е…үйқ й•ҝзҜҷзҡ„еҠӣйҮҸдёҚи¶ід»ҘдјёеҲ°ж»©еӨҙ пјҢ з«ӢеңЁиҲ№еӨҙзҡ„еӨҙзәӨе’ҢдәҢй©ҫй•ҝе°ұиҰҒжһңж–ӯи·ідёӢж°ҙ пјҢ еҘ—дёҠзәӨз»ідёҖжӯҘдёҖжӯҘеҫҖеүҚжӢүиҲ№ гҖӮ жӢүиҲ№зҡ„зәӨз»і пјҢ з”ұеҚҒе…ӯдёғиӮЎжөёиҝҮжЎҗжІ№зҡ„зҜҫжқЎе„ҝзј–з»ҮжҲҗ пјҢ й•ҝдәҢеҚҒжқҘзұі пјҢ жӢүеӨ§иҲ№ж—¶е°ұжҚўжҲҗдёүеҚҒеӨҡзұізҡ„ 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жё…жү¬еҗӣиҮӘеӘ’дҪ“#дәәе‘ҳеӨ§йҮҸжөҒеӨұжҲ–е°ҶеҜјиҮҙдјҒдёҡиө°еҗ‘иЎ°иҗҪпјҢе№ёзҫҺиӮЎд»Ҫ继з»ӯдәҸжҚҹ
- гҖҺе”Ҝе“ҒдјҡгҖҸе№ёзҫҺиӮЎд»Ҫ继з»ӯдәҸжҚҹ дәәе‘ҳеӨ§йҮҸжөҒеӨұжҲ–е°ҶеҜјиҮҙдјҒдёҡиө°еҗ‘иЎ°иҗҪ
- дәәжүҚв– NBAдёҺеҸ‘еұ•иҒ”зӣҹе…ұеҗҢе»әз«Ӣж–°йЎ№зӣ®пјҢд»ҘеҮҸе°‘дәәжүҚжөҒеӨұ
- гҖҢгҖҚиҝҮеҺ»еҚҠе№ҙеҠ еҜҶиҙ§еёҒзӨҫеҢәдәәж•°дёӢйҷҚжҳҫи‘—пјҢжҲҗе‘ҳжөҒеӨұжҜ”зҺҮеңЁ25%~75%д№Ӣй—ҙ
- #е·қ科и§ӮеҜҹ#йҒӮе®Ғпјҡеӣӣе·қжұҹж·®е…¬еҸёе…ЁеҠӣд»ҘиөҙиөўжҲҳй«ҳдә§
- #еӨҸеҲ©#дёӨзҷҫеҗҚеӨҸеҲ©е‘ҳе·ҘдёҫжҠҘдёҖжұҪ жҒ¶ж„Ҹз”©зӣҳиҮҙеӣҪжңүиө„дә§жөҒеӨұ
- гҖҢеӨӘе№іжҙӢж—¶е°ҡзҪ‘гҖҚзҺ»е°ҝй…ёжөҒеӨұиҮҙиЎ°еҗ—пјҹе°қиҜ•иӮҢеә•дҝқж№ҝеҗҺжҲ‘зҹҘйҒ“зӯ”жЎҲдәҶ
- гҖҺгҖҸзҫҺеӣҫз”ЁжҲ·йҖҗе№ҙжөҒеӨұ еҰӮдҪ•з•ҷдҪҸвҖңе№ҙиҪ»зҡ„еҝғвҖқпјҹ
- жқҺеӨ«еӯҗиҜҙеҸІTBв– еҚ—е®ӢеҫҲзҫҺеҘҪпјҹзҷҫ姓еҫҲеҜҢи¶іпјҹжҸӯејҖеҚ—е®Ӣзҡ„еҶ…幕пјҢзңӢзңӢдёҚзқҖи°ғзҡ„еҚ—е®Ӣжңқе»·
- гҖҢгҖҚжҡҙйЈҺйӣҶеӣўпјҡе‘ҳе·ҘжҢҒз»ӯеӨ§йҮҸжөҒеӨұ зӣ®еүҚе…¬еҸёд»…еү© 10 дҪҷдә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