ж–°дә¬жҠҘ科塔иҗЁе°”пјҡд»Һе°ҸиҜҙеҲ°з”өеҪұ( дәҢ )
е®үдёңе°јеҘҘе°јйҖҡиҝҮиҝҷз§Қж–№ејҸз»ҷеҮәдәҶжүҳ马ж–Ҝзҡ„иә«д»Ҫпјҡдё“дёҡж‘„еҪұеёҲ пјҢ дёӯдә§йҳ¶зә§ пјҢ жңүиұӘиҪҰе’Ңдј е‘јжңә пјҢ иҝҳжңүдёҖй—ҙдёӘдәәж‘„еҪұе·ҘдҪңе®Ө гҖӮ д»–дёәдәҶжӢҚж‘„е·Ҙдәәйҳ¶зә§е·ҘдҪңзҡ„ж ·еӯҗ пјҢ дё“й—Ёжү“жү®жҲҗжҷ®йҖҡдәә пјҢ 并еңЁе·ҘеҸӢзҡ„её®еҠ©дёӢж··е…Ҙе·ҘеҺӮ гҖӮ д»–зңӢдјјжҳҜдёҖдҪҚдёҚеҠЎжӯЈдёҡзҡ„иҠұиҠұе…¬еӯҗ пјҢ е®һйҷ…дёҠеҜ№ж‘„еҪұе°ӨдёәжҢҡзҲұ пјҢ д№ғиҮіж„ҝж„Ҹд»ҳеҮәз”ҹе‘Ҫ гҖӮ
еңЁгҖҠйӯ”й¬јж¶ҺгҖӢдёӯ пјҢ ж•…дәӢдё»и§’зҪ—дјҜзү№В·зұіжӯҮе°”жҳҜдёҖдҪҚж—…еұ…е·ҙй»Һзҡ„жҷәеҲ©дәә пјҢ е№іж—¶д»ҺдәӢжі•иҜӯзҝ»иҜ‘е·ҘдҪң пјҢ еҒ¶е°”е°қиҜ•дёҡдҪҷж‘„еҪұ гҖӮ е®үдёңе°јеҘҘе°јжҠҠж•…дәӢзҡ„еҸ‘з”ҹең°д»Һе·ҙй»Һжҗ¬еҲ°дәҶдјҰж•Ұ пјҢ 并еҠ е…ҘеҜ№дёҠжөҒиүәжңҜеңҲзіңзғӮз”ҹжҙ»зҡ„еҲ»з”» гҖӮ
еӣһеҲ°е·ҘдҪңе®ӨеҗҺ пјҢ жүҳ马ж–Ҝз«ӢеҚіиў«зӯүеҫ…еӨҡж—¶зҡ„дҝҠдҝҸжЁЎзү№еҢ…еӣҙ пјҢ дёҚеҫ—дёҚжҠ•е…ҘжӢҚж‘„е·ҘдҪң гҖӮ еңЁжӢҚж‘„еҘіжЁЎзү№зҡ„иҝҮзЁӢдёӯ пјҢ жүҳ马ж–Ҝе…Ёжғ…жҠ•е…Ҙ пјҢ ж»ЎжҖҖжҝҖжғ… пјҢ жҺҢжҺ§зқҖдёҖеҲҮ гҖӮ
е®үдёңе°јеҘҘе°јд»ҘжӯӨиҜҙжҳҺж‘„еҪұжңәзҡ„йңёжқғеҠҹиғҪпјҡжүҳ马ж–ҜиҮӘи®ӨдёәеҸҜд»ҘйҖҡиҝҮж‘„еҪұе®ҡж јдёӢзңҹе®һдё–з•ҢжқҘжҺҢжҺ§зҺ°е®һ гҖӮ жүҳ马ж–Ҝе·ҰжүӢжӢҝж‘„еҪұжңә пјҢ еқҗеңЁеҘіжЁЎзү№иә«дёҠзҡ„з»Ҹе…ёй•ңеӨҙпјҲиҝҷеј еү§з…§д№ҹиў«з”ЁдҪңдәҶе°Ғйқўпјү пјҢ иҜҙжҳҺдәҶж‘„еҪұиЎҢдҪҝзқҖдёҺжҖ§иЎҢдёәзӣёдјјзҡ„еҠҹиғҪпјҡеҚ жңү гҖӮ
йҡҸеҗҺ пјҢ жүҳ马ж–Ҝе·ҰжүӢжҢӮзқҖзӣёжңәејҖе§ӢеңЁе…¬еӣӯжҷғиҚЎ пјҢ ж— ж„ҸдёӯеҸ‘зҺ°дёҖеҜ№дёӯе№ҙз”·еҘіеңЁиҚүең°дёҠдәІзғӯ гҖӮ еӣ дёәиҒҢдёҡж‘„еҪұеёҲзҡ„иә«д»ҪдҪҝ然 пјҢ жүҳ马ж–Ҝз«ӢеҚіжӢҚдёӢдәҶиҝҷдёӘеңәжҷҜ гҖӮ е®ҢдәӢеҗҺ пјҢ д»–иҪ¬иә«зҰ»ејҖ гҖӮ дёҚжғі пјҢ жӢҚж‘„иЎҢдёәиў«еҘідәәеҸ‘зҺ° гҖӮ еҘ№зҙ§йҡҸжүҳ马ж–Ҝ пјҢ жғіиҰҒзҙўеӣһиғ¶зүҮ пјҢ еҚҙиў«жүҳ马ж–ҜдёҘеҺүжӢ’з»қ гҖӮ з”ҡиҮіеңЁеҘідәәзҙўиҰҒиғ¶зүҮзҡ„иҝҮзЁӢдёӯ пјҢ жүҳ马ж–Ҝд№ҹдёҚеҝҳе°ҶиҝҷдёӘз”»йқўжӢҚдёӢ гҖӮ
вҖңжңҖйҮҚиҰҒзҡ„дёҚжҳҜжҳҜеҗҰжңүиғ¶еҚ· пјҢ иҖҢжҳҜи°ҒзҹҘйҒ“жҲ‘дјҡжҠҠиҝҷ件дәӢе‘ҠиҜүдҪ 们 гҖӮ з»“жһңжҳҜ пјҢ жҲ‘еҲ¶жӯўдәҶиҮӘе·ұзҡ„и§Ӯеҝө пјҢ дёҚд»…еңЁе…¬е…ұеңәеҗҲжӢҚз…§дёҚиў«е…Ғи®ё пјҢ иҝҳеҫ—еҸ–еҶідәҺдҪ еҲ°еә•жӢҚдәӣд»Җд№ҲвҖҰвҖҰвҖқ
еӣһеҲ°е·ҘдҪңе®ӨеҗҺ пјҢ жүҳ马ж–ҜеҸ‘зҺ°з…§зүҮдёӯзҡ„еҘідәәжқҘеҲ°е®¶дёӯ пјҢ 继з»ӯзҙўиҰҒиғ¶еҚ· гҖӮ еҘідәәеңЁжүҳ马ж–Ҝзҡ„иҜұжғ‘дёӢ пјҢ дё»еҠЁи„ұиЎЈи®©жүҳ马ж–ҜжӢҚж‘„ пјҢ дёӨдәәй—ҙеҸ‘з”ҹдәҶдәІеҜҶзҡ„жҺҘеҗ» гҖӮ еҘідәәиө°еҗҺ пјҢ жүҳ马ж–Ҝе…Ёжғ…жҠ•е…Ҙжҙ—еҚ°з…§зүҮ гҖӮ еӣ дёәеҘідәәзҡ„еҸҚеӨҚйҳ»жҢ пјҢ жүҳ马ж–Ҝи®Өе®ҡиҝҷ件дәӢиӮҜе®ҡжңүи№Ҡи·· гҖӮ еңЁеҶІжҙ—еҮәжқҘзҡ„з…§зүҮдёҠ пјҢ д»–д»”з»ҶеҲҶиҫЁжҜҸдёҖеӨ„з»ҶиҠӮ гҖӮ йҖҡиҝҮж”ҫеӨ§з…§зүҮ пјҢ д»–дјјд№ҺеңЁзҜұз¬ҶеӨ–зҡ„еҜҶжһ—дёӯеҸ‘зҺ°дәҶдәәзҡ„иә«еҪұ пјҢ дёҖжҠҠжҸЎзқҖжһӘзҡ„жүӢд»Һж ‘зҜұдёӯдјёеҮәжқҘ гҖӮ иҝҷеј•иө·дәҶжүҳ马ж–Ҝзҡ„жҖҖз–‘ пјҢ д»–дјјд№ҺеҸ‘зҺ°дәҶдёҖе®—еӣ е©ҡеӨ–жғ…еҜјиҮҙзҡ„и°ӢжқҖжЎҲ гҖӮ
жүҳ马ж–Ҝж·ұеӨңйҮҚеӣһжӢҚз…§зҺ°еңә пјҢ зңҹзҡ„еҸ‘зҺ°дәҶдёҖе…·з”·жҖ§е°ёдҪ“ пјҢ жӯЈжҳҜдёӢеҚҲдёҺеҘідәәжӢҘжҠұзҡ„з”·дәә пјҢ е®үиҜҰең°иәәеңЁиҚүең°дёҠ гҖӮ 第дәҢеӨ© пјҢ еҪ“жүҳ马ж–ҜеҶҚж¬ЎеӣһеҲ°иҚүең°ж—¶ пјҢ е°ёдҪ“е·Із»ҸдёҚи§ҒдәҶ гҖӮ з”өеҪұз»“е°ҫ пјҢ еӨұйӯӮиҗҪйӯ„зҡ„жүҳ马ж–ҜеңЁзҗғеңәиҫ№зңӢеҲ°дёҖзҫӨе¬үзҡ®еЈ«еңЁжү“зҪ‘зҗғ пјҢ иҝҷжҳҜдёҖеңәжІЎжңүзҪ‘зҗғе’ҢзҪ‘зҗғжӢҚзҡ„иҷҡжӢҹжҜ”иөӣ гҖӮ д»–иҝҳеё®еҠ©д»–们жҚЎиө·йӮЈдёӘдёҚеӯҳеңЁзҡ„вҖңзҪ‘зҗғвҖқ пјҢ е°Ҷе…¶жҺ·еӣһзҗғеңәеҶ… гҖӮ д»–еҜ№зҺ°е®һзҡ„и®ӨзҹҘе®Ңе…ЁжЁЎзіҠдәҶ гҖӮ
жҜҸдёҖж¬Ўж”ҫеӨ§иғ¶зүҮ пјҢ жүҳ马ж–ҜйғҪи®Өе®ҡиҮӘе·ұи·қзҰ»вҖңзңҹзӣёвҖқжӣҙиҝ‘дәҶдёҖжӯҘ пјҢ дҪҶдәӢе®һдёҠ пјҢ зңҹзӣёзҰ»д»–и¶ҠжқҘи¶Ҡиҝң гҖӮ еҮ¶жқҖжЎҲеҲ°еә•жңүжІЎжңүеҸ‘з”ҹпјҹд»–з»ҸеҺҶдәҶд»ҺзЎ®е®ҡеҲ°дёҚзЎ®е®ҡзҡ„иҝҮзЁӢ гҖӮ йӮЈеӨ©жҷҡдёҠ пјҢ д»–еңЁиҚүең°дёҠеҸ‘зҺ°зҡ„е°ёдҪ“жҳҜеҗҰжҳҜд»–зҡ„дёҖеңәжўҰе‘ўпјҹз”ұдәҺжІЎжңүз”Ёж‘„еҪұжңәи®°еҪ•дёӢиҝҷдёҖеҲ» пјҢ еӣ жӯӨд»–дҫҝж— жі•зЎ®иҜҒи®°еҝҶзҡ„зңҹе®һжҖ§ гҖӮ еҚідҫҝж‘„еҪұжңәзңҹзҡ„и®°еҪ•дёӢйӮЈдёҖеҲ» пјҢ зңҹзӣёе°ұиғҪзЎ®е®ҡеҗ—пјҹгҖҠж”ҫеӨ§гҖӢз»“е°ҫдёӨдёӘе¬үзҡ®еЈ«еңЁзҪ‘зҗғеңәз©әжүӢжү“зҪ‘зҗғзҡ„дёҫеҠЁ пјҢ дјјд№ҺеҸҲиҜҙжҳҺдәҶзңји§Ғ并дёҚдёәе®һ гҖӮ зңҹе®һдёҺе№»жғізҡ„з•ҢйҷҗеңЁе“ӘйҮҢпјҹиҝҷжҳҜгҖҠж”ҫеӨ§гҖӢжғіжҸҗеҮәзҡ„й—®йўҳ гҖӮ
еҜ№дәҺзҪ—дјҜзү№В·зұіжӯҮе°”жқҘиҜҙ пјҢ и®©д»–йҷ·е…Ҙеӣ°еўғзҡ„дёҚжҳҜз…§зүҮ пјҢ иҖҢжҳҜд»–зҡ„ж„ҸиҜҶ гҖӮ зңҹзӣёдёҚеҸӘжқҘиҮӘдәҺж„ҹе®ҳжҲ–жңәеҷЁи®°еҪ•зҡ„еӨ–йғЁдё–з•Ң пјҢ еҗҢж ·йңҖиҰҒж„ҸиҜҶзҡ„еҸӮдёҺ гҖӮ еҰӮеҗҢеҸҷиҝ°иҖ…еңЁе°ҸиҜҙдёӯиҜҙзҡ„ пјҢ вҖңзұіжӯҮе°”з—ҙиҝ·дәҺж–ҮеӯҰеҲӣдҪңе’Ңзј–йҖ дёҚеҲҮе®һйҷ…зҡ„ж•…дәӢ гҖӮ вҖқгҖҠйӯ”й¬јж¶ҺгҖӢжІЎжңүиҙЁз–‘ж‘„еҪұзҡ„зңҹе®һжҖ§ пјҢ е®ғжҖқиҖғзҡ„жҳҜж„ҹе®ҳеҠ иҜёз…§зүҮдёҠзҡ„дё»и§ӮеҲӣйҖ жҖ§ гҖӮ з…§зүҮиҷҪ然еҺҹж ·е‘ҲзҺ°еҮәзҺ°е®һдё–з•Ң пјҢ дҪҶеҜ№з…§зүҮзҡ„зҗҶи§Је’ҢиҜ йҮҠзҰ»дёҚејҖж„ҹе®ҳзҡ„еҸӮдёҺ пјҢ иҝҷе°ұж¶үеҸҠж„ҹе®ҳе’ҢжңәеҷЁе“ӘдёӘжӣҙиғҪи®ӨиҜҶзңҹе®һдё–з•Ңзҡ„й—®йўҳ гҖӮ
еҸҜд»ҘиҜҙ пјҢ 科塔иҗЁе°”е’Ңе®үдёңе°јеҘҘе°јеҹәдәҺж‘„еҪұзҡ„жң¬иҙЁеҒҡдәҶиҜӯиЁҖе’ҢеҪұеғҸдёӨз§ҚеӘ’д»ӢжүҖиғҪеҒҡеҲ°зҡ„жҖқиҖғе’ҢиҜ йҮҠ гҖӮ гҖҠйӯ”й¬јж¶ҺгҖӢдёӯзҡ„еҸҷиҝ°иҖ…дёҖејҖе§Ӣе°ұйҷ·е…ҘеҸҷдәӢдәәз§°е’ҢеҸҷдәӢж—¶жҖҒзҡ„ж··д№ұдёӯ пјҢ йҡҸд№Ӣдё»и§’зҪ—дјҜзү№В·зұіжӯҮе°”д№ҹйҷ·е…ҘиҜӯиЁҖзҡ„ж··д№ұдёӯпјҡеҪ“д»–жғіеҜ№з…§зүҮиҝӣиЎҢдёҖз§ҚзЎ®е®ҡжҖ§зҡ„иҜ йҮҠ пјҢ еҚҙеҸ‘зҺ°ж‘„еҪұиҺ·еҫ—зҡ„вҖңеҶіе®ҡжҖ§зһ¬й—ҙвҖқпјҲеёғеҲ—жқҫеҗҚиЁҖпјүдёҚд»…жІЎжңүе°ҶзҺ°е®һдё–з•ҢзЎ®е®ҡдёӢжқҘ пјҢ еҸҚиҖҢејҖеҗҜдәҶжҖқз»ҙзҡ„ж— е°ҪжғіиұЎ гҖӮ еңЁгҖҠж”ҫеӨ§гҖӢдёӯ пјҢ жүҳ马ж–ҜзӣёдҝЎз…§зүҮиғҪи®°еҪ•дёӢзҺ°е®һдё–з•Ңзңҹе®һеҸ‘з”ҹзҡ„зһ¬й—ҙ пјҢ з…§зүҮеҜ№зҺ°е®һдё–з•Ңжңүжҹҗз§ҚзЎ®иҜҒдҪңз”Ё пјҢ дёҚж–ӯж”ҫеӨ§жҙ—еҚ°еҺҹеҲқз…§зүҮзҡ„жңәжў°иЎҢдёәиҮӘе§ӢиҮіз»Ҳз¬јзҪ©еңЁе®ўи§ӮжҖ§д№ӢдёӢ гҖӮ еҸҜеҪ“他第дәҢеӨ©йҮҚеӣһвҖңзҠҜзҪӘвҖқзҺ°еңәеҸ‘зҺ°е°ёдҪ“иҺ«еҗҚж¶ҲеӨұеҗҺ пјҢ жңәеҷЁпјҲж‘„еҪұжңәпјүе’Ңж„ҹе®ҳпјҲзңјзқӣпјүеҜ№д»–иҖҢиЁҖжүҚеҸҳеҫ—дёҚеҸҜзӣёдҝЎ 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ж–°дә¬жҠҘ|дә¬йғҠйҷҶең°жЎғејҖе§ӢеҘ—иўӢ жЎғеҶңзӣјж— иўӢж Ҫеҹ№жҠҖжңҜ
- ж–°дә¬жҠҘ|еҲ°жӯӨдёҖжёёпҪңеҘҪзҺ©зҡ„з‘һеЈ«дёңйғЁпјҢдҪ“йӘҢеҫ’жӯҘдёҺзәәз»Үзҡ„д№җи¶Ј
- ж–°дә¬жҠҘ|еҢ—дә¬жө·ж·ҖиӯҰж–№жҹҘеӨ„зҪ‘иҙ·е№іеҸ°зҲұжҠ•иө„пјҢе®һйҷ…жҺ§еҲ¶дәәиў«дёҠзҪ‘иҝҪйҖғ
- ж–°дә¬жҠҘ|иҖғдәҶвҖңзҲ¶жҜҚеҗҲж јиҜҒвҖқзҡ„зҲ№еҰҲпјҢе°ұзңҹзҡ„еҗҲж јдәҶеҗ—пјҹ
- ж–°дә¬жҠҘ|йЈһзҢӘе…ӯдёҖдәІеӯҗй…’еә—йў„и®ўзҺҜжҜ”еўһ1000%пјҢжүҳз®ЎжңҚеҠЎеҸ—ж¬ўиҝҺ
- ж–°дә¬жҠҘ|е„ҝз«ҘиҠӮдёЁдҪ 家еӯ©еӯҗзҡ„иә«й«ҳжӯЈеёёеҗ—пјҹ
- зәӘе®һеҪұзӨҫ|зҺ°иҙ§ йҹҰдјҜ иӮ–е°” еҜҮеҫ·еҚЎ еј—е…°е…Ӣ иҗЁе°”еҠ еӨҡ з»Ҹе…ёж‘„еҪұдҪңе“ҒйӣҶ
- ж–°дә¬жҠҘ|йҮҚеәҶдёҖжҷҜеҢәе…ӯдёҖеүҚеҠЁзү©жүҺе ҶеҮәз”ҹ зҹ®й©¬е‘ҶиҗҢзҺҜе°ҫзӢҗзҢҙж·ҳж°”
- ж–°дә¬жҠҘ|е…ӯдёҖеёҰеЁғеҺ»е“Әе„ҝзҺ©пјҹй«ҳеҫ·ең°еӣҫдёҠзәҝеҮәжёёеҠЁжҖҒжҰңеҚ•
- иҗЁе°”зҺӣ|еҘ№жӣҫжҳҜж‘©жҙӣе“ҘжңҖзҫҺзҺӢеҰғпјҢеӣҪзҺӢдёәеҘ№ж”ҫејғеҗҺе®«дҪідёҪпјҢеҚҙзӘҒ然жҲҗдәҶдёӢе ӮеҰ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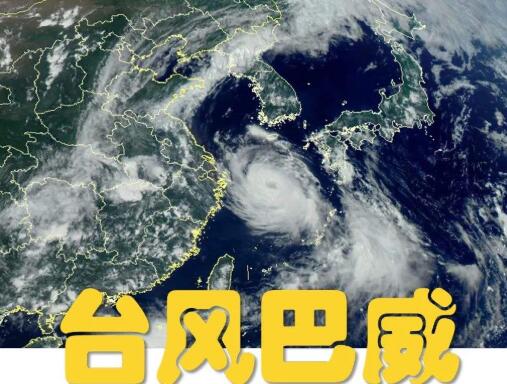



![[иҠ¬е§Ёзҡ„ж•…дәӢдјҡ]еӣҪд№’йҳҹеңЁжҫій—ЁиҝӣиЎҢж··дёҠеҫӘзҺҜеҜ№жҠ—иөӣпјҒзҺӢжҘҡй’Ұе’Ңеӯҷйў–иҺҺжҺ’еҗҚ第дәҢпјҒ](https://imgcdn.toutiaoyule.com/20200418/20200418154109944806a_t.jp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