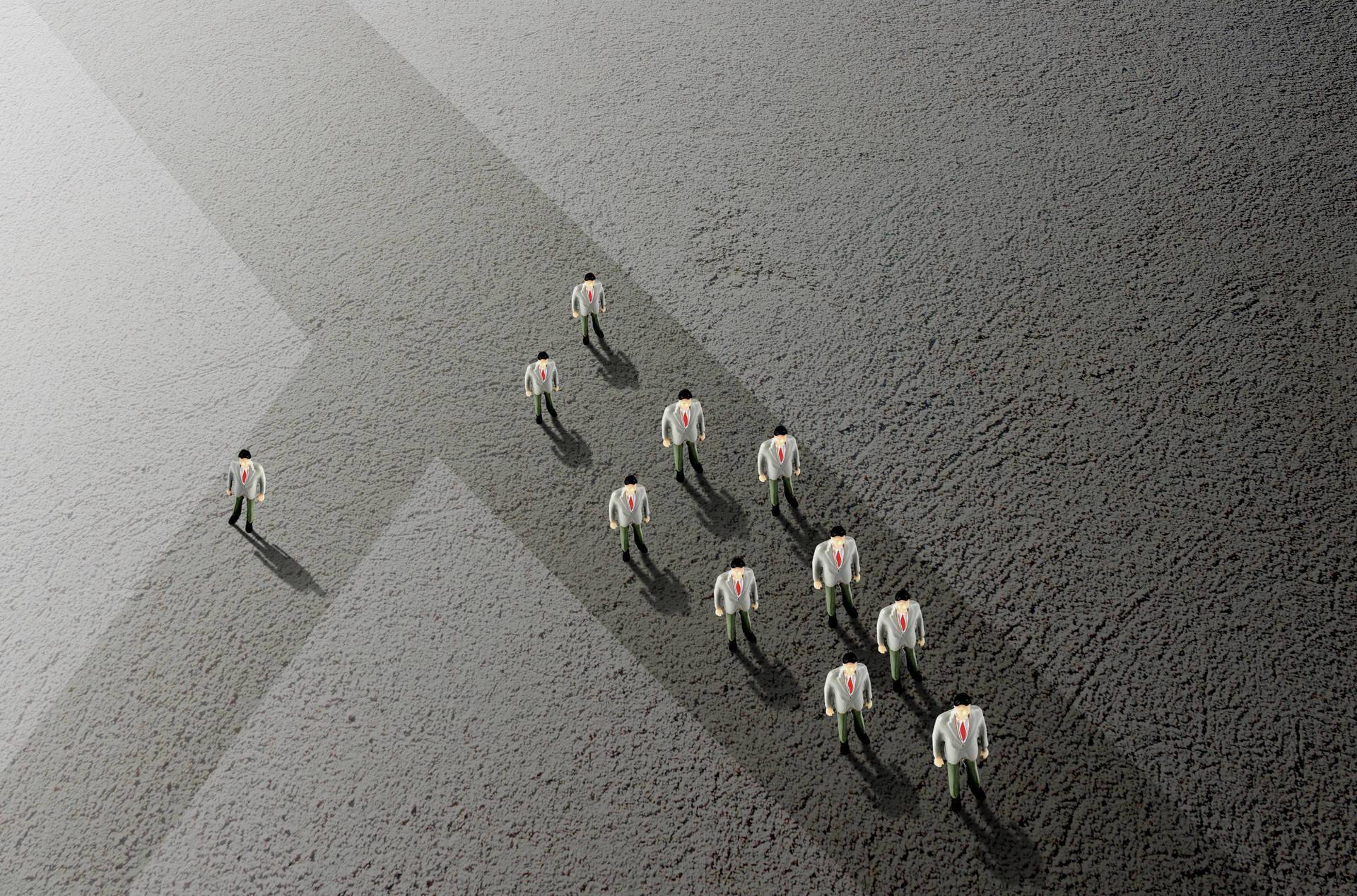作为女权主义者,我该不该割双眼皮?( 八 )
| 德勤《中国医疗美容O2O市场分析》
在女权主义内部 , 关于整形手术的讨论 , 主要可以分成两派 。
一派认为 , 整形工业体现的是父权制度对女性身体的剥削 。 美国女权主义者纳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在《美貌神话》中认为, 美貌神话在男性凝视和资本主义的打造下 , 成为了操控女性的工具 。 女性利用整容手术改变容貌的行为 , 是父权制继续生存下去的土壤之一 。
所谓“美”的标准 , 是社会强加于女性身体之上的 , 让女性审视自己的身体 , 厌恶自己的身体 , 从而试图改变身体 。 当女性屈从于男权社会强加于她身上的外部标准 , 就不能说这是女性自主选择的结果 。 女性或许认为自己作出了自由选择 , 而实际上 , 她们不过是做了男权社会要求她们做的事 。
女性看似有选择 , 实际上并没得选 。 因而 , 加拿大女权主义者凯瑟琳·摩根(Kathryn Morgan)提出女性整形不应该是去整“美” , 而是应该去整“丑”——只有当女性突破和颠覆了那些所谓的一致认可的美的标准时 , 才是真正的反抗 。
另一派认为 , 整形是女性通过掌控自己的身体为自己赋权 。 荷兰女权主义者凯西·戴维斯(Kathy Davis)认为 , 以往对整形手术的批评 , 只顾及了女权主义的“政治正确” , 没有倾听女性自己的声音 。 戴维斯通过对几位做过胸部整形手术的女性进行访谈 , 发现她们只是想变得普通 , 不想因为胸部过大而被投以异样的目光 , 也不想因为胸部过小而被嘲笑“飞机场” 。 接受整形手术的女性 , 希望的不过是终结自己的痛苦 。 她们作出的是理性的、负责任的选择 。 女性在试图运用身体来重塑自我和周遭世界的关系 。
戴维斯在《重塑女体:整形手术的两难》中指出 , “我虽然强烈反对女人为了美丽去挨刀……(但)正因为我把整形手术视为两难 , 我才能够去探索她们的痛苦 , 了解她们如何运用自己的坚韧来减轻痛苦 , 努力在一个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秩序下 , 挣点活动空间 。 ”
挖出“心结”?
我分析自己内心后发现 , 对于我来说 , 似乎两派的观点在我身体上都有体现——“病因”不在我体内 , 但“病灶”在 。
双眼皮是我的“心结” 。 在记忆中 , 我从小就不喜欢自己的眼睛 。 小时候 , 家人经常夸双眼皮的妹妹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 , 而只会夸我“聪明” 。 我曾因此而难过 , 认为对于一个女孩来说 , 漂亮才是最高等级的赞美 。 只是因为我不够漂亮 , 大家才会费尽心力从我身上找寻其它可以夸奖的优点 。
拍照的时候 , 小小年纪的我就很心机地瞪大眼睛 。 照片洗出来之后 , 我的眼睛是变大了 , 但看着也不自然甚至有点滑稽 。 长大后 , 我自拍的时候依然会想办法把眼睛弄成双眼皮 , 不然就拍垂下眼睑、或者闭眼的自己 , 反正就是不希望以真实的面“目”出镜 。
上学后 , 通过讲述基因遗传的生物课 , 我知道了双眼皮是由显性基因决定的 , 推断出爸爸的大双眼皮是Aa(爷爷是单眼皮aa , 所以爸爸的双眼皮一定是Aa) , 妈妈的单眼皮是aa 。 爸妈的后代眼皮有50%概率的Aa , 50%概率的aa 。 爸妈常常开玩笑说 , 我没遗传好 。
而当我向家人和朋友表露“我想割双眼皮”的想法 , 大部分人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没必要 , 真的没必要” 。 和我关系最好的妹妹更是直接表示反对 。 当时我回她说 , 每一个单眼皮的人或许心里都有过做双眼皮手术的想法 , 这是你们双眼皮的人永远不可能感同身受的 。
以双眼皮为美的观点 , 是外界强加于我身体之上的 , 但我确实因此而苦恼 。 在像芭比制造工厂的私立医院体验了一圈 , 我也切身感受到了消费社会对女性的追堵 。 至于做了双眼皮 , 我会不会变得更开心、更自信?我希望会 。 就算不会 , 我觉得自己也能借手术刀挖出横亘心头许久的疙瘩 。 只有流血 , 才能挖出疙瘩 , 别无二法 。
推荐阅读
- 抗议扎克伯格对特朗普言论“不作为”,脸书员工在推特上发起“线上抗议”
- 异地联动警银合作为企业追回290余万被骗资金
- 三亚新增一例温州籍无症状感染者:其父曾作为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接受集中医学观察
- 检察官业绩考评新规矩引领新作为:担当者上 有为者进
- 央行: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
- 纪念赵超构先生诞辰110周年,他作为报坛名家,这些故事你可知?
- 丰台丰台千万元购车补贴怎么领?攻略来了
- 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创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 主动作为暖民心
- 中新网评:为什么疫情下美国疾控中心不断被边缘化?
- 白衣天使抗疫归来“白衣天使”讲故事:作为一名护士我很自豪








![[谈八卦的璐璐]孕妈尽量多吃4种常见食物,或排出胎毒,预防新生儿黄,怀孕期间](https://imgcdn.toutiaoyule.com/20200415/20200415092721790535a_t.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