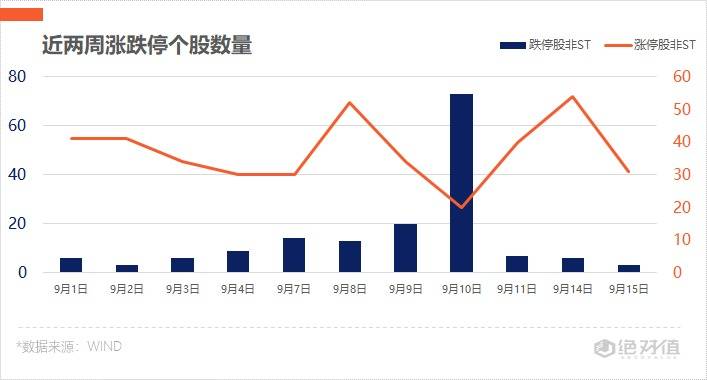е‘Ёе…Ҳз”ҹ|дёӯеӣҪзӘқжЈҡе»әйҖ ж—¶ | 第дёҖдәәз§°( еӣӣ )
зңјеүҚиҝҷдҪҚе Ӯе§җжҳҜдёӘ讲究дҪҶжІЎеӨҡе°‘еҝғжҖқзҡ„дәә пјҢ еӣ жӯӨеңЁзҰ»е©ҡзҡ„дәӢжғ…дёҠжІЎжңүеҫ—еҲ°д»Җд№Ҳиҙўдә§ пјҢ иҷҪ然жҳҜеҘ№зҡ„иҖҒе…¬жңүдәҶжғ…дәә гҖӮ е Ӯе§җжҳҜж•…дәӢзҡ„жң«е°ҫ пјҢ е Ӯе§җзҰ»е©ҡжҳҜжң«е°ҫзҡ„жң«е°ҫ пјҢ еҘ№зҡ„е„ҝеӯҗи·ҹеҘ№дёҖиө·з”ҹжҙ» пјҢ еҰӮжһңе„ҝеӯҗжІЎжңүе°Ҹе„ҝйә»з—№з—Ү пјҢ зҺ°еңЁиҜҙиҜқиғҪжё…жҘҡдёҖзӮ№ пјҢ йӮЈд№ҲиҝҷдёӘжң«е°ҫдјҡжӣҙдҪҝдәәзЁҚеҫ®е®Ҫж…°дёҖзӮ№ гҖӮ
жҲ‘们и·ҹе Ӯе§җеҗғжҷҡйҘӯ пјҢ еҸҲеҗғеҲ°и®ёеӨҡз§ҚдёҚдёҖж ·зҡ„дёңиҘҝ гҖӮ жҲ‘们еҗғдәҶеҫҲеӨҡ пјҢ д№ҹе–қдәҶе•Өй…’ пјҢ е…¶й—ҙе Ӯе§җзҡ„е„ҝеӯҗжғіеҗ‘жҲ‘们д»Ӣз»ҚдёҖдёӘйЈҹзү©зҡ„еҗғжі• пјҢ д»–иҜҙдёҚжё…жҘҡ пјҢ еҸӘжңүд»–зҡ„еҰҲеҰҲиғҪеҗ¬жҮӮ гҖӮ е Ӯе§җ笑зқҖеҗ‘жҲ‘们зҝ»иҜ‘д»–зҡ„ж„ҸжҖқ гҖӮ жҲ‘们зӮ№еӨҙ笑 пјҢ д»–дёҚиҜҙиҜқ пјҢ ж»Ўи¶іең°дҪҺдёӢеӨҙ гҖӮ йӮЈж°”ж°ӣжңүзӮ№е„ҝеғҸе“„дёҖдёӘе°Ҹеӯ© гҖӮ жІҹйҖҡзҡ„з»“жһңжҳҜжҲ‘们дҪҝд»–дёҚеҶҚиҜҙиҜқ гҖӮ
еҗғе®Ңж•Јеңә пјҢ е Ӯе§җйӘ‘дәҶдёҖиҫҶз”өеҠЁиҪҰ пјҢ еҘ№зҡ„е„ҝеӯҗеқҗеңЁиә«еҗҺ пјҢ жҜҚеӯҗдәҢдәәжү“дәҶжӢӣе‘ј пјҢ еҫҖиҝңеӨ„ејҖеҺ» гҖӮ 他们зҡ„иә«еҪұеңЁжҲ‘们еүҚйқўж¶ҲеӨұ гҖӮ
еғҸз”өеҪұ пјҢ иҝҷдёҖзһ¬й—ҙ пјҢ е‘Ёе…Ҳз”ҹиҜҙ пјҢ жҳҜеҗ§ гҖӮ
дә”
жҲ‘们еҲ°жіүе·һжқҘжҳҜеӣ дёәжҲ‘们еҪ“дёӯзҡ„е‘Ёе…Ҳз”ҹд№ҹеҜ№йӮЈж ӢиҖҒжҲҝеӯҗжӢҘжңү继жүҝжқғ гҖӮ еңЁжқҘжіүе·һзҡ„и·ҜдёҠд»–е°ұејҖе§Ӣи®Іиҝ°жіүе·һзҡ„ж•…дәӢ пјҢ жҠұжӯү пјҢ жҲ‘еҗ¬еҫ—еӣ«еӣөеҗһжһЈ пјҢ еӣ жӯӨи®Іеҫ—зЈ•зЈ•з»Ҡз»Ҡ гҖӮ е‘Ёе…Ҳз”ҹжҳҜдёҖдҪҚйҖҚйҒҘеӣӣжө·зҡ„дәә пјҢ йҡҗеҢҝиҖ… пјҢ жөҒжөӘиҖ… пјҢ жҲ‘еҝҳдәҶд»–зҡ„д№ҰдёҠжҳҜиҮӘз§°иҝҳжҳҜеҲ«дәәзҡ„иҜҙжі• пјҢ иҜҙд»–жҳҜвҖңдёҮйҡҫйҖғи„ұд№ӢйҖғвҖқ гҖӮ жҲ‘们еңЁдёҖе®ҡзЁӢеәҰдёҠйғҪдјҡйҖғи„ұ пјҢ иҢғејҸ пјҢ д№үеҠЎ пјҢ д№ жғҜ пјҢ зі»з»ҹ пјҢ 规еҲҷ пјҢ йғҪеҫҲе®№жҳ“ гҖӮ еҸҜжҳҜжҲ‘们没法йҖғи„ұдәҺеҫҖдәӢ гҖӮ е‘Ёе…Ҳз”ҹд№ҹжҳҜжіүе·һеҫҖдәӢзҡ„дёҖе‘ҳ пјҢ д№ҹжҳҜиҖҒжҲҝеӯҗзҡ„дёҖйғЁеҲҶ пјҢ д»–д№ҹи®ёжҳҜйӮЈжңЁжқҝдёҠзҡ„иӢ”и—“ пјҢ д№ҹи®ёд№ҹжҳҜйӮЈеҸЈдә• пјҢ дёҚжё…жҘҡ пјҢ дёҚзҹҘйҒ“ пјҢ д№ҹи®ёжҳҜдёҖеқ—з“Ұз ҫиҖҢе·І гҖӮ д№ҹи®ёжҳҜй—ЁжқҝдёҠзҷҪиӣҫдёӯзҡ„дёҖеҸӘ гҖӮ
еӨңжҷҡ пјҢ жҲ‘们еҮ дёӘдәәе–қзқҖй…’ пјҢ еңЁеӨ©еҸ°дёҠејҖе§Ӣи®Ёи®әдәӢжғ… гҖӮ и®Ёи®әеҲ°жңҖеҗҺеҫҖеҫҖдёҚзҹҘйҒ“еңЁи®Ёи®әд»Җд№Ҳ гҖӮ жҲ‘们дҪҸзҡ„йӮЈе®¶ж°‘е®ҝеҫҲйқҷ пјҢ жіүе·һзҡ„дёңеЎ”е’ҢиҘҝеЎ”жёҗжёҗеҸӘеү©дёӢиҪ®е»“ гҖӮ жҲ‘们еҘҪеғҸи°ҲеҲ°дәҶдёүеІӣз”ұзәӘеӨ«зҡ„гҖҠйҮ‘йҳҒеҜәгҖӢ гҖӮ йЈҺеҗ№еңЁи„ёдёҠ пјҢ й…’зІҫеңЁжҲ‘зҡ„иә«дёҠ移еҠЁ гҖӮ
иүәжңҜзҡ„йҒ“и·ҜжҳҜжҺҘиҝ‘зңҹе®һзҡ„йҒ“и·Ҝ пјҢ жҲ‘еҜ№д»–们иҜҙ гҖӮ еҰӮжһңдҪ е–қдәҶеҫҲеӨҡй…’дҪ е°ұдјҡиҜҙеҮәйӮЈдәӣеҘҮеҘҮжҖӘжҖӘзҡ„иҜқ пјҢ е®ғеҜ№еҲ«дәәжІЎжңүд»Җд№Ҳд»·еҖј пјҢ д№ҹи®ёеҜ№дҪ иҮӘе·ұжңү пјҢ д№ҹи®ёеҜ№и·ҹдҪ дёҖиө·е–қй…’зҡ„жңӢеҸӢжңү гҖӮ
ж•…дәӢзҡ„з»“е°ҫе°ұжҳҜжӯ»дәЎ пјҢ жҲ‘жҳҜдёӘжІЎд»Җд№ҲйҖүжӢ©жқғзҡ„дәә пјҢ жҲ‘жҳҜдёӘ NobodyгҖӮ жҲ‘зҡ„иӢұж–ҮеҫҲзіҹзі•дҪҶжҲ‘и®°еҫ—иҝҷдёӘеҚ•иҜҚ пјҢ NobodyпјҢ жҜ«дёҚйҮҚиҰҒзҡ„дәә пјҢ жҳҜеҗ§пјҹ
дҪ й”ҷдәҶ пјҢ е‘Ёе…Ҳз”ҹиҜҙ гҖӮ д»–й…’еҗҺзҡ„еЈ°йҹіеӣ дёәеҺҡйҮҚиҖҢеўһеҠ дәҶдёҖдәӣжқғеЁҒж„ҹ гҖӮ
дҪ дёҚжҳҜ nobodyпјҢ дҪ дёҚиҰҒжҠҠиҮӘе·ұж”ҫиҝӣеҸҰдёҖдёӘи®Ёи®әжЎҶжһ¶еҺ»е®үж…°иҮӘе·ұ пјҢ жҲ‘们жүҖжңүдәәе…ҲжҳҜиҰҒз”ҹжҙ» пјҢ еңЁз”ҹжҙ»йҮҢдҪ дёҚз®—жҳҜ nobody пјҢ дҪ жңүйӮЈд№ҲеӨҡеҸҜд»ҘйҖүжӢ©зҡ„ гҖӮ зңҹжӯЈзҡ„ nobody жҳҜжҲ‘зҡ„е Ӯе§җе’ҢеҘ№е„ҝеӯҗ пјҢ е‘Ёе…Ҳз”ҹиҜҙ пјҢ зңҹжӯЈзҡ„ nobody жҳҜйӮЈдёӘжөҒжөӘжұү гҖӮ
е…ӯ
еҢ—дә¬зҡ„дјҡи®®жЎҢдёҠжӯӨж—¶жІүй»ҳдәҶ пјҢ еӨ§е®¶дјјд№ҺеңЁжҖқиҖғдёҖдёӘд»Җд№Ҳй—®йўҳ пјҢ жҲ‘жІЎеҗ¬еҲ° пјҢ еӣ жӯӨеҸӘеҘҪдҪҺдёӢеӨҙ пјҢ д№ҹеҒҮиЈ…жӯЈеңЁжҖқиҖғ гҖӮ зӘ—еӨ–е‘је•ёзҡ„еҶ·з©әж°”иҙҙеңЁзҺ»з’ғдёҠ пјҢ жёёејӢ пјҢ йҖЎе·Ў пјҢ еғҸеӨҸеӨ©зҡ„иӢҚиқҮйӮЈж ·жғій’»иҝӣжқҘ гҖӮ е®ғ们еҲ¶йҖ еҮәеЈ°йҹіжӣІжҠҳзҡ„еҷӘйҹі пјҢ еғҸеҸЈе“Ё пјҢ еғҸеҸ№жҒҜ пјҢ д№ҹеғҸзІ—йҮҚзҡ„е–ҳж°” гҖӮ еұӢйҮҢжҳҜжҡ–зҡ„ пјҢ жңүдёҖз§Қиў«еӣҙеӣ°зҡ„ж„ҹи§үзҺҜз»•еӣӣе‘Ё гҖӮ
жҲ‘з»ҷе‘Ёе…Ҳз”ҹеҸ‘дәҶдёӘдҝЎжҒҜ пјҢ жҲ‘й—®д»– пјҢ еңЁжіүе·һйӮЈдёӘеё®дҪ 们зңӢ家зҡ„жөҒжөӘжұүеҸ«д»Җд№ҲеҗҚеӯ—пјҹ
жҲ‘д№ҹдёҚи®°еҫ—дәҶ пјҢ е‘Ёе…Ҳз”ҹиҜҙ гҖӮ
еңЁжіүе·һйӮЈеӨ© пјҢ жҲ‘еӣһжғізқҖ пјҢ жҲ‘们и·ҹзқҖе Ӯе§җеңЁйӮЈж ӢиҖҒе®…еӯҗз»•дәҶдёҖеңҲ пјҢ жңҖеҗҺжүҚеҲ°дәҶжөҒжөӘжұүзҡ„ең°ж–№ гҖӮ
жҳҜзҡ„ пјҢ жҳҜең°ж–№ пјҢ дёҚжҳҜжҲҝеӯҗ гҖӮ и·ҹжҲ‘жғіиұЎзҡ„дёҚеҗҢ пјҢ е‘Ёе…Ҳз”ҹиҜҙжөҒжөӘжұү帮他们зңӢ家 пјҢ йӮЈд№ҲжҲ‘д»Ҙдёәд»–дјҡдҪҸеңЁиҖҒжҲҝеӯҗйҮҢ пјҢ еӣ жӯӨжҲ‘们еңЁйӮЈеӨ§жҲҝеӯҗйҮҢиө° пјҢ жҲ‘жҳҜзӯүзқҖеңЁжҹҗдёӘи§’иҗҪзҡ„дёҖй—ҙйҮҢзңӢи§Ғз”ҹжҙ»з”Ёе“Ғ пјҢ еәҠй“әгҖҒжЎҢжӨ…гҖҒи„ёзӣҶд»Җд№Ҳзҡ„ гҖӮ
дҪҶжҳҜжІЎжңү гҖӮ жҲ‘们жҳҜдёҖзӣҙиө°еҲ°дәҶжҲҝеӯҗеӨ–йқў пјҢ еұӢеҗҺзҡ„дёҖеқ—еғҸдёӢж°ҙйҒ“зҡ„жұҮйӣҶеҢә пјҢ з”ұдәҺе»әи®ҫ规еҲ’зҡ„еӨұиҙҘиҖҢеҪўжҲҗзҡ„йӮЈж ·дёҖеӨ„з©әең°дёҠ гҖӮ жңүдёҖдёӘй»‘иүІзҡ„зӘқжЈҡ гҖӮ зӘқжЈҡ пјҢ еә”иҜҘз”ЁиҝҷдёӘиҜҚвҖ”вҖ”дёҖдёӘдёүи§’еҪўзҡ„зӘқжЈҡвҖ”вҖ”еҮ еқ—жңЁжҹұжҗӯиө·жқҘ пјҢ зңӢиө·жқҘзӣёеҪ“еқҡеӣә пјҢ дёҚжҳҜеҸӘдҪҸдәҶдёүдёӨе№ҙзҡ„ж ·еӯҗ гҖӮ ж—Ғиҫ№жҳҜеҮ ж №й’ўдёқ пјҢ жҢӮдәҶеҮ 件衣зү© пјҢ е…¶дёӯжңүеҮ 件зәўиүІзҡ„еҘідәәеҶ…иЎЈ пјҢ еңЁйЈҺйҮҢйқўж‘ҮжҷғзқҖ 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зҲұзәўиҒҠж—…жёё|еңЁдёӯеӣҪзҡ„еӨ–еӣҪжёёе®ўдәәж•°жӯЈеңЁиҝ…йҖҹеўһеҠ пјҢеӨ–еӣҪдәәеҜ№дёӯеӣҪзҡ„еҸ‘еұ•ж„ҹеҲ°жғҠ讶
- ж—…иЎҢи¶ЈдәӢзҺ°еңә|дёӯеӣҪвҖңжңҖеқ‘дәәвҖқзҡ„4еӨ§жҷҜзӮ№пјҢйј“жөӘеұҝдёҠжҰңпјҢжёёе®ўиЎЁзӨәдёҚж„ҝеҺ»з¬¬дәҢж¬Ў
- зҲұж—…жёёзҡ„е°Ҹзұіе•Ұ|дёӯеӣҪдәәдёҖз”ҹвҖңеҝ…еҺ»вҖқзҡ„4еә§еҹҺеёӮпјҢж—¶й—ҙеңЁеҝҷд№ҹиҰҒеҺ»пјҢзңӢзңӢдҪ еҺ»иҝҮеҮ еә§
- дёӯеӣҪжҳ“з»ҸйЈҺж°ҙе®қе…ё|зӢ¬е®¶гҖҗжҜҸж—Ҙе®ңеҝҢгҖ‘2020е№ҙ7жңҲ21ж—Ҙ
- еӨ§зҗҶ|вҖңеҗје ӮиҖҒзҒ«й”…иҮҙйғ‘жҒәе…Ҳз”ҹзҡ„дёҖе°ҒдҝЎвҖқеј•зғӯи®®пјҢвҖңиө°пјҢеҺ»еӨ§зҗҶпјҒвҖқеңЁзңӢж•°з ҙдёҮ
- дёӯеӣҪж—…жёёж–°й—»зҪ‘|жҺўзҙўдёүжұҹжәҗеӣҪ家公еӣӯзҡ„йҰ–жү№е…ҲиЎҢиҖ…
- иҘҝеҸҢзүҲзәі|дә‘еҚ—зҡ„еӨңжҺўпјҢжүҚжҳҜдёӯеӣҪеӨңжҺўжҙ»еҠЁзҡ„зҺӢзӮё
- ж—…жёёдёҺж‘„еҪұmedia|ж°ёе…ҙдёӯеӣҪ第дёҖ银жҘјпјҢиҖ—银дә”дёҮдҪҷдёӨпјҢеҚҙжӣҫе…ҘеӣҙеҚҒеӨ§дё‘йҷӢе»әзӯ‘пјҒ
- еҘҮи‘©|зӣҳзӮ№дёҖдёӢйӮЈдәӣи®©дәәе“ӯ笑дёҚеҫ—еҘҮи‘©жӯ»дәЎзҡ„дёӯеӣҪеҸӨд»ЈзҡҮеёқ
- дёӯзҲұж–ҮеҢ–дј еӘ’|гҖҠдёӯеӣҪзҲұжғ…иҜ—еҲҠгҖӢжұҹйЈһиҚҗиҜ—пјҲ第дәҢжңҹпјү







![[科жҠҖеҗүжҷ®иөӣ]vivoе“ҒзүҢжҖҺж ·пјҹдёүжңҲд»ҪжүӢжңәеёӮеңәй”ҖйҮҸзЁіеұ…第дәҢпјҢз”Ёж•°жҚ®иҜҙиҜқдёүжңҲд»ҪеӣҪеҶ…жүӢжңәеёӮеңәй”ҖйҮҸпјҢvivoиЎЁзҺ°дә®зңјд»Ҙз”ЁжҲ·дёәдёӯеҝғпјҢиҙҙеҝғжңҚеҠЎж·ұеҫ—дәәеҝғе“ҒзүҢе®һеҠӣпјҢз”Ёдә§е“Ғе“ҒиҙЁиҜҙиҜқз»“иҜӯ](http://ttbs.guangsuss.com/image/c92ba5d463221c86eb29b93205308d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