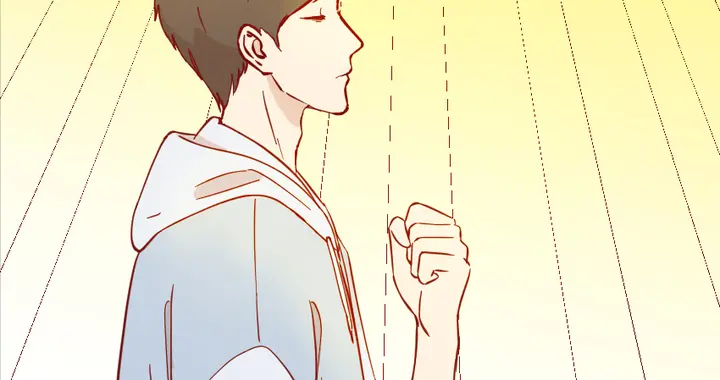|“土到掉渣”的五条人,凭什么能成功出圈?( 二 )
粗糙、广东、市井 , 这是仁科在一次采访中对自己音乐的形容 。 他和阿茂力求贴近打工仔的生活 , 打动寓居城乡之人的破碎之心 。 他们不拒绝这个社会 , 而是一直在融入它 , 但是 , 方言的门槛、宣传资源的有限 , 让这支希望影响更多人的乐队遇到壁垒 , 直到《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出现 , 他们终于有了走向大众的可能 。
本文插图
五条人参加《乐队的夏天》开场logo 。
在《乐队的夏天》的舞台 , 他们看起来很像是小镇出身、酷拽酷拽的青年人 , 但在私底下 , 他们又和知识分子一样爱读书 。 在博尔赫斯书店 , 仁科曾经买过一本吉尔·德勒兹的《运动-影像》 , 这件事被作家叶三记录下来:
“他熟练地在扉页上盖上博尔赫斯书店的钢印 。 收款台旁边的书架上摆着让-菲利普·图森全集 , 封面是仁科的女朋友设计的 。 其中一本《急迫与忍耐》的封面上 , 一个人安详地躺在远去的公共汽车旁 , 双手放在胸前 。 仁科说他是这幅画的模特 。 ”(正午故事:《五条人: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
一双红色人字拖
本文插图
五条人参加《乐队的夏天》之后 , 网友制作的表情包 。 来自微博@乐队的夏天 。
在粤语里 , 条是“个”的意思 , 所谓五条人 , 就是五个人 , 仁科和阿茂组建乐队时 , 期盼着今后能人丁兴旺 , 就把名字起做了五条人 。 关于这个名字还有一个段子:“讲的是五条人被请到一场音乐节上做演出 。 主办方听说乐队名叫五条人 , 就给安排了五个人住的房间 。 ”(民谣故事:《专访五条人:爱情在发廊里撒谎 , 音乐在石牌桥成精》)
他们的定位在草根 , 在那些城乡之间飘摇行走、卖力维生的人群中 。 他们不为王侯将相唱颂歌 , 吟咏打工仔的哀愁与喜乐 。 小贩、底层员工、流浪艺人、乡镇女孩 , 乃至那些在黑暗缝隙夹缝求生的失语者 , 是他们歌曲里的群像 , 在歌曲《李阿伯》里 , 他们唱道:
“田边李阿伯/拿着锄头 戴着斗笠/口中叼着一根烟/我问他:嘿 , 那是什么烟?/——“卷烟呢”/我递给阿伯一根烟/他说:你这种烟没什么味/我问他生活过得好不好?/他说勉勉强强过日子 。 ”
五条人歌唱江湖众生 , 但并不是士大夫那样悲天悯人的姿态 , 他们有点皮、有点逗 , 用下里巴人 , 玩阳春白雪 , 他们有意识地把粤语、潮汕方言融入歌曲 , 在市井烟火中延续知识分子的底色 , 在音乐品位上 , 五条人的歌曲让人想起台湾客家美浓镇出来的交工乐队 , 尽管姿态上“土里土气” , 但他们关心的主题并不小众 , 包含了全球化、贫富分化、打工子弟生存境况等宏大主题 。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 , 五条人把目光对准产业化后利益旁落的边缘人 , 聚焦那些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却面临失语困境的底层 。
因此 , 五条人其实在用柔软的外壳藏住一根尖刺 。 它指向了中国的现实问题 , 那些失落的人、幻灭的人、不甘的人 , 成为音乐人凝视的焦点 。 就像欧阳江河的长诗《凤凰》里写道:
“那些夜里归来的民工 , /倒在单据和车票上 , 沉沉睡去 。 /造房者和居住者 , 彼此没有看见 。 /地产商站在星空深处 , 把星星/像烟头一样掐灭 。 他们用吸星大法/把地火点燃的烟花盛世/吸进肺腑 , 然后 , 优雅地吐出印花税 。 ”
本文插图
“我们喜欢写一些身边人的故事 。 ”图片来自爱奇艺截图 。
《道山靓仔》也是这样一首有现实关怀的曲子 。 它表面上玩世不恭、有些搞笑 , 歌曲里那位靓仔 , 一边被现实锤打 , 一边嘲弄现实 , 但仔细品味 , 所谓道山靓仔 , 既是海丰小城酷拽酷拽的青年 , 也是那些身处阶层固化时代 , 郁郁不得志的年轻人 。 他们渴望出人头地 , 却被现实壁垒阻拦 , 想让阿妈有一天脸上有光 , 却糊里糊涂 , 沦落到派出所的命运 。
推荐阅读
- 真理科技原创 知道为什么自己的Vlog不如别人的好吗?飞宇VLOG pocket2体验
- 科学家|数位伟大的科学家都承认上帝的存在,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了什么?
- 青岛12家景区对所有游客免门票|青岛12家景区对所有游客免门票 哪12家免费?哪些打折?免费时间什么时候?
- 咖啡可乐2021年在美国上架|咖啡可乐2021年在美国上架什么情况?怎么回事?终于真相了,原来是这样!
- 悲剧!妈妈倒车时不慎撞死自己孩子 她应该负什么责任?
- 小伙重拾失传高楼米线绝活|小伙重拾失传高楼米线绝活什么情况?终于真相了,原来是这样!
- 海峡网|李健姚勇为什么退出水木年华,水木年华成员资料
- 维权骑士游戏|荒野乱斗:什么射手值得玩?S级射手布洛克全方位上手教学
- 大连疫情或起始于海鲜加工车间|大连疫情或起始于海鲜加工车间 具体什么情况?
- 枝头的喜鹊|准大学生入学应该预备什么?只需这四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