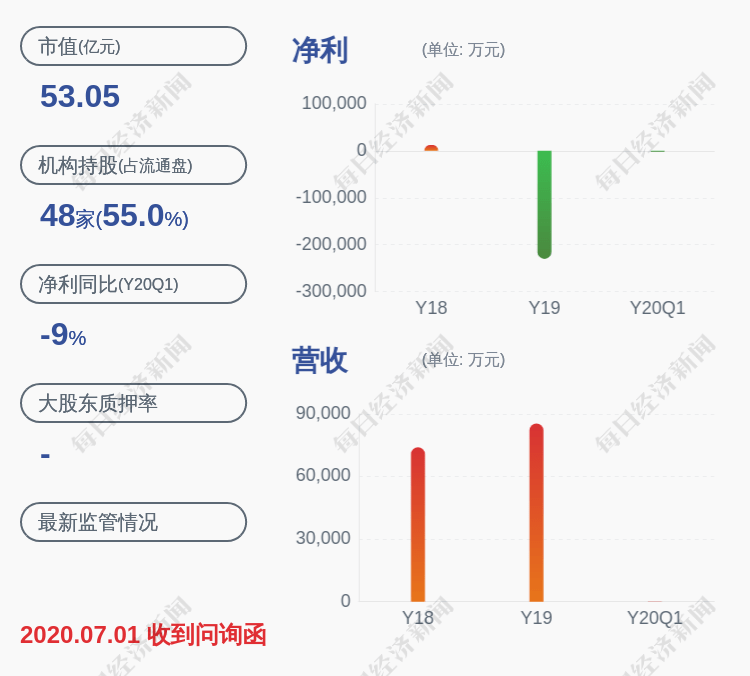з”ҹжҙ»|жҖқжғіиҖ…пҪңеӯҷеҗ‘жҷЁпјҡжҲ‘з»ҷеӨ–еӣҪеӯҰз”ҹи®ІвҖңиә«дҪ“еҸ‘иӮӨеҸ—д№ӢзҲ¶жҜҚвҖқпјҢ他们дёәдҪ•еҫҲеҸ—йңҮеҠЁпјҹ( дёү )
еңЁиҝҷз§Қз”ҹе‘Ҫзҡ„延з»ӯдёӯпјҢжңҖдё»иҰҒзҡ„жғ…ж„ҹдёҚжҳҜеёҢи…ҠжүҖејәи°ғзҡ„вҖңжғ…зҲұвҖқпјҢжҲ–жҳҜеӨ«еҰ»д№Ӣй—ҙзҡ„жғ…ж„ҹпјҢиҖҢжҳҜзҲ¶жҜҚдёҺеӯҗеҘід№Ӣй—ҙзҡ„вҖңдәІдәІвҖқгҖӮеӣ жӯӨдёӯеӣҪж–ҮеҢ–дёӯпјҢе°ұи®ІжұӮдәІдәІпјҢ然еҗҺеӯқжӮҢгҖҒд»ҒзҲұпјҢд»Һиҝҷз§ҚжңҖиҙЁжңҙгҖҒжңҖеҹәзЎҖгҖҒжңҖиҮӘ然зҡ„жғ…ж„ҹдёӯеҸ‘еұ•еҮәдёҖдёӘеҹәжң¬еҫ·жҖ§пјҢз§°д№ӢдёәвҖңеӯқвҖқгҖӮиҝҷеңЁиҘҝж–№ж–ҮеҢ–иғҢжҷҜдёӢеҫҲйҡҫзҗҶи§ЈпјҢеӣ дёәеңЁд»–们зңӢжқҘпјҢзҲ¶жҜҚеӯҗеҘід№Ӣй—ҙжҳҜдёҖз§ҚиҮӘ然жғ…ж„ҹпјҢи°ҲдёҚдёҠеҫ·жҖ§гҖӮжҲ‘们зңӢиҝҷдёӘвҖңеӯқвҖқеӯ—пјҢдёҠйқўжҳҜдёҖдёӘвҖңиҖҒвҖқпјҢдёӢйқўжҳҜдёҖдёӘвҖңеӯҗвҖқпјҢиҝҷжҳҜдёҖз§ҚеҫҲжңҙзҙ зҡ„иЎЁиҫҫж–№ејҸгҖӮдёӯеӣҪж–ҮеҢ–йҖҡиҝҮвҖңеӯқвҖқиҝҷж ·дёҖз§Қеҫ·жҖ§пјҢе°ҶдёӨдёӘдё–д»ЈиҝһжҺҘиө·жқҘгҖӮ
еҗҢж—¶пјҢиҝҷдёҖеҫ·жҖ§д№ҹжҳҜжңүиҮӘ然еҹәзЎҖзҡ„пјҢйӮЈе°ұжҳҜз”ұвҖңдәІдәІвҖқзҡ„жғ…ж„ҹжқҘж”Ҝж’‘гҖӮеҪ“然пјҢиҝҷиҝҳдёҚеӨҹгҖӮжүҖд»ҘпјҢеӯ”еӯҗи®Ід»ҒзҲұгҖҒи®Ід»ҒиҖ…зҲұдәәпјҢеӯҹеӯҗи®Ід»Ғж°‘гҖҒи®ІзҲұзү©пјҢе°ҶиҝҷдёҖжғ…ж„ҹдёҚж–ӯжҺЁе№ҝеҮәжқҘпјҢжңҖеҗҺиҫҫеҲ°жіӣзҲұдј—з”ҹгҖҒжіӣзҲұеӨ©дёӢзҡ„жҰӮеҝөгҖӮиҝҷж ·дёҖдёӘжҰӮеҝөзҡ„иө·зӮ№пјҢе°ұдёҚжҳҜд»ҺеҚ•зәҜзҡ„дёӘдҪ“гҖҒд»ҺиҮӘжҲ‘еҮәеҸ‘пјҢиҖҢжҳҜд»ҘдәәдёҺдәәзӣёдә’д№Ӣй—ҙзҡ„дәІжғ…дҪңдёәеҹәзӮ№гҖӮиҝҷе°ұжҳҜдёӯеӣҪж–ҮжҳҺеңЁдёӨеҚғеӨҡе№ҙзҡ„еҺҶеҸІдёӯпјҢйҖҗжёҗеҸ‘еұ•еҮәжқҘзҡ„зҗҶи§Јдё–з•ҢгҖҒзҗҶи§Јз”ҹе‘Ҫзҡ„дёҖз§Қеҹәжң¬жҖҒеҠҝпјҢ并且еҪўжҲҗдәҶиҮӘиә«зҡ„ж јеұҖгҖӮеҪ“然пјҢе…¶дёӯд№ҹиҮӘ然дјҡжңүдёҖдәӣеұҖйҷҗжҖ§пјҢдҪҶдёӯеӣҪдәәзҗҶи§Јз”ҹе‘Ҫзҡ„ж–№ејҸжҳҜжңүе…¶жҷ®йҒҚжҖ§зҡ„гҖӮ
2019е№ҙдёӢеҚҠе№ҙпјҢжҲ‘еңЁжҹҸжһ—иҮӘз”ұеӨ§еӯҰе“ІеӯҰзі»и®ІдёӯеӣҪе“ІеӯҰгҖӮеҪ“жҲ‘и®ІеҲ°вҖңиә«дҪ“еҸ‘иӮӨеҸ—д№ӢзҲ¶жҜҚвҖқзҡ„ж—¶еҖҷпјҢеӨ–еӣҪеӯҰз”ҹжҷ®йҒҚеҫҲеҸ—йңҮеҠЁгҖӮ他们и§үеҫ—иҝҷд№ҲдёҖдёӘжё…жҷ°зҡ„пјҢеҜ№дәҺдәәзұ»жқҘиҜҙйқһеёёжҷ®йҒҚзҡ„з”ҹеӯҳи®әдәӢе®һпјҢеҚҙжҳҜ他们д»ҺжқҘжІЎжңүи®ӨзңҹжғіиҝҮзҡ„гҖӮеңЁиҘҝж–№зҺ°д»ЈзӨҫдјҡдёӯпјҢдәә们дҪҶеҮЎжғіеҲ°дәәпјҢдјјд№ҺйғҪеҸӘжҳҜвҖңдёӘдҪ“вҖқпјҢвҖңиә«дҪ“еҸ‘иӮӨеҸ—д№ӢзҲ¶жҜҚвҖқиҝҷдёӘз”ҹеӯҳи®әеҹәжң¬дәӢе®һе®Ңе…ЁжҲҗдәҶзӣІзӮ№гҖӮ
дёәдҪ•вҖңеӯқвҖқеңЁдёӯеӣҪж–ҮеҢ–йҮҢеҰӮжӯӨйҮҚиҰҒпјҹеҘ—用马дёҒВ·и·Ҝеҫ·жүҖиҜҙзҡ„вҖңеӣ дҝЎз§°д№үвҖқпјҢдёӯеӣҪж–ҮеҢ–зҡ„жҰӮеҝөе°ұжҳҜвҖңеӣ еӯқз§°д№үвҖқгҖӮеҜ№з”ұвҖңдәІдәІвҖқиҖҢжқҘзҡ„вҖңеӯқвҖқзҡ„йҮҚи§ҶпјҢжҳҜзӣҳжҙ»дёӯеӣҪж–ҮеҢ–зҡ„дёҖдёӘжһўзәҪзӮ№гҖҒж ёеҝғзӮ№пјҢе®ғжҳҫзӨәдәҶжҲ‘们еҜ№дәҺеёҢжңӣгҖҒдёҚжңҪе’Ңдё–д»Јзӣёе…ізҡ„дёҖдәӣиҒ”зі»гҖӮ
вҖңдәІдәІвҖқдёҺвҖңдёӘдҪ“вҖқ并дёҚзӣёдә’жҺ’ж–ҘеҶІзӘҒ
е°Ҫз®ЎеҰӮжӯӨејәи°ғвҖңдәІдәІвҖқпјҢдҪҶжҲ‘们еҝ…йЎ»жүҝи®ӨеңЁзҺ°д»ЈзӨҫдјҡйҮҢпјҢвҖңдёӘдҪ“вҖқдҫқ然жңүе®ғйқһеёёз§ҜжһҒзҡ„дёҖйқўгҖӮ然иҖҢпјҢеҚ•зәҜи®ІвҖңдёӘдҪ“вҖқд№ҹжҳҜжңүдёҖе®ҡй—®йўҳзҡ„пјҢвҖңзҺ°д»Јз—…вҖқдёӯзҡ„ж¶ҲжһҒгҖҒиҷҡж— дё»д№үгҖҒзӣёеҜ№дё»д№үзӯүпјҢйғҪдёҺиҝҮдәҺејәи°ғдёӘдҪ“жңүе…ігҖӮе°ұеғҸи®ІеҲ°вҖң家вҖқпјҢе…¶е®һд№ҹжҳҜдёӨз§Қжғ…ж„ҹпјҢдёҖз§ҚжҳҜдәІеҲҮзҡ„гҖҒжё©жҡ–зҡ„пјҢдёҖз§ҚжҳҜиЎҖзјҳзҡ„гҖҒзӢӯйҡҳзҡ„гҖҒеЁҒжқғзҡ„гҖӮеӣ жӯӨпјҢжҲ‘еҶҷгҖҠи®ә家гҖӢиҝҷжң¬д№ҰжңүдёҖдёӘеүҜж ҮйўҳпјҢеҸ«дҪңвҖңдёӘдҪ“дёҺдәІдәІвҖқпјҢиҝҷе°ұдёҚеҗҢдәҺдј з»ҹж–ҮеҢ–жүҖејәи°ғзҡ„вҖңдәІдәІдёҺе°Ҡе°ҠвҖқгҖӮеӣ дёәвҖңдәІдәІе°Ҡе°ҠвҖқејәи°ғзҡ„жҳҜзӯүзә§жҖ§пјҢеҢ…жӢ¬иғҢеҗҺзҡ„зӨјеҲ¶пјҢиҝҷ并дёҚжҳҜдёҖдёӘе»әз«ӢеңЁзҺ°д»Јж„Ҹд№үдёҠдәәдәәе№ізӯүзҡ„еҲ¶еәҰгҖӮ
зҺ°д»ЈзӨҫдјҡеҜ№жқғеҲ©гҖҒе№ізӯүгҖҒиҮӘз”ұгҖҒд»·еҖјгҖҒе°ҠдёҘжҳҜжңүй«ҳеәҰи®ӨеҗҢзҡ„пјҢжІЎжңүдәәдјҡи§үеҫ—иҮӘе·ұз”ҹжқҘжҜ”еҲ«дәәдҪҺдёҖзӯүпјҢиҝҷдёҖеүҚжҸҗжңүе…¶ж„Ҹд№үд»·еҖје’ҢзҺ°е®һжҖ§гҖӮдҪҶеҗҢж—¶пјҢжҲ‘们еҸ‘зҺ°вҖңдёӘдҪ“вҖқжҳҜжңүеҫҲеӨ§зјәеӨұзҡ„пјҢжІЎжңүе’Ңи°җ家еәӯж”Ҝж’‘зҡ„вҖңдёӘдҪ“вҖқдјҡеҸ‘з”ҹеҗ„з§ҚеҒҸе·®пјҢеӣ жӯӨе°ұйңҖиҰҒжҲ‘们зҡ„дёҖдәӣдј з»ҹж–ҮеҢ–иө„жәҗжқҘж”Ҝж’‘гҖҒеҸ‘жү¬пјҢжҜ”еҰӮиҜҙвҖңдәІдәІвҖқ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жҲ‘们д№ҹеә”иҜҘзңӢеҲ°вҖңдәІдәІвҖқзҡ„еұҖйҷҗжҖ§гҖӮеңЁдј з»ҹзӨҫдјҡйҮҢпјҢеңЁд»Ҙдј з»ҹжқ‘зӨҫдёәдёӯеҝғзҡ„зҶҹдәәзӨҫдјҡйҮҢпјҢвҖңдәІдәІвҖқиө·зҡ„дҪңз”ЁеҫҲеӨ§пјҢдҪҶжҳҜеңЁе…·жңүй«ҳеәҰжөҒеҠЁжҖ§зҡ„зҺ°д»ЈзӨҫдјҡйҮҢпјҢеҸӘжңүеңЁе……еҲҶе°ҠйҮҚдёӘдҪ“д»·еҖјзҡ„еүҚжҸҗдёӢпјҢжҲ‘们жүҚиғҪжқҘи°ҲвҖңдәІдәІвҖқеҰӮдҪ•еҸ‘жҢҘдҪңз”ЁгҖӮ
жңүдәәиҙЁз–‘пјҢдёӯеӣҪдәәи®ІжҺЁе·ұеҸҠдәәпјҢдҪҶеҘҪеғҸжҲ‘们еҸӘиғҪвҖңжҺЁвҖқеҲ°иҮӘе·ұдәәпјҢеҲ«дәәе°ұжҺЁдёҚиҝҮеҺ»дәҶгҖӮдј з»ҹж–ҮеҢ–жҳҜжҖҺд№Ҳи§ЈеҶіиҝҷдёӘй—®йўҳзҡ„пјҹйӮЈе°ұжҳҜйҖҡиҝҮвҖңж•ҷеҢ–вҖқжқҘе…ӢжңҚиҝҷз§ҚзӢӯйҡҳжҖ§гҖӮдёҫдёӘдҫӢеӯҗжқҘи®ІпјҢжҜ”еҰӮвҖңд»ҒзҲұвҖқзҡ„зӯүе·®пјҢ儒家зү№еҲ«ејәи°ғвҖңзҲұжңүзӯүе·®вҖқпјҢдҪҶеҸҲзү№еҲ«ејәи°ғвҖңжҺЁе·ұеҸҠдәәвҖқгҖӮиҝҷйҮҢзҡ„вҖңжҺЁеҸҠвҖқзү№еҲ«йҮҚиҰҒпјҢе®ғеҸҜд»Ҙд»ҺвҖңиҖҒеҗҫиҖҒд»ҘеҸҠдәәд№ӢиҖҒпјҢе№јеҗҫе№јд»ҘеҸҠдәәд№Ӣе№јвҖқзҡ„вҖңдәІдәІвҖқдёҖзӣҙвҖңжҺЁеҸҠвҖқеҲ°вҖңж°‘иғһзү©дёҺвҖқпјҢд№ҹе°ұжҳҜжіӣзҲұеӨ©дёӢгҖӮдҪҶиҝҷдёӘзҲұжҳҜжңүзӯүе·®зҡ„пјҢд№ҹе°ұжҳҜзҲұзҡ„вҖңжҺЁеҸҠвҖқ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е°ұжңүдёҖдёӘдёҚж–ӯйҖ’еҮҸзҡ„иҝҮзЁӢгҖӮиҖҢеҸӨдәәи§ЈеҶіиҝҷдёҖй—®йўҳпјҢеҫҲйҮҚиҰҒзҡ„зҺҜиҠӮе°ұеңЁдәҺвҖңж•ҷеҢ–вҖқпјҢйҖҡиҝҮж•ҷиӮІдёҚж–ӯең°жү©еӨ§гҖҒжү©е……гҖӮ
еҗҢж ·жҳҜеҜ№дәҺвҖңд»ҒзҲұвҖқзҡ„еҲҶжһҗпјҢеӨ§еҚ«В·дј‘и°ҹгҖҒдәҡеҪ“В·ж–ҜеҜҶеҜ№вҖңзҲұжңүзӯүе·®вҖқе°ұз»ҷеҮәдәҶеҸҰеӨ–дёҖдёӘж–№жЎҲгҖӮ他们и®ӨдёәвҖңзҲұжңүзӯүе·®вҖқпјҢеӣ жӯӨе°ұжҳҜдёҚе……еҲҶзҡ„пјҢдәә们иҰҒжңүдёҖз§Қдәәдёәзҡ„еҫ·жҖ§вҖ”вҖ”жӯЈд№үпјҢд№ҹе°ұжҳҜжі•еҫӢпјҢжқҘе№ізӯүеҜ№еҫ…жҜҸдёҖдёӘдәәпјҢд»ҘжӯӨжқҘејҘиЎҘвҖңд»ҒзҲұвҖқиҝҷз§ҚиҮӘ然еҫ·жҖ§зҡ„зјәеӨұгҖӮиҝҷжҳҜдёҚеҗҢзҡ„еҺҶеҸІгҖҒж–ҮеҢ–з»ҷеҮәзҡ„дёҚеҗҢи·Ҝеҫ„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еҶңжқ‘讲究вҖңеүҚдёҚж ҪжЎ‘гҖҒеҗҺдёҚж ҪжҹівҖқдёӢеҚҠеҸҘжүҚжҳҜзІҫеҚҺпјҢиҜҙе°Ҫз”ҹжҙ»жҷәж…§пјҒ
- з”ҹжҙ»дёӯйҒҮеҲ°е°ҸдәәжҖҺд№ҲеҠһй¬ји°·еӯҗжҺҢжҸЎиҝҷ3жӢӣпјҢ让他们жҲҗдёәдҪ зҡ„еҠ©еҠӣ
- иҖҒдәәзӢ¬иҮӘз”ҹжҙ»еңЁеұұйҮҢпјҢд»–з”Ё40е№ҙзҡ„ж—¶й—ҙпјҢжҠҠжӮ¬еҙ–еҸҳжҲҗдёҖдёӘе·ЁеӨ§иүәжңҜе“Ғ
- еҒҡдәӢдёҚжҳҺжҷәпјҢз”ҹжҙ»дёҚеҰӮж„Ҹ
- е”җжңқз»ҸжөҺз№ҒиҚЈгҖҒиҙёжҳ“е•Ҷе“Ғз№ҒеӨҡпјҢдёәдҪ•й…’еҷЁжҲҗдёәж—Ҙеёёз”ҹжҙ»зҡ„ж Үй…Қпјҹ
- 笔记·еӨ©зҝ»ең°иҰҶд№ҹиҰҒеҘҪеҘҪз”ҹжҙ»
- гҖҠжӮҜеҶңгҖӢдҪңиҖ…пјҡеҗғеҫ—вҖңиӢҰдёӯиӢҰвҖқзҡ„дәәпјҢеӨ§еӨҡжҜҒеңЁдәҶвҖңдәәдёҠдәәвҖқзҡ„з”ҹжҙ»
- дёҮдёҖеҸҳжңүй’ұдәҶпјҢжҲ‘иҜҘйҖүжӢ©й«ҳдәҺз”ҹжҙ»зҡ„иүәжңҜпјҢиҝҳжҳҜйҖүжӢ©иҙҙиҝ‘з”ҹжҙ»зҡ„и®ҫи®Ў
- еҲӣж„ҸжқҘжәҗдәҺз”ҹжҙ»пјҢиүәжңҜжқҘжәҗдәҺз”ҹжҙ»
- еӣӣеҚҒдёүе№ҙйҖЁйјҺй“ӯж–ҮйҮҢзҡ„з§ҳеҜ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