зҝ»жЎҲ|д»–з”Ёж•ҙдёӘз”ҹе‘ҪжқҘеҶҷдҪңпјҢдёәиў«еҶӨжһүзҡ„йҷ¶жёҠжҳҺвҖңзҝ»жЎҲвҖқ
дёҖд№қе…ӯдёҖе№ҙжң«пјҢгҖҠдәәж°‘ж–ҮеӯҰгҖӢеҸ‘иЎЁдәҶйҷҲзҝ”й№Өзҡ„гҖҠйҷ¶жёҠжҳҺеҶҷгҖҲжҢҪжӯҢгҖүгҖӢпјҢдҪҝжІүеҜӮиҗ§жқЎзҡ„еҺҶеҸІе°ҸиҜҙеҲӣдҪңзғӯй—№иө·жқҘпјҢд»…дёҖе№ҙеӨҡж—¶й—ҙдҫҝжңүиҝ‘еӣӣеҚҒзҜҮеҺҶеҸІе°ҸиҜҙеҶ’еҮәж–ҮеқӣгҖӮеӣ жӯӨйҷҲзҝ”й№ӨеҶҷзҡ„гҖҠйҷ¶жёҠжҳҺеҶҷгҖҲжҢҪжӯҢгҖүгҖӢиў«и§ҶдёәеҪ“ж—¶еҺҶеҸІе°ҸиҜҙзҡ„вҖңе…Ҳй©ұвҖқгҖӮеҺҶеҸІе°ҸиҜҙеҺҶжқҘиў«з§°дёәвҖңиұЎеҫҒжҖ§вҖқзҡ„еҸҷиҝ°пјҢжҳҜвҖңеҖҹеҸӨдәәзҡ„й…’жқҜпјҢжөҮдҪң家иҮӘе·ұиғёдёӯзҡ„еқ—еһ’вҖқгҖӮеҪ“然пјҢе®ғдёҚжҳҜе°ҶеҺҶеҸІдәӢ件зӣҙжҺҘеҜ№еә”еҲ°зҺ°е®һж”ҝжІ»пјҢжҒ°жҒ°зӣёеҸҚпјҢе®ғдёҖзӣҙдҝқжҢҒеҜ№ж”ҝжІ»зҡ„з–ҸзҰ»пјҢжӣҙеӨҡжҳҜдёҖз§Қж–ҮеҢ–иұЎеҫҒпјҢжҜ”еҰӮгҖҠйҷ¶жёҠжҳҺеҶҷгҖҲжҢҪжӯҢгҖүгҖӢпјҢжӣҙеӨҡең°жҳҜеҜ№зҹҘиҜҶиҖ…зІҫзҘһеҶ…йқўзҡ„дёҖз§ҚжҺўзҙўгҖӮиҖҢд№ӢеҗҺеҮәзүҲзҡ„й•ҝзҜҮеҺҶеҸІе°ҸиҜҙгҖҠжқҺиҮӘжҲҗгҖӢпјҢиў«жҲҸжӣ°пјҡвҖңй«ҳеӨ«дәәеӨӘй«ҳпјҢзәўеЁҳеӯҗеӨӘзәўпјҢжқҺиҮӘжҲҗжҲҗдёәж— дә§йҳ¶зә§йўҶиў–гҖӮвҖқиҜ»иҖ…е’ҢиҜ„и®әз•ҢеҜ№йҷҲзҝ”й№ӨдҪңе“ҒзғӯзғҲиөһиӘүпјҢиҖҢеҜ№гҖҠжқҺиҮӘжҲҗгҖӢзҡ„и°Ёж…Һе’ҢеҶ·жј пјҢйҷӨдәҶдёҺдҪңе“Ғзҡ„жҖқжғіжҖ§е’ҢиүәжңҜжҖ§еҸҠе®ЎзҫҺзӣёе…іпјҢжҖ•д№ҹдёҺдҪңиҖ…зҡ„ж–ҮеҢ–дәәж јиҜ„д»·еҲҶдёҚејҖгҖӮж–ҮеӯҰд№ӢеӨ–зҡ„дёңиҘҝпјҢж°ёиҝңе·ҰеҸідёҚдәҶж–ҮеӯҰгҖӮ
йҷҲзҷҪе°ҳжҺЁеҙҮйҷҲзҝ”й№ӨйҒ“пјҡвҖңдёҖиҲ¬дҪң家жҳҜз”Ёзәёе’Ң笔еҶҷдҪңзҡ„пјҢйқ©е‘ҪдҪң家жҳҜз”ЁиЎҖе’ҢиӮүеҶҷдҪңзҡ„пјҢзҝ”й№ӨжҳҜз”Ёд»–ж•ҙдёӘз”ҹе‘ҪжқҘеҶҷдҪңзҡ„пјҢжүҖд»ҘжҲ‘з§°д»–дёәзңҹжӯЈзҡ„дҪң家гҖӮеӣ дёәпјҢд»–йҰ–е…ҲжҳҜдёҖдёӘзңҹжӯЈзҡ„дәәгҖӮвҖқжҳҜзҡ„пјҢйҷҲзҝ”й№Өе…Ҳз”ҹжҳҜз”Ёз”ҹе‘ҪзҙўзҗҙеҘҸжӣІпјҢеҘҸе“ҚеҚғеҸӨз»қе”ұгҖҠйҷ¶жёҠжҳҺеҶҷгҖҲжҢҪжӯҢгҖүгҖӢе’ҢгҖҠе№ҝйҷөж•ЈгҖӢгҖӮ

ж–Үз« жҸ’еӣҫ
в–ҢйҷҲзҝ”й№Өе’ҢеҰ»еӯҗзҺӢиҝӘиӢҘ
вҖңжө…иҚүвҖқдёҺвҖңжІүй’ҹвҖқ
йҷҲзҝ”й№ӨжҜ”жІҲд»Һж–ҮеӨ§дёҖеІҒпјҢдёҠдё–зәӘдәҢеҚҒе№ҙд»ЈеҲқпјҢдёӨдәәзӣёиҜҶеңЁеҢ—дә¬гҖӮжІҲд»Һж–Үе…Ҳз”ҹеңЁгҖҠеҝҶзҝ”й№ӨгҖӢдёҖж–ҮдёӯеҶҷйҒ“пјҢжІҲд»Һж–ҮдәҺдёҖд№қдәҢдәҢе№ҙеӯӨиә«д»Һж№ҳиҘҝеҮӨеҮ°жқҘеҲ°еҢ—дә¬еҚҠе·ҘеҚҠиҜ»пјҢз”ҹжҙ»жё…иӢҰпјҢдёәдәҶз”ҹи®ЎпјҢдёҖд№қдәҢдә”е№ҙжқҘеҲ°еҢ—дә¬йҰҷеұұж…Ҳе№јйҷўеҒҡдәҶдёҖдёӘе°ҸиҒҢе‘ҳпјҢдҪҸеңЁйҰҷеұұйҘӯеә—еүҚеұұй—Ёж–°е®ҝиҲҚйҮҢгҖӮвҖңеҲ«зҡ„иҒҢе‘ҳеӣ дёәдёҠдёӢжһҒдёҚж–№дҫҝпјҢеӨҡдёҚд№җж„Ҹжҗ¬еҲ°йӮЈдёӘе®ҝиҲҚеҺ»гҖӮжҲ‘з®—жҳҜ第дёҖдёӘжҗ¬иҝӣеҺ»зҡ„жҙ»дәәгҖӮзҝ”й№Өд»ҺжҲ‘зҡ„дҝЎдёӯзҹҘйҒ“иҝҷдёӘж–°дҪҸеӨ„еҘҮзү№зҺҜеўғеҗҺпјҢдёҚд№…е°ұе……ж»Ўе…ҙи¶ЈпјҢйӘ‘дәҶжҜӣй©ҙеҲ°йўҗе’ҢеӣӯпјҢжҚўдәҶдёҖеҢ№е°ҸжҜӣй©ҙпјҢдёҠйҰҷеұұжқҘеҜ»е№Ҫи®ҝиғңпјҢжҲҗдәҶжҲ‘дҪҸеӨ„зҡ„е®ўдәәдәҶгҖӮеңЁйӮЈз®ҖйҷӢе®ҝиҲҚдёӯпјҢе’ҢжҲ‘еҗҢиҝҮдәҶдёүеӨ©дёҚжҳ“еҝҳеҚҙзҡ„ж—ҘеӯҗвҖҰвҖҰвҖқ
йҷҲзҝ”й№ӨжҳҜйҮҚеәҶдәәпјҢдәҢеҚҒе№ҙд»Је°ұеҲ°еҢ—дә¬е’ҢдёҠжө·еҸӮдёҺз»„з»Үж–ҮеӯҰзӨҫеӣўжө…иҚүзӨҫе’ҢжІүй’ҹзӨҫпјҢзӨҫе‘ҳжңүжһ—еҰӮзЁ·гҖҒйҷҲзӮңи°ҹгҖҒиөөжҷҜж·ұгҖҒеҶҜиҮігҖҒеҶҜж–ҮзӮізӯүпјҢеӨҡдёәеӣӣе·қзұҚгҖӮйІҒиҝ…и®ӨдёәпјҡвҖңжө…иҚүзӨҫвҖқе…¶е®һд№ҹжҳҜвҖңдёәиүәжңҜиҖҢиүәжңҜвҖқзҡ„дҪң家еӣўдҪ“пјҢдҪҶ他们зҡ„еӯЈеҲҠпјҢжҜҸдёҖжңҹйғҪжҳҫзӨәзқҖеҠӘеҠӣпјӣеҗ‘еӨ–пјҢеңЁж‘„еҸ–ејӮеҹҹеҪұе“ҚпјҢеҗ‘еҶ…жҢ–жҺҳиҮӘе·ұзҡ„зҒөйӯӮпјҢиҰҒеҸ‘и§ҒеҝғйҮҢзҡ„зңјзқӣе’Ңе–үиҲҢпјҢжқҘеҮқи§Ҷиҝҷдё–з•ҢпјҢе°Ҷзңҹе’ҢзҫҺжӯҢе”ұз»ҷеҜӮеҜһзҡ„дәә们гҖӮвҖқйІҒиҝ…еҜ№вҖңжІүй’ҹзӨҫвҖқиҜ„д»·д№ҹеҫҲй«ҳпјҡвҖңжІүй’ҹзӨҫзЎ®жҳҜдёӯеӣҪзҡ„жңҖеқҡйҹ§гҖҒжңҖиҜҡе®һпјҢжҢЈжүҺеҫ—жңҖд№…зҡ„еӣўдҪ“вҖқпјҲгҖҠгҖҲдёӯеӣҪж–°ж–ҮеӯҰеӨ§зі»гҖүе°ҸиҜҙдәҢйӣҶеәҸгҖӢпјүгҖӮйІҒиҝ…иҝҷд№Ҳй«ҳеәҰиҜ„д»·дёҖдёӘж–ҮеӯҰзӨҫеӣўпјҢжҳҜжһҒдёәе°‘и§Ғзҡ„гҖ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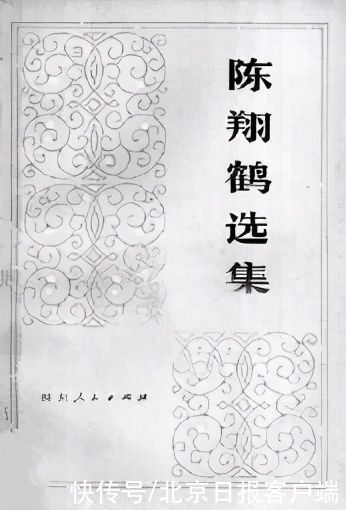
ж–Үз« жҸ’еӣ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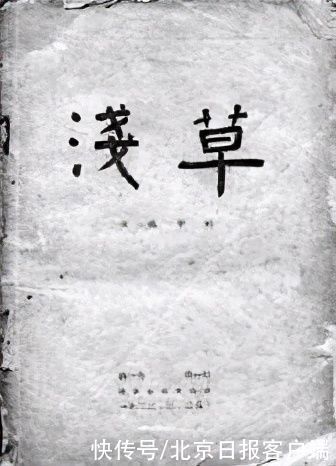
ж–Үз« жҸ’еӣҫ
в–ҢйҷҲзҝ”й№ӨеҸӮдёҺзҡ„гҖҒжҲҗз«ӢдәҺдёҠдё–зәӘ20е№ҙд»Јзҡ„жө…иҚүзӨҫеҮәзүҲеҲҠзү©
дҪңдёәжө…иҚүзӨҫе’ҢжІүй’ҹзӨҫзҡ„дё»еҠӣпјҢйҷҲзҝ”й№ӨжӣҫеҶҷеҮәгҖҠжӮјвҖ”вҖ”гҖӢгҖҠдёҚе®үе®ҡзҡ„зҒөйӯӮгҖӢпјҢ收е…Ҙе°ҸиҜҙйӣҶгҖҠдёҚе®үе®ҡзҡ„зҒөйӯӮгҖӢпјҢе…¶е°ҸиҜҙдёӯпјҢеӨ§еӨҡжҳҜдёҖдәӣеҝ§йғҒжӮІи§ӮиҖҢеҸҲиӢҰиӢҰжҢЈжүҺзҡ„зҹҘиҜҶйқ’е№ҙпјҢиҝҷдәӣдәәзү©йғҪеёҰжңүйҷҲзҝ”й№ӨиҮӘиә«зҡ„жҠ•еҪұгҖӮдёҖд№қдёүе…«е№ҙпјҢйҷҲзҝ”й№ӨеҠ е…ҘдәҶдёӯеӣҪе…ұдә§е…ҡпјҢдёҖд№қдә”дёүе№ҙи°ғеҲ°еҢ—дә¬пјҢд»»дёӯеӣҪдҪңеҚҸзҗҶдәӢгҖҒеҸӨе…ёж–ҮеӯҰйғЁеүҜйғЁй•ҝпјҢеҗҺеҸҲи°ғеҲ°зӨҫ科йҷўпјҢеҶҚеҲ°гҖҠе…үжҳҺж—ҘжҠҘВ·еүҜеҲҠгҖӢд»»гҖҠж–ҮеӯҰйҒ—дә§гҖӢдё“ж Ҹдё»зј–гҖҒгҖҠж–ҮеӯҰз ”з©¶еӯЈеҲҠгҖӢдё»зј–гҖӮ
йҷҲзҝ”й№ӨеҲҡи°ғеҲ°еҢ—дә¬пјҢеҸҲдёҺжІҲд»Һж–Үи°ӢйқўпјҢзҷҪдә‘иӢҚзӢ—пјҢе·ІиҝҮдёүеҚҒдёӘе№ҙеӨҙпјҢдәҢдәәжғіиө·йҰҷеұұеҫҖдәӢпјҢж„ҹж…ЁиүҜеӨҡгҖӮйҷҲзҝ”й№Өиҝҳжё…жҷ°ең°и®°еҫ—пјҢжІҲд»Һж–ҮеңЁдёҖжЈөеҸӨжқҫеүҚпјҢжҠұдәҶдёҖйқўзҗөзҗ¶пјҢдёәд»–еј№иҝҮгҖҠжўөзҺӢе®«гҖӢжӣІеӯҗгҖӮжҲ–и®ёеӣ дёәжІҲд»Һж–ҮеҲқеӯҰпјҢд»–еҪ“йқўз¬‘жӣ°пјҡвҖңеј№еҫ—зңҹ蹩и„ҡпјҢеҗ¬жқҘдёҚжҲҗдёӘи…”и°ғпјҢиҝңдёҚеҰӮйҷ¶жҪңжҢҘвҖҳж— ејҰзҗҙвҖҷжңүж„ҸжҖқвҖҰвҖҰвҖқдёӨдҪҚд№Ұз”ҹзәҜзңҹзҺҮзӣҙзҡ„йЈҺи°Ҡе№із”ҹпјҢи®©жҲ‘们зңӢеҲ°д»–们ж–ҮеҢ–зҒөйӯӮзҡ„е№ІеҮҖгҖӮжӣҙжңүи¶Јзҡ„жҳҜпјҢжІҲд»Һж–Үе…Ҳз”ҹеҫҲж—©е°ұиҝңзҰ»дәҶж–ҮеӯҰпјҢгҖҠжўөзҺӢе®«гҖӢд№ҹжңӘжҲҗжӣІи°ғпјҢдҪҶйҷҲзҝ”й№ӨеҚҙд»Ҙз”ҹе‘ҪзҙўзҗҙеҘҸжӣІпјҢдёәйҷ¶жҪңеј№иө·еҚғеҸӨз»қе”ұгҖҠйҷ¶жёҠжҳҺеҶҷгҖҲжҢҪжӯҢгҖүгҖӢе’ҢгҖҠе№ҝйҷөж•ЈгҖӢ
жҺЁиҚҗйҳ…иҜ»
- иҖҒдәәзӢ¬иҮӘз”ҹжҙ»еңЁеұұйҮҢпјҢд»–з”Ё40е№ҙзҡ„ж—¶й—ҙпјҢжҠҠжӮ¬еҙ–еҸҳжҲҗдёҖдёӘе·ЁеӨ§иүәжңҜе“Ғ
- жӯҰжқҫеҲ°еә•жңүеӨҡеҺүе®іпјҹж•ҙдёӘжўҒеұұиғҪжҲҳиғңд»–зҡ„пјҢеҸӘжңүиҝҷдёүдәә
- иЁҖжғ…ж–Үеҫ—зҹҘдә”е№ҙеүҚиў«дј‘ејғзҡ„зҺӢеҰғз”ҹдәҶеҜ№еҸҢз”ҹеӯҗпјҢж•ҙдёӘзҺӢеәңйғҪжІёи…ҫдәҶпјҒ
- жӯӨдәәзІҫйҖҡеҘҮй—ЁйҒҒз”ІпјҢдё»е…¬е…өиҙҘиў«иҝҪжқҖпјҢд»–з”ЁзҹіеӨҙйҳөйҖҖж•Ң
- ж–ҮзҺ©ж ёжЎғж•ҙдёӘзҡ„еҫҲеёёи§ҒпјҢдҪҶжӮЁи§ҒиҝҮеҲҮејҖжқҘзӣҳзҺ©зҡ„еҗ—
- иҘҝжёёжңҖеӨ§зҡ„вҖңеқ‘вҖқиҙ§пјҢж•ҙдёӘиҘҝиЎҢйғҪеңЁеқ‘дәәпјҢеҒҸеҒҸиҝҳжІЎдәәзңӢеҮәпјҒ
- зҺӢеӢғеҺ»йғҠеӨ–иёҸйқ’пјҢеҶҷдёӢдёҖйҰ–иҜ—пјҢејҖзҜҮдёӨеҸҘдҫҝжғҠиүідәҶж•ҙдёӘжҳҘеӨ©
- дёӯеӣҪеҺҶеҸІдёҠжӣҫдёўеӨұжӯӨең°иҝ‘1000е№ҙпјҢд»ҺиҖҢдёўдәҶж•ҙдёӘиҝ‘д»ЈпјҢиҮід»ҠжғӢжғң
- жҳҺжңқ|ж•ҙдёӘжҳҺд»Јеқҗй•Үдә‘еҚ—200еӨҡе№ҙзҡ„вҖңжІҗзҺӢеәңвҖқжҳҜдёӘд»Җд№ҲжқҘеӨҙпјҹ
- дёүеӣҪдёӨжҷӢеҚ—еҢ—жңқ|еӯҷзӯ–и®©еј зә®еҺ»и®ёжҳҢзӮ«иҖҖжүҚеӯҰпјҢеҸӘдёәдәҶдәүдёӘи„ёйқўпјҢеҚҙж•‘дәҶж•ҙдёӘжұҹдё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