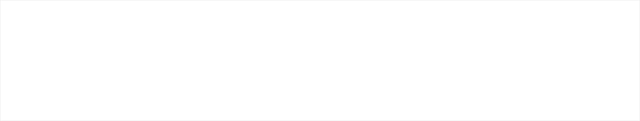еҶҜеҸӢе…°дёҺвҖңжқҺзәҰз‘ҹйҡҫйўҳвҖқ( дәҢ )
еҶҜеҸӢе…°ж•…еұ…зҡ„йӣ•еЎ‘2 еҶҜеҸӢе…°еҜ№вҖңжқҺзәҰз‘ҹйҡҫйўҳвҖқзҡ„еҲқжӯҘеӣһзӯ”еҶҜеҸӢе…°еңЁгҖҠдёәгҖӢж–ҮдёӯжҸҗеҮәдәҶдёәд»Җд№ҲдёӯеӣҪжІЎжңүдә§з”ҹиҝ‘代科еӯҰзҡ„й—®йўҳд№ӢеҗҺ пјҢ з«ӢеҚід»Һе“ІеӯҰдёҠдҪңеҮәдәҶеҲқжӯҘеӣһзӯ” гҖӮ жӯӨеҗҺд»–иҷҪ然没жңүеҶҚдёәжӯӨиҖҢдё“й—ЁеҶҷиҝҮж–Үз« пјҢ дҪҶд»–еҜ№дәҺиҝҷдёҖй—®йўҳеҚҙз»ҷдәҶз»Ҳз”ҹзҡ„е…іжіЁ гҖӮ еңЁд»ҘеҗҺзҡ„е“ІеӯҰеҸІз ”究е’Ңе“ІеӯҰдҪ“зі»зҡ„еҲӣйҖ дёӯ пјҢ д»–йҡҸж—¶жіЁж„Ҹдҝ®жӯЈгҖҒдё°еҜҢе’Ңе®Ңе–„иҮӘе·ұжӣҫз»ҸеҒҡеҮәзҡ„и§ЈйҮҠ гҖӮ иҝҷе°ұдҪҝд»–еҜ№иҝҷдёҖй—®йўҳзҡ„еӣһзӯ”жҳҫзҺ°еҮәдёҖдёӘеҸ‘еұ•зҡ„иҝҮзЁӢ гҖӮеңЁгҖҠдёәгҖӢж–Үдёӯ пјҢ еҶҜеҸӢе…°д»Һдәәзҡ„жҖқжғіеҠЁжңәеҮәеҸ‘ пјҢ жқҘи§ЈйҮҠдёӯеӣҪжІЎжңүдә§з”ҹ科еӯҰзҡ„еҺҹеӣ гҖӮ д»–иҜҙпјҡвҖңең°зҗҶгҖҒж°”еҖҷгҖҒз»ҸжөҺжқЎд»¶йғҪжҳҜеҪўжҲҗеҺҶеҸІзҡ„йҮҚиҰҒеӣ зҙ пјҢ иҝҷжҳҜдёҚжҲҗй—®йўҳзҡ„ пјҢ дҪҶжҳҜжҲ‘们еҝғйҮҢиҰҒи®°дҪҸ пјҢ е®ғ们йғҪжҳҜдҪҝеҺҶеҸІжҲҗдёәеҸҜиғҪзҡ„жқЎд»¶ гҖӮ е®ғ们йғҪжҳҜдёҖеңәжҲҸйҮҢдёҚеҸҜзјәе°‘зҡ„еёғжҷҜ пјҢ иҖҢдёҚжҳҜе®ғзҡ„еҺҹеӣ гҖӮ дҪҝеҺҶеҸІжҲҗдёәе®һйҷ…зҡ„еҺҹеӣ зҡ„жҳҜжұӮз”ҹзҡ„ж„Ҹеҝ—е’ҢжұӮе№ёзҰҸзҡ„ж¬Іжңӣ гҖӮ вҖқжҺҘзқҖд»–иҖғеҜҹдәҶдёӯеӣҪе“ІеӯҰдёӯе…ідәҺе–„е’Ңе№ёзҰҸзҡ„и§Ӯеҝө гҖӮ д»–жҢҮеҮә пјҢ еңЁдёӯеӣҪе“ІеӯҰзҡ„жәҗеӨҙ пјҢ жӣҫеҗҢж—¶еҮәзҺ°дәҶдёүз§ҚдёҚеҗҢзҡ„зҗҶжғізұ»еһӢ пјҢ еҚіе„’家гҖҒйҒ“家е’Ң墨家 гҖӮ е…¶дёӯ пјҢ йҒ“е®¶дё»еј еӨҚеҪ’иҮӘ然 пјҢ и®Өдёәе…ЁиғҪзҡ„вҖңйҒ“вҖқз»ҷдәҲдёҮзү©д»Ҙе…¶иҮӘе·ұзҡ„иҮӘ然 пјҢ еңЁе…¶иҮӘ然дёӯдёҮзү©еҫ—еҲ°иҮӘе·ұзҡ„ж»Ўи¶і гҖӮ еӣ жӯӨ пјҢ дёҮзү©еңЁе…¶иҮӘ然зҠ¶жҖҒдёӯйғҪжҳҜе®Ңе–„зҡ„ пјҢ дёҚйңҖиҰҒдәәдёә пјҢ дәәдёәеҸӘдјҡжү°д№ұиҮӘ然 пјҢ дә§з”ҹз—ӣиӢҰ пјҢ жӯЈжүҖи°“вҖңеҮ«иғ«иҷҪзҹӯ пјҢ з»ӯд№ӢеҲҷеҝ§пјӣй№Өиғ«иҷҪй•ҝ пјҢ ж–ӯд№ӢеҲҷжӮІ гҖӮ ж•…жҖ§й•ҝйқһжүҖж–ӯ пјҢ жҖ§зҹӯйқһжүҖз»ӯ пјҢ ж— жүҖеҺ»еҝ§д№ҹ гҖӮ вҖқеӣ жӯӨдәәжүҖеә”еҪ“еҒҡзҡ„ пјҢ е°ұжҳҜйҒөеҫӘзқҖиҮӘе·ұзҡ„иҮӘ然 пјҢ ж»Ўи¶ідәҺиҮӘе·ұзҡ„е‘Ҫиҝҗ пјҢ иҖҢдёҚеә”еҪ“иҜ•еӣҫеҺ»ж”№йҖ иҮӘ然 пјҢ дёҺе‘ҪиҝҗжҠ—дәү гҖӮ иҝҷе°ұиҰҒжұӮжҲ‘们еҺ»и®ӨиҜҶиҮӘе·ұ пјҢ жҺ§еҲ¶иҮӘе·ұ пјҢ еҗ‘иҮӘе·ұеҺ»жұӮвҖңйҒ“вҖқ пјҢ еӣ дёәвҖңйҒ“вҖқе°ұеңЁжҲ‘们д№Ӣдёӯ гҖӮ дәҺжҳҜдёәйҒ“зҡ„ж–№жі• пјҢ е°ұдёҚжҳҜдәәдёәең°еңЁйҒ“дёҠйқўеҠ дәӣд»Җд№Ҳ пјҢ иҖҢжҳҜжҠҠж—©е·Ідәәдёәең°еҠ еңЁйҒ“дёҠйқўзҡ„дёңиҘҝеҺ»жҺү гҖӮ иҝҷе°ұеҶіе®ҡдәҶйӮЈдәӣиҜ•еӣҫжҺҢжҸЎж”№еҸҳиҮӘ然зҹҘиҜҶзҡ„дәәзҡ„еҠӘеҠӣ пјҢ жҳҜжҜ«ж— д»·еҖјзҡ„ гҖӮ дёҺйҒ“家зӣёеҸҚ пјҢ 墨家еҲҷдё»еј дәәдёә пјҢ е…¶еҹәжң¬и§ӮеҝөжҳҜеҠҹеҲ© пјҢ еҲӨж–ӯдёҖеҲҮзҡ„ж ҮеҮҶеңЁе…¶жҳҜеҗҰжңүз”Ё гҖӮ е…¶жңҖй«ҳзҗҶжғіжҳҜжңүжңҖеӨҡзҡ„дәәеҸЈ пјҢ еҝ…йңҖзҡ„зү©иҙЁиҙўеҜҢ пјҢ дәәж°‘е’Ңи°җзӣёеӨ„ пјҢ зӣёдәІзӣёзҲұ гҖӮ дҪҶз”ұдәҺдәәжҖ§е№¶дёҚе®Ңе–„ пјҢ дәәзұ»еӨӘиҝ‘и§Ҷ пјҢ зңӢдёҚи§ҒиҮӘе·ұзҡ„й•ҝиҝңеҲ©зӣҠ пјҢ еӣ жӯӨиҰҒе®һзҺ°иҝҷдёҖзҗҶжғі пјҢ еҸӘиғҪйқ жқғеЁҒгҖҒйқ ж•ҷиӮІгҖҒйқ дәәдёә гҖӮ еӣ жӯӨеўЁеӯҗж—¶еҲ»еҮҶеӨҮзқҖеҗ‘дёҖеҲҮд»–д»ҘдёәдёҚиғҪдёҺиҙўеҜҢгҖҒдәәеҸЈзҡ„еўһй•ҝзӣёе®№зҡ„дәӢзү©дҪңжҲҳ гҖӮ вҖңеўЁеӯҗзЎ®е®һжҳҜдёҖдҪҚж•ҷеҜјдәә们еңЁеӨ–з•ҢеҜ»жұӮе№ёзҰҸзҡ„е“ІеӯҰ家 гҖӮ д»–дёҚеғҸйҒ“家йӮЈж ·жғі пјҢ д»–дёҚд»ҘдёәдәәеңЁиҮӘ然зҠ¶жҖҒдёӯжңҖе№ёзҰҸ пјҢ дёҚд»ҘдёәдәәйңҖиҰҒеҒҡгҖҒеә”еҪ“еҒҡзҡ„жҳҜеӨҚеҪ’иҮӘ然 пјҢ зӣёеҸҚзҡ„жӯЈжҳҜиҰҒж‘Ҷи„ұиҮӘ然вҖқ пјҢжүҖд»Ҙ墨家зҡ„зІҫзҘһжҳҜ科еӯҰзҡ„ гҖӮ 儒家еҲҷжҳҜеҜ№йҒ“家е’Ң墨家зҡ„и°ғе’Ң пјҢ дё»еј дёӯйҒ“ гҖӮ дҪҶжҳҜеңЁеӯ”еӯҗд№ӢеҗҺ пјҢ 儒家еҚҙеҲҶжҲҗдәҶдёӨжҙҫ гҖӮ д»ҘиҺ·еҫ—儒家жӯЈз»ҹең°дҪҚиў«и§Ҷдёәеӯ”еӯҗеҗҲ法继жүҝдәәзҡ„еӯҹеӯҗдёәд»ЈиЎЁзҡ„дёҖжҙҫ пјҢ жҜ”иҫғжҺҘиҝ‘иҮӘ然иҝҷдёҖз«ҜпјӣеҸҰдёҖжҙҫд»ҘиҚҖеӯҗдёәд»ЈиЎЁ пјҢ жҜ”иҫғйқ иҝ‘дәәдёәиҝҷдёҖз«Ҝ гҖӮ еӯҹеӯҗдё»еј дәәжҖ§жң¬е–„ пјҢ еӣ жӯӨдәәеә”еҪ“жұӮе…¶вҖңеңЁжҲ‘иҖ…вҖқ пјҢ иҖҢдёҚеә”жҺ§еҲ¶еңЁд»–д№ӢеӨ–зҡ„дёңиҘҝ гҖӮ еӣ дёәдәәзҡ„еҶ…еҝғжңүдёҠеӨ©иөӢдәҲзҡ„еӨ©зҗҶ пјҢ д»–еҸҜд»Ҙд»ҺдёӯиҺ·еҫ—зңҹзҗҶе’Ңе№ёзҰҸ гҖӮ жүҖи°“вҖңдёҮзү©зҡҶеӨҮдәҺжҲ‘зҹЈ пјҢ еҸҚиә«иҖҢиҜҡ пјҢ д№җиҺ«еӨ§з„үвҖқ гҖӮ еҸҜи§Ғ пјҢ жӯЈз»ҹ儒家еҫҲжҺҘиҝ‘йҒ“家 пјҢ иҖҢеҺ»еўЁе®¶з”ҡиҝң гҖӮ вҖңе№ёзҰҸе’ҢзңҹзҗҶйғҪеңЁжҲ‘们еҝғйҮҢ пјҢ еҸӘжңүеңЁжҲ‘们еҝғйҮҢ пјҢ дёҚжҳҜеңЁеӨ–йғЁдё–з•ҢйҮҢ пјҢ жүҚиғҪжұӮеҫ—е№ёзҰҸе’ҢзңҹзҗҶвҖқ гҖӮ иҮӘи®ӨдёәжҳҜ儒家зңҹжӯЈдј дәәзҡ„иҚҖеӯҗ пјҢ еҲҷе®Јз§°дәәжҖ§жҳҜз»қеҜ№зҡ„жҒ¶ пјҢ жүҖд»ҘйңҖиҰҒж”№е–„дәәжҖ§ пјҢ иҰҒз”ЁеҫҒжңҚиҮӘ然жқҘд»ЈжӣҝеӨҚеҪ’иҮӘ然 гҖӮдёҠиҝ°еҗҢж—¶е…ҙиө·зҡ„е„’гҖҒеўЁгҖҒйҒ“дёү家 пјҢ дёәдәҶз”ҹеӯҳ пјҢ еҪјжӯӨй—ҙиҝӣиЎҢдәҶжҝҖзғҲзҡ„ж–—дәү гҖӮ ж–—дәүзҡ„з»“жһңжҳҜ пјҢ еҸҜжҖңзҡ„墨家е®Ңе…ЁеӨұиҙҘ пјҢ дёҚд№…е°ұж°ёиҝңж¶ҲеӨұдәҶпјӣиҖҢ儒家дёӯжҺҘиҝ‘墨家зҡ„иҚҖеӯҗжҖқжғі пјҢ д№ҹжңӘеҫ—еҲ°з»§жүҝе’ҢеҸ‘еұ• пјҢ д»–зҡ„еӯҰиҜҙ пјҢ е’Ңз§ҰзҺӢжңқдёҖиө· пјҢ еҫҲеҝ«иҖҢдё”ж°ёиҝңзҡ„ж¶ҲдәЎдәҶ гҖӮ иҮӘжӯӨд№ӢеҗҺ пјҢ дёӯеӣҪе“ІеӯҰдёӯзҡ„вҖңдәәдёәвҖқи·ҜзәҝеҶҚд№ҹжІЎжңүеҮәзҺ°дәҶ гҖӮдҪӣж•ҷзҡ„дј дәәжҳҜеӨ–жқҘж–ҮеҢ–еҜ№дёӯеӣҪжң¬еңҹж–ҮеҢ–зҡ„第дёҖж¬Ўе…Ҙдҫө пјҢ дҪҶдҪӣж•ҷйқһдҪҶжІЎжңүж”№еҸҳвҖңиҮӘ然вҖқеһӢе“ІеӯҰдё»е®°дёӯеӣҪжҖқжғізҡ„жІүеҜӮеұҖйқў пјҢ еҸҚиҖҢдҪҝеҫ—е®ғзҡ„еһ„ж–ӯең°дҪҚжӣҙеҠ зЁіеӣә гҖӮ еӣ дёәдҪӣж•ҷиҷҪдёҚеҗҢдәҺ儒家е’ҢйҒ“家 пјҢ дҪҶжң¬иҙЁдёҠд№ҹеұһдәҺжһҒз«ҜвҖңиҮӘ然вҖқеһӢзҡ„е“ІеӯҰ пјҢ е®ғеңЁдёӯеӣҪз«ҷзЁіи„ҡи·ҹеҗҺ пјҢ дҫҝе’Ң儒家гҖҒйҒ“家дёҖиө·зӣҳиёһеңЁдёӯеӣҪдәәзҡ„жҖқжғіж·ұеӨ„ пјҢ дҪҝеҫ—дёӯеӣҪдәәзҡ„еҝғзҒөй•ҝжңҹеҫҳеҫҠдәҺе„’гҖҒйҮҠгҖҒйҒ“д№Ӣй—ҙ гҖӮеҲ°е®Ӣжңқж—¶ пјҢ е„’гҖҒйҮҠгҖҒйҒ“иў«дёҖдәӣж–°зҡ„еӨ©жүҚдәәзү©еҗҲдёүдёәдёҖ пјҢ дәҺжҳҜвҖң新儒家вҖқдҫҝзҷ»дёҠдәҶеҺҶеҸІиҲһеҸ° пјҢ ејҖе§Ӣдё»е®°дёӯеӣҪдәәзҡ„еҝғзҒө гҖӮ 新儒家дёҚеҗҢдәҺеҺҹжқҘзҡ„儒家 гҖӮ еҺҹжқҘзҡ„儒家и®Өдёә пјҢ дәәжҖ§иҷҪ然жҳҜе–„зҡ„ пјҢ дҪҶе…¶е–„еҸӘдёҚиҝҮжҳҜдёӘиҗҢиҠҪ пјҢ жҳҜдёӘвҖңз«ҜвҖқ гҖӮ иҖҢдё” пјҢ дәәжҖ§дёӯйҷӨдәҶе–„зҡ„жҲҗд»Ҫд№ӢеӨ– пјҢ иҝҳжңүдәӣе…¶д»–жҲҗд»Ҫ пјҢ еҚідәәж¬І пјҢ иҝҷдәӣжҲҗд»Ҫжң¬иә«ж— жүҖи°“е–„жҒ¶ пјҢ дҪҶиӢҘдёҚйҖӮеҪ“жҺ§еҲ¶ пјҢ е°ұдјҡйҖҡеҗ‘жҒ¶ пјҢ еӣ жӯӨдәәз”ҹжқҘ并дёҚжҳҜе®Ңе–„зҡ„ пјҢ еҸӘжңүеҶ…еҝғзҡ„зҗҶжҖ§е®Ңе…ЁеҸ‘еұ•дәҶ пјҢ дҪҺзә§зҡ„ж¬Іжңӣе…ЁйғЁж¶ҲйҷӨдәҶ пјҢ жүҚиғҪжҲҗдёәе®Ңдәә гҖӮ иҖҢ新儒家еҚҙи®Өдёә пјҢ дәәз”ҹжқҘе°ұжҳҜе®Ңе–„зҡ„ пјҢ дәәзҡ„еҝғзҒөиҷҪ然дёәдәәж¬ІжүҖи”Ҫ пјҢ дҪҶеҸӘиҰҒжё…йҷӨдәҶиҝҷдәӣдәәж¬І пјҢ зңҹжӯЈзҡ„еҝғзҒөе°ұдјҡеҰӮй’»зҹіиҲ¬иҮӘж”ҫе…үиҠ’ гҖӮ еӣ жӯӨ пјҢ дәәжүҖеә”иҜҘеҒҡзҡ„ пјҢ е°ұжҳҜи®ӨиҜҶе’ҢжҺ§еҲ¶иҮӘе·ұзҡ„еҝғзҒө пјҢ е°ұжҳҜеҺ»дәәж¬Ід»ҘеӯҳеӨ©зҗҶ пјҢ д»ҘжҲҗдёәеңЈдәә пјҢ д»ҘиҺ·еҫ—жңҖеӨ§зҡ„е№ёзҰҸ гҖӮеңЁиҖғеҜҹдәҶжҢҮеҜјдёӯеӣҪеҝғзҒөзҡ„зҗҶжғід№ӢеҗҺ пјҢ еҶҜеҸӢе…°жҢҮеҮәпјҡвҖңдҪ•и°“е–„ пјҢ дёӯеӣҪзҡ„и§Ӯеҝөе°ұжҳҜеҰӮжӯӨ гҖӮ вҖҰвҖҰдёӯеӣҪ пјҢ иҮӘд»Һд»–зҡ„ж°‘ж—ҸжҖқжғідёӯвҖҳдәәдёәвҖҷи·Ҝзәҝж¶ҲдәЎд№ӢеҗҺ пјҢ е°ұд»Ҙе…ЁйғЁзІҫзҘһеҠӣйҮҸиҮҙеҠӣдәҺеҸҰдёҖжқЎи·Ҝзәҝ пјҢ иҝҷе°ұжҳҜ пјҢ зӣҙжҺҘең°еңЁдәәеҝғд№ӢеҶ…еҜ»жұӮе–„е’Ңе№ёзҰҸ гҖӮ вҖқ еңЁиҝҷж ·дёҖз§Қе№ёзҰҸи§Ӯзҡ„ж”Ҝй…Қд№ӢдёӢ пјҢ 科еӯҰжҳҜж— жі•дә§з”ҹзҡ„ пјҢ еӣ дёә科еӯҰзҡ„з”ЁеӨ„ пјҢ жҢүз…§з¬ӣеҚЎе°”е’Ңеҹ№ж №зҡ„иҜҙжі• пјҢ е°ұжҳҜдёәдәҶзЎ®е®һжҖ§е’ҢеҠӣйҮҸ пјҢ д№ҹе°ұжҳҜдёәдәҶи®ӨиҜҶиҮӘ然е’ҢжҺ§еҲ¶иҮӘ然 гҖӮ дёәдәҶзЎ®е®һжҖ§ пјҢ иҰҒи®ӨиҜҶиҮӘ然 пјҢ е°ұйңҖиҰҒд»Һзү©еҮәеҸ‘ пјҢ з ”з©¶иҮӘ然з•Ң пјҢ 并еңЁиҝҷдёҖиҝҮзЁӢдёӯ пјҢ е…»жҲҗзІҫзЎ®гҖҒдёҘеҜҶзҡ„жҖқз»ҙд№ жғҜ гҖӮ иҖҢдёӯеӣҪзҡ„жҖқжғіеҚҙжҳҜд»Һеҗ„дәәиҮӘе·ұзҡ„еҝғзҒөеҮәеҸ‘ пјҢ 他们еёҢжңӣзҹҘйҒ“зҡ„еҸӘжҳҜ他们иҮӘе·ұ пјҢ еӣ жӯӨеҸӘиҰҒиҮӘе·ұдҪ“йӘҢе°ұеӨҹдәҶ пјҢ ж— йЎ»иҜҒжҳҺ пјҢ дёҚйңҖиҰҒ科еӯҰзҡ„жҖқз»ҙж–№жі• гҖӮ 他们еҗҢж ·дёҚйңҖиҰҒ科еӯҰзҡ„еҠӣйҮҸ пјҢ еӣ дёә他们еёҢжңӣеҫҒжңҚзҡ„д№ҹеҸӘжҳҜ他们иҮӘе·ұ гҖӮ еңЁд»–们зңјдёӯ пјҢ жҷәж…§зҡ„еҶ…е®№дёҚжҳҜзҗҶжҷәзҡ„зҹҘиҜҶ пјҢ жҷәж…§зҡ„еҠҹиғҪд№ҹдёҚжҳҜеўһеҠ зү©иҙЁиҙўеҜҢ гҖӮ 既然дёҚйңҖиҰҒ科еӯҰзҡ„зЎ®е®һжҖ§ пјҢ еҸҲдёҚйңҖиҰҒ科еӯҰзҡ„еҠӣйҮҸ пјҢ 科еӯҰиҮӘ然д№ҹе°ұжІЎжңүд»»дҪ•з”ЁеӨ„дәҶ гҖӮ жІЎжңүз”ЁеӨ„ пјҢ еҸҲжҖҺд№ҲеҸҜиғҪеҸ‘еұ•иө·жқҘе‘ўпјҹеӣ жӯӨ пјҢ дёӯеӣҪжңӘдә§з”ҹ科еӯҰ пјҢ жҳҜеӣ дёә пјҢ еңЁдёӯеӣҪдәәзңӢжқҘ пјҢ 他们дёҚйңҖиҰҒ科еӯҰ гҖӮиҖҢиҘҝж–№еҲҷдёҚеҗҢ пјҢ 他们зҡ„е“ІеӯҰеұһдәҺвҖңдәәдёәвҖқи·Ҝзәҝ пјҢ е…¶зІҫзҘһжҳҜи®ӨиҜҶе’ҢиҜҒе®һеӨ–еңЁзҡ„дё–з•Ң пјҢ вҖң他们йҰ–е…ҲеҠӣжұӮи®ӨиҜҶе®ғ пјҢ еҜ№е®ғзҶҹжӮүдәҶд№ӢеҗҺе°ұеҠӣжұӮеҫҒжңҚе®ғ гҖӮ жүҖд»Ҙ他们注е®ҡдәҶиҰҒжңү科еӯҰ пјҢ ж—ўдёәдәҶзЎ®е®һжҖ§ пјҢ еҸҲдёәдәҶеҠӣйҮҸвҖқ гҖӮ еҸҜд»ҘжғіиұЎ пјҢ вҖңеҰӮжһңдёӯеӣҪдәәйҒөеҫӘеўЁеӯҗзҡ„е–„еҚіжңүз”Ёзҡ„жҖқжғі пјҢ жҲ–иҖ…йҒөеҫӘиҚҖеӯҗзҡ„еҲ¶еӨ©иҖҢдёҚйўӮеӨ©зҡ„жҖқжғі пјҢ йӮЈе°ұеҫҲеҸҜиғҪж—©е°ұдә§з”ҹдәҶ科еӯҰвҖқ гҖӮ иҝҷдёӘзҢңжөӢжҳҜжңүдәӢе®һж №жҚ®зҡ„ пјҢ еӣ дёәеңЁгҖҠеўЁеӯҗгҖӢгҖҒгҖҠиҚҖеӯҗгҖӢдёӯзҡ„зЎ®жңүи®ёеӨҡ科еӯҰзҡ„иҗҢиҠҪ гҖӮжҖ»д№Ӣ пјҢ еңЁгҖҠдёәгҖӢж–Үдёӯ пјҢ еҶҜеҸӢе…°жҳҜжҠҠвҖңжұӮз”ҹзҡ„ж„Ҹеҝ—е’ҢжұӮе№ёзҰҸзҡ„ж¬ІжңӣвҖқзӯүжҖқжғіеӣ зҙ зңӢжҲҗжҳҜеҺҶеҸІеҸ‘еұ•зҡ„еҺҹеӣ пјҢ и®ӨдёәдёӯеӣҪжңӘдә§з”ҹиҝ‘代科еӯҰзҡ„ж №жәҗ пјҢ еңЁдәҺдёӯеӣҪдёҚеҗҢдәҺиҘҝж–№зҡ„дәҺеҝғдёӯиҺ·еҫ—жңҖеӨ§е№ёзҰҸзҡ„е№ёзҰҸи§Ӯ гҖӮ иҝҷз§Қе№ёзҰҸи§ӮеҶіе®ҡзқҖ他们дёҚдјҡдә§з”ҹеҜ№з§‘еӯҰзҡ„йңҖжұӮ пјҢ еңЁиҝҷз§Қе№ёзҰҸи§Ӯзҡ„ж”Ҝй…ҚдёӢ пјҢ 科еӯҰжҳҜжіЁе®ҡдёҚеҸҜиғҪдә§з”ҹзҡ„ пјҢ еҚідҫҝжҳҜжңүдәҶ科еӯҰзҡ„иҗҢиҠҪ пјҢ д№ҹдјҡиў«и§ҶдҪңйӣ•иҷ«е°ҸжҠҖгҖҒз”ҡиҮіж—Ғй—Ёе·ҰйҒ“ пјҢ иҖҢж— жі•еҫ—еҲ°еҸ‘еұ• гҖӮеҶҜеҸӢе…°еңЁдёҠдёӘдё–зәӘ20е№ҙд»ЈжҸҗеҮәзҡ„иҝҷз§Қи§ӮзӮ№ пјҢ еҜ№дәҺеҗҺжқҘдәә们еҜ№жқҺзәҰз‘ҹйҡҫйўҳзҡ„з ҙи§Ј пјҢ жңүзқҖзӣёеҪ“йҮҚиҰҒзҡ„ж„Ҹд№ү пјҢ еңЁжҹҗз§Қж„Ҹд№үдёҠ пјҢ еҸҜд»ҘиҜҙжҳҜеҘ е®ҡдәҶдёҖдёӘеҹәзЎҖ гҖӮ еҲ°зӣ®еүҚдёәжӯў пјҢ еңЁдёәжқҺзәҰз‘ҹйҡҫйўҳжүҖжҸҗдҫӣзҡ„еҗ„з§Қи§Јзӯ”дёӯ пјҢ еҫҲеӨҡйғҪиғҪд»ҺеҶҜеҸӢе…°зҡ„иҝҷзҜҮж–Үз« дёӯжүҫеҲ°еҪұеӯҗ гҖӮ иҝҷдёҖж–№йқўеӣә然жҳҜеӣ дёәеҶҜеҸӢе…°жүҖжҸҗдҫӣзҡ„зӯ”жЎҲжҳҜе“ІеӯҰеұӮйқўзҡ„ пјҢ жҜ•з«ҹе“ІеӯҰжҳҜдёҖз§Қж–ҮеҢ–зҡ„ж ёеҝғе’ҢеҹәзЎҖпјӣеҸҰдёҖж–№йқў пјҢ д№ҹеҸҚжҳ дәҶеҶҜеҸӢе…°зҡ„и§Јзӯ”зҡ„еҗҲзҗҶжҖ§дёҺз”ҹе‘ҪеҠӣ гҖӮ 然иҖҢ пјҢ иҝҷз§Қи§Јзӯ”еңЁзҺ°еңЁзңӢжқҘеҸҲжҳҫеҫ—дёҚеӨҹе®Ңж•ҙ пјҢ еӣ дёәе®ғ并没жңүжҸӯзӨәдёӯеӣҪдј з»ҹзҡ„е№ёзҰҸи§ӮжүҖд»Ҙдә§з”ҹзҡ„зӨҫдјҡеҺҶеҸІжқЎд»¶ пјҢ д№ҹжІЎжңүиҜҙжҳҺеңЁе“ІеӯҰзҡ„вҖңиҮӘ然вҖқи·ҜзәҝдёҺвҖңдәәдёәвҖқи·Ҝзәҝзҡ„ж–—дәүдёӯ пјҢ вҖңиҮӘ然вҖқи·ҜзәҝеҸ–иғң并й•ҝжңҹж”Ҝй…ҚдёӯеӣҪдәәеҝғзҒөзҡ„еҺҶеҸІеҝ…然жҖ§ пјҢ иҖҢиҝҷе®һйҷ…дёҠжүҚжҳҜжӣҙдёәж №жң¬зҡ„еҺҹеӣ гҖӮ еҘҪеңЁеҶҜеҸӢе…°еңЁд»ҘеҗҺзҡ„е“ІеӯҰеҸІз ”究е’Ңж–°зҗҶеӯҰдҪ“зі»зҡ„е»әжһ„дёӯ пјҢ ејҘиЎҘдәҶиҝҷдёҖдёҚи¶і гҖӮ иҝҷдёҖзӮ№жҲ‘们е°ҶеңЁдёӢж–ҮиҜҰз»ҶжҺўи®Ё гҖӮйңҖиҰҒиҜҙжҳҺзҡ„жҳҜ пјҢ иҷҪ然е’Ңд»–еҗҺжқҘзҡ„е“ІеӯҰеҸІз ”究е’Ңж–°зҗҶеӯҰдҪ“зі»зҡ„е»әжһ„зӣёжҜ” пјҢ иҝҷзҜҮж–Үз« еҜ№дёӯеӣҪе“ІеӯҰзҡ„иҙЎзҢ®дјјд№ҺжҳҜеҫ®дёҚи¶ійҒ“зҡ„ пјҢ дҪҶжҳҜеҜ№дәҺеҶҜеҸӢе…°дёӘдәәжҖқжғізҡ„еҸ‘еұ•жқҘиҜҙ пјҢ е®ғеҚҙжҳҜзӣёеҪ“йҮҚиҰҒзҡ„ пјҢ еҸҜд»ҘиҜҙ пјҢ е®ғжҳҜеҶҜеҸӢе…°зңҹжӯЈе“ІеӯҰжҙ»еҠЁзҡ„иө·зӮ№ пјҢ е®ғеҹәжң¬дёҠзЎ®е®ҡдәҶеҶҜеҸӢе…°д»ҘеҗҺе“ІеӯҰз ”з©¶зҡ„ж–№еҗ‘ гҖӮ еҰӮжһңиҜҙеңЁиҝҷд№ӢеүҚ пјҢ еҶҜеҸӢе…°дё»иҰҒжҳҜеңЁеӯҰд№ е“ІеӯҰзҡ„иҜқ пјҢ йӮЈд№Ҳ пјҢ д»ҘиҝҷзҜҮж–Үз« дёәж Үеҝ— пјҢ еҶҜеҸӢе…°ејҖе§ӢдәҶзңҹжӯЈзҡ„е“ІеӯҰеҲӣйҖ гҖӮ еңЁиҝҷзҜҮж–Үз« дёӯ пјҢ еҶҜеҸӢе…°дёәдәҶи§ЈйҮҠдёӯеӣҪдёәд»Җд№ҲжІЎжңүдә§з”ҹиҝ‘д»ЈиҮӘ然科еӯҰзҡ„й—®йўҳ пјҢ д»Ҙд»–ж·ұеҺҡзҡ„дёӯеӣҪе“ІеӯҰеҠҹеә•е’ҢиүҜеҘҪзҡ„иҘҝж–№е“ІеӯҰзҙ е…» пјҢ жҜ”иҫғдәҶдёӯиҘҝе“ІеӯҰдј з»ҹеңЁе№ёзҰҸи§ӮгҖҒд»·еҖјж ҮеҮҶзӯүж–№йқўзҡ„е·®ејӮ пјҢ жҸҗеҮәдәҶвҖңиҮӘ然вҖқеһӢе“ІеӯҰдёҺвҖңдәәдёәвҖқеһӢе“ІеӯҰзҡ„еҢәеҲҶ пјҢ жұӮе№ёзҰҸдәҺеҶ…дёҺжұӮе№ёзҰҸдәҺеӨ–зҡ„е“ІеӯҰзҡ„дёҚеҗҢ гҖӮ иҝҷдәӣйғҪдёәд»–еҗҺжқҘзҡ„еҚҡеЈ«и®әж–ҮвҖ”вҖ”гҖҠеӨ©дәәжҚҹзӣҠи®әгҖӢзҡ„еҶҷдҪңеҘ е®ҡдәҶеҫҲеҘҪзҡ„еҹәзЎҖ пјҢ е®һйҷ…дёҠиҝҷдәӣд№ҹйғҪжҳҜгҖҠеӨ©дәәжҚҹзӣҠи®әгҖӢзҡ„еҹәжң¬и§ӮзӮ№ гҖӮ иҖҢгҖҠеӨ©дәәжҚҹзӣҠи®әгҖӢеҸҲжһ„жҲҗдәҶд»–зҡ„гҖҠдёӯеӣҪе“ІеӯҰеҸІгҖӢзҡ„еҹәзЎҖ пјҢ д»–зҡ„дёӨеҚ·жң¬гҖҠдёӯеӣҪе“ІеӯҰеҸІгҖӢжӯЈжҳҜгҖҠеӨ©дәәжҚҹзӣҠи®әгҖӢзҡ„еҗҲд№ҺйҖ»иҫ‘зҡ„еҸ‘еұ• гҖӮ 30е№ҙд»Ј пјҢ еҪ“д»–и®Іе®ҢдәҶе®ӢжҳҺзҡ„新儒家д№ӢеҗҺ пјҢ е°ұжҺҘзқҖжңұеӯҗи®Іиө·дәҶж–°зҗҶеӯҰ пјҢ еҶҷеҮәйҮҢзЁӢзў‘ејҸзҡ„вҖңиҙһе…ғе…ӯд№ҰвҖқ пјҢ е»әжҲҗдёӯеӣҪзҺ°д»ЈжңҖе®Ңж•ҙзҡ„е“ІеӯҰдҪ“зі» пјҢ д»ҺиҖҢ继жүҝдәҶдёӯеӣҪе“ІеӯҰзҡ„вҖңиҮӘ然вҖқеһӢдј з»ҹ пјҢ 继з»ӯеңЁеҶ…еҝғеҜ»жұӮзқҖе№ёзҰҸ гҖӮ еӣ жӯӨ пјҢ еҸҜд»ҘиҜҙ пјҢ еҶҜеҸӢе…°еҜ№дёӯеӣҪе“ІеӯҰзҡ„дёҖеҲҮиҙЎзҢ® пјҢ йғҪеҸ‘з«ҜдәҺгҖҠдёәд»Җд№ҲдёӯеӣҪжІЎжңү科еӯҰгҖӢиҝҷзҜҮж–Үз« пјҢ иҝҷзҜҮж–Үз« жҳҜе…¶е…ЁйғЁе“ІеӯҰеҲӣйҖ жҙ»еҠЁзҡ„иө·зӮ№ гҖӮ еҸҚиҝҮжқҘзңӢ пјҢ жҲ‘们д№ҹеҸҜд»ҘиҜҙ пјҢ е®һйҷ…дёҠеҶҜеҸӢе…°дёҖз”ҹд№ҹйғҪжҳҜеңЁеӣһзӯ”иҝҷдёӘй—®йўҳ пјҢ д»–е’ҢжқҺзәҰз‘ҹдёҖж · пјҢ жҳҜдёӘжҜ•з”ҹиҮҙеҠӣдәҺи§ЈйҮҠдёӯеӣҪдёәд»Җд№ҲжІЎжңүдә§з”ҹиҝ‘д»ЈиҮӘ然科еӯҰзҡ„еӯҰиҖ… гҖ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