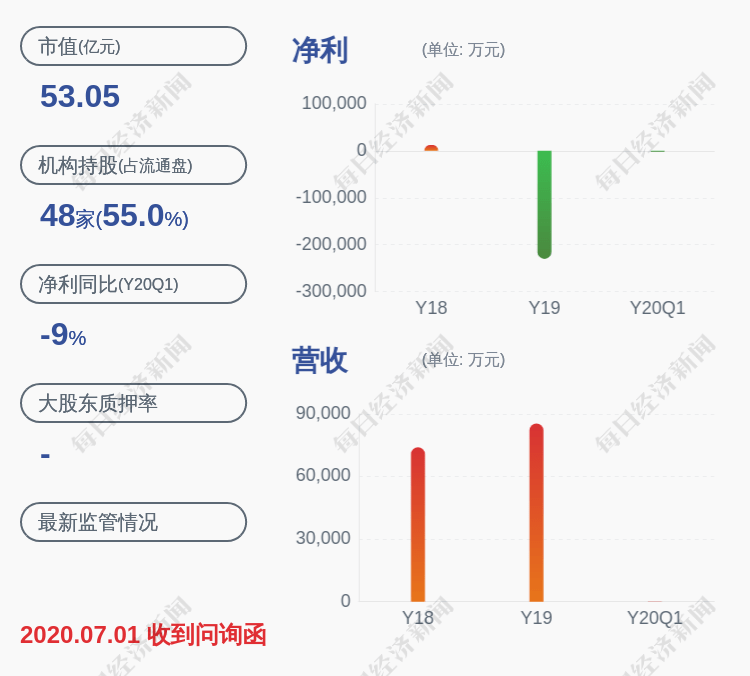静安史观未立而身先死,何其悲也!寅恪继之,以碑铭之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静安为新史观之士范,从此休止了纷纭众说。静安先生痛心二次易代,便“义无再辱”,而寅恪一生,又逢国共易代,间以抗日战争,其祖、父辈皆为抗战而死,其本人亦在抗战中九死一生,经此累累世变,竟得以新生,大概凡此总总,才是他能于新史观上更进一层的财富,才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仅在为静安立碑中作为士范得以确立,而且在《论》和《柳如是别传》中作为我民族之女范而遗传,这是寅恪先生以永恒之女性引导我民族上升的新格调。
至此,寅恪先生以“独立之精神”开始了他“一个人的文艺复兴”,确立了诗化史学的范式,以“自由之思想”完成了他的“史学革命”,实现了从王朝史观向文化个体史观的转型。
中国传统史观,最具代表性者为“二司马”,一是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另一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前者是贯通天人古今而成一家之言的通史,后者则是将一代代王朝排列起来,当作历史的一面面镜子,起到“资治”作用,发挥“通鉴”功能,为本朝立言。
此二者,一为通史,一为通鉴,寅恪祖训“不问政”,故其治史,不为通鉴取向,而取通史路线,若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新史观,著一“吾心”之通史,则可谓举世期待,惜其未能成就,所著《论》和《柳如是别传》,乃新史观之“小试”,新范式之“红妆”,寅恪先生所留遗憾,吾辈当继而竟之。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前五卷,中信出版社)
---
推荐阅读
- 中国古代史上价值连城的5件国宝,若有幸得到一件,便可富甲天下
- 陈省身的数学人生开创几何新纪元,为中国数学教育打下坚实基础
- 美国历史教材上仅有的六位中国人,你可知道他们都是哪些人
- 玩石头就要做赏石文化的传播者,可一些人却成了奇石的封存者
- 中国网络文学能否撕掉“二等文学”标签?
- 中国武术由来已久,“武学盛世”和“武学末世”分别是什么时候?
- 中国嘉德专家老师评鉴清雍正斗彩瓷器及市场价值
- 「张忆滨」|丹青追梦 水墨本色-中国当代书画名家个人云展览
- 中国画中的理想男人
- 安徽萧县: 为青少年成长搭建文化教育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