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6日,网络上风传一篇文章《他竟然也在<文史哲>发过文章?》,该文出自《文史哲》微信公众号,作者为徐庆全先生。
出于职业习惯,我细读了该文,了解了作者依据材料做出的基本判断,要点大致如下:
1、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山东省发现一部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后,将其报送中华书局;因六十年代康生的特殊地位,中华书局又通过出版局、文化部将此事上报给康生。康生就此事与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金灿然和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有过二封书信;
2、据冯其庸先生回忆,六十年代康生曾计划与冯其庸先生合作搞一本《聊斋志异选》;
3、据钱伯城先生回忆,康生对《聊斋志异》版本有过专门研究,在《文学遗产》增刊发过文章;
4、《文史哲》1963年第四期发表署名“杜荇”的文章《新发现的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初校后记》。
【 文史哲|宁稼雨:“杜荇”:你是康生,还是任笃行?——与徐庆全先生商榷】综合以上信息,徐庆全先生得出大胆推测——《文史哲》发表学术论文的“杜荇”,或即大名鼎鼎的康生。
看过徐先生的文章,尤其是看过“杜荇”在《文史哲》发表的论文之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位“杜荇”应该不是康生,而是对《聊斋志异》版本下过几十年功夫的学术前辈任笃行先生。
我把这个初步看法在微信朋友圈发表,并向《文史哲》编辑部提供我的意见后,得到很多朋友的赞同和支持,还有些前辈和朋友主动向我提供相关信息。
我本人也通过各种途径联系和咨询了与任笃行先生有过交往合作的几位当事人,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古代小说版本研究专家刘世德先生,山东大学著名教授袁世硕先生和王平教授,齐鲁书社前社长、总编宫晓卫先生,齐鲁书社前副总编周晶先生。
在综合我本人对任笃行先生及其学术成就,以及相关信息材料之后,我大致把这个问题梳理了一下,在微信朋友圈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阐述对此事的认知和判断。
首先,能够证明“杜荇”真实身份的原始材料已经不存,无法找到作为铁证的原始根据。这些原始根据应该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当事人,二是《文史哲》刊物的原始档案文献。
但是,无论是徐庆全先生推测的康生,还是我认为的任笃行,都已经作古,无法从当事人角度得到确认;事情发生后,我联系了《文史哲》主编王学典先生,向他咨询《文史哲》编辑部历史档案情况。得到的答复是,文化革命前《文史哲》刊物的全部档案,已经于文革中全部销毁。所以只能另辟蹊径,从其他线索来追寻“杜荇”的真实身份。
其次,据徐庆全先生文和宫晓卫先生提供信息,康生和任笃行都接触过“杜荇”文章所涉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其时间先后顺序应该是,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发现之后,山东省出版总社始终为该版本所有者,其间由山东省出版局报送给中华书局,经中华书局报送文化部,报送到康生手里,康生阅完之后产生了徐文提到的两封信。嗣后康生将该书归还给山东省出版总社。
这个顺序说明,作为当时山东省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任笃行在二十卷抄本发现之后的第一时间就接触了这个版本,时间上比康生更早,因而也就比康生有更充裕的时间来从事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的版本校勘工作。
据宫晓卫先生提供信息,九十年代齐鲁书社社庆活动,打算重印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时,他专门从山东省出版总社资料室调阅了该版本原件,里面夹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康生于某年某月某日还”,书中还有部分康生批阅的文字。
宫晓卫先生给我的原话是说:“兄的猜测应是对的,杜荇肯定不是康生。我记得很清楚康生在原版本里所记文字仅数条,都极简,有二、三十字的仅两条,和杜荇的文章完全不类。”
就目前我了解掌握的信息材料,我认为任笃行为“杜荇”的可能性和可信性要更大一些。主要理由和根据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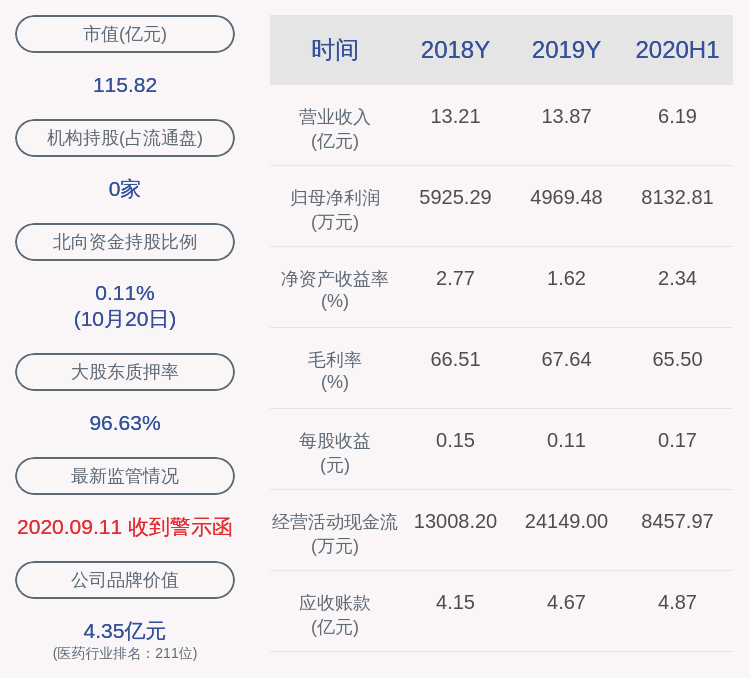







![[颜素护肤]鞠婧祎的下睫毛:明星们堪比整容的化妆技巧教程,汤唯的下颌线](https://imgcdn.toutiaoyule.com/20200421/20200421224227548211a_t.jp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