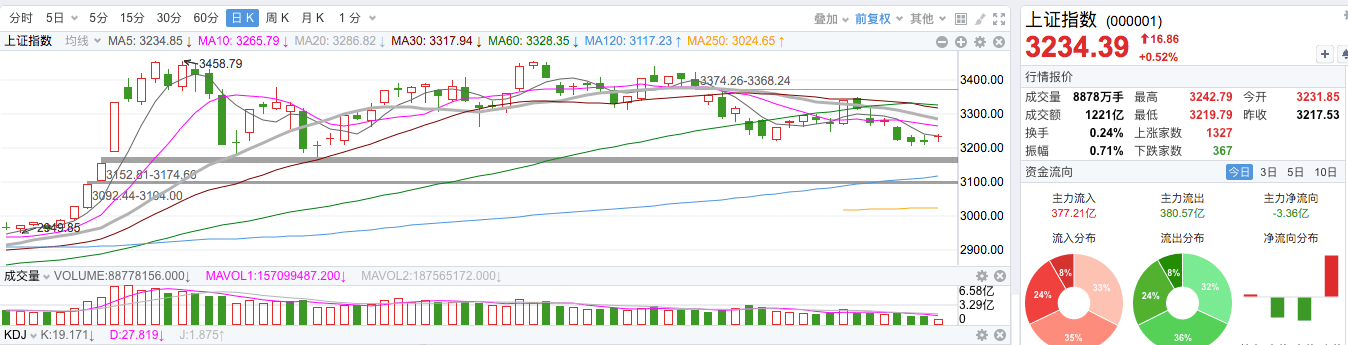相比之下,康生在文史研究方面的确有很深的功力,但他的涉猎面很广,从文史研究到文物考古,皆有染指。他也的确写过《聊斋志异》的版本文章。《文史哲》微信公众号徐庆全先生文章下面读者留言援引著名古代小说版本研究专家刘世德先生介绍:
关于康生在《文学遗产》上发表有关《聊斋志异》的文章,钱伯城先生所言不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刘世德先生曾有文字提及。康生笔名叶余,发表过两次。前一次发表的是《关于〈聊斋志异〉的第一次刻本》(第169期),后一次是《关于〈聊斋志异〉的几种本子》(第204期)。敬以奉闻!
康生这两篇发表于《文学遗产》增刊的文章,虽然现在难以找到,但从文章题目来看,这是两篇关于《聊斋志异》版本的科普性质的文章。
第一篇应该是介绍《聊斋志异》第一次刻本(青柯亭本)情况的内容,第二篇应该是介绍几种《聊斋志异》重要版本的内容。这两篇文章虽然与“杜荇”的文章也有一定的逻辑关联,但从与“杜荇”文章的学术深度差异和逻辑关联的紧密度上来看,完全无法与任笃行的三篇文章和《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这样的皇皇巨著相提并论。
徐庆全先生文章中提到康生曾约请冯其庸先生合作完成《聊斋志异选》一事,将其作为推测康生为“杜荇”的理由根据之一。我倒是觉得,如果没有任笃行在《聊斋志异》版本研究方面的深厚功力和卓越成果,这个说法也许有些道理。
但是看了任笃行的成果,业内人士很容易判断区分出二者的学术价值高下。
首先,作品选一类文学选本固然也有学术价值,但其主要功能作用是向社会大众做普及宣传,是一种科普工作。
相比之下,古籍版本校勘才是更加具有专业性、学术性和学术深度的硬邦邦的学术研究工作。从这个工作性质上看,任笃行先生的三篇文章和《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与署名“杜荇”的文章在文章专业性质属性上更加吻合一致。
其次,从徐文中可以看到,康生找冯其庸先生“合作”,说白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合作,而是找一位打工的合作者,即由冯其庸出力,康生坐享其成来一起署名。实际工作不是康生本人来做的。
如果康生是“杜荇”本人,说明他已经在《聊斋志异》版本方面下过多年深入功夫,烂熟于心,完成一本《聊斋志异选》简直就是顺手牵羊的举手之劳,完全用不着另外找一位专家来捉刀代笔。所以,这个材料实际上应该是康生并非“杜荇”本人的证据。两相比较,更有理由相信,任笃行才是“杜荇”笔名的使用者。
第五,“杜荇”文章与康生信件在时间问题上有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困难。
“杜荇”文章发表于《文史哲》1963年第四期,按双月刊计算,时间应该在1963年七月八月间;从徐庆全先生文章中提到的康生两封信的落款时间看,第一封的落款时间是6月14日,没有具体年份,第二封信落实时间为1963年9月24日。
如果理解没有错误,第一封信的年份也应该在1963年。是康生收到该版本后三个月之内的两次信件。如果这个理解能够成立,那么客观上就形成这样的时间对比:《文史哲》上面的“杜荇”文章,刚好发表在康生这两次信件的时间当中。
也就是说,如果康生就是“杜荇”,那么他在收到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之后,需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写好这篇翔实的长篇考据文章,而且还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让《文史哲》发表。
按通常的刊物审稿发表时间,七月八月出版的刊物,最晚在四五月间就已经完成审稿、校对和排版工作。当时还没有现在的计算机排版,还是人工铅字排版,时间上应该更早一些。也就是说,当康生拿到这部二十四卷抄本的时候,《文史哲》那篇署名“杜荇”的文章已经审读校对发排,马上进入印刷程序了。
从这个时间顺序上看,康生完全没有足够的时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成这篇版本考据大作,因而基本上可以排除康生为“杜荇”文章作者的可能性。可以作为此说佐证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世德先生给我的微信回复中,特别强调了一句:“康生的笔名是’叶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