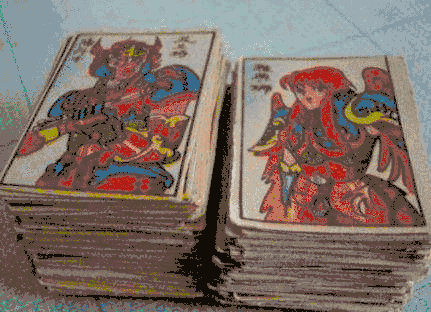вҖңдә”еӣӣвҖқзІҫзҘһдј жүҝдёӯзҡ„еӣһжәҜдёҺејҳжү¬( е…« )
дҪҷиӢұж—¶е…Ҳз”ҹеңЁеӣһеҝҶж–Үз« гҖҠжҲ‘иө°иҝҮзҡ„и·ҜгҖӢдёӯи®Іиҝ°е°‘е№ҙж—¶еӣ дёәжҠ—ж—ҘжҲҳдәүиў«йҖҒеҲ°е®үеҫҪзҡ„жҪңеұұд№ЎдёӢз”ҹжҙ»дәҶдёғе…«е№ҙе·ҰеҸі гҖӮ дҪҷе…Ҳз”ҹжҸҗеҲ° пјҢ еңЁд№Ўжқ‘зҡ„з”ҹжҙ»дёӯеҫҲе°‘жңүдәәеҺ»жү“е®ҳеҸё пјҢ 并дёҚжҳҜеҫҲйңҖиҰҒжі•еҫӢ пјҢ д»Қ然жҳҜз”Ёйқһеёёдј з»ҹзҡ„ж–№ејҸжқҘеӨ„зҗҶеҲҶжӯ§е’Ңдәүи®® пјҢ еҢ…жӢ¬е…¬е…ұзҘ е ӮгҖҒд№Ўжқ‘зҡ„е…¬е…ұз”ҹжҙ»гҖҒд»·еҖји§ӮеҝөзӯүйғҪејҘжј«зқҖдёҖз§ҚйҮҚеӨ©зҗҶдәәжғ…иғңиҝҮжі•еҫӢеҲ¶еәҰзҡ„зү№иҙЁ гҖӮ еҰӮжһңдёҖдёӘе№ҙиҪ»дәәзҠҜдәҶй”ҷиҜҜ пјҢ жҳҜзҘ е Ӯзҡ„еҮ дёӘй•ҝиҖҒжқҘи®Ёи®ә пјҢ дёҚйңҖиҰҒиҜүиҜёжі•еҫӢжҲ–иҖ…жҡҙеҠӣ гҖӮ иҝҷдәӣз»ҸеҺҶи®©д»–еңЁйҳ…иҜ»жңүе…ідј з»ҹдёӯеӣҪзҡ„еҗ„з§Қж–Үжң¬ж—¶йғҪз»ҷдәҲд»–зңҹеҲҮзҡ„ж„ҹеҸ— гҖӮ
еҜ№дәҺдёӯеӣҪдј з»ҹзҡ„жү№иҜ„ пјҢ жҲ‘们иҜҘеҰӮдҪ•зңӢеҫ…пјҹжҲ‘жӣҫеҶҷиҝҮдёҖзҜҮжҠҘзәёж–Үз« еҖҹз”ЁиғЎйҖӮзҡ„жҖқжғіиө„жәҗи®Ёи®әж°‘ж—Ҹзҡ„иҮӘдҝЎеҝғд»Һе“ӘйҮҢжқҘ гҖӮ жҲ‘们д№ӢеүҚжңүдёҖз§Қи§ӮеҝөвҖ”вҖ”дёҖдёӘдәәеҰӮжһңзҲұеӣҪ пјҢ е°ұеә”иҜҘжӣҙеӨҡең°е‘је”ӨгҖҒеҸ‘жү¬гҖҒйҳҗйҮҠдј з»ҹдёӯзҫҺеҘҪзҡ„гҖҒдјҳиүҜзҡ„йқўзӣё пјҢ иҖҢдёҚиғҪжҖ»жҳҜиӢӣиҙЈдј з»ҹе’Ңжү№иҜ„дёӯеӣҪ гҖӮ
д№қдёҖе…«дәӢеҸҳд»ҘеҗҺ пјҢ иғЎйҖӮеҪ“ж—¶е’ҢдёҖдёӘеҢ—дә¬еӨ§еӯҰзҡ„ж—Ғеҗ¬з”ҹеҜҝз”ҹпјҲжқҘиҮӘиҙөе·һпјүеҸҚеӨҚйҖҡдҝЎгҖҒеҜ№иҜқ пјҢ еҜҝз”ҹеңЁд№ҰдҝЎйҮҢеҜ№иғЎйҖӮиҜҙпјҡвҖңжҲ‘们д»Ҡж—Ҙд№Ӣж”№иҝӣдёҚеҰӮж—Ҙжң¬д№ӢйҖҹиҖ… пјҢ е°ұжҳҜеӣ дёәжҲ‘们зҡ„еӣәжңүж–ҮеҢ–еӨӘдё°еҜҢдәҶ гҖӮ еҜҢдәҺеҲӣйҖ жҖ§зҡ„дәә пјҢ дёӘжҖ§еҝ…ејә пјҢ жҺҘеҸ—жҖ§е°ұиҫғзј“ гҖӮ еҜҢдәҺжЁЎд»ҝжҖ§зҡ„ пјҢ жҺҘеҸ—жҖ§иҷҪејә пјҢ дҪҶеҲӣйҖ еҠӣе°ұжңүйҷҗдәҶ гҖӮ ж—Ҙдәәд»Ҡж—Ҙд№ӢдјҳдәҺжҲ‘иҖ… пјҢ е°ұеӣ е…¶жң¬жқҘзҡ„ж–ҮеҢ–ж №еҹәжһҒжө… пјҢ жЁЎд»ҝжҖ§ејә пјҢ иғҪд»Ҙе…ЁеҠӣжҺҘеҸ—еӨ–жқҘж–ҮеҢ– пјҢ жҲ‘们иҝҳеңЁеҫҳеҫҠгҖҒжҜ”иҫғгҖҒдәүи®әд№Ӣйҷ… пјҢ еҘ№е·Іе°ҪйҮҸеҗёеҸ–дәҶ гҖӮ вҖқиғЎйҖӮй’ҲеҜ№иҝҷдёӘй—®йўҳеңЁгҖҠзӢ¬з«ӢиҜ„и®әгҖӢдёҠиҝһз»ӯеҸ‘иЎЁдәҶгҖҠдҝЎеҝғдёҺеҸҚзңҒгҖӢгҖҒгҖҠеҶҚи®әдҝЎеҝғдёҺеҸҚзңҒгҖӢгҖҒгҖҠдёүи®әдҝЎеҝғдёҺеҸҚзңҒгҖӢ пјҢ д»–жҢҮеҮәдёҖдёӘж°‘ж—ҸзңҹжӯЈиҮӘжҲ‘зҡ„зЎ®иҜҒ пјҢ еҰӮжһңдёҚиғҪе®№еҝҚеҜ№иҮӘжҲ‘зҡ„жү№иҜ„е’ҢеҸҚзңҒзҡ„иҜқ пјҢ йӮЈиҝҷз§ҚжүҖи°“зҡ„ж°‘ж—ҸиҮӘдҝЎе…¶е®һжҳҜеҫҲи„Ҷејұзҡ„ гҖӮ еҸҰеӨ–дёҖж–№йқў пјҢ еҪ“дёҖдёӘж–ҮеҢ–дј з»ҹйҮҢзҡ„зҹҘиҜҶеҲҶеӯҗеҜ№иҝҮеҺ»жңүдёҖз§ҚеҸҚжҖқдёҺжү№иҜ„ пјҢ 并且иЁҖд№ӢжңүзҗҶгҖҒиЁҖд№ӢжңүжҚ® пјҢ е…¶е®һ并дёҚж„Ҹе‘ізқҖд»–еҜ№иҝҷдёӘж°‘ж—Ҹе’ҢеӣҪ家зҡ„ж–ҮеҢ–жІЎжңүжғ…ж„ҹгҖҒжІЎжңүзҗҶи§ЈгҖҒжІЎжңүи®ӨеҗҢ гҖӮ зӣёеҸҚ пјҢ иҝҷеҸҜиғҪжҳҜдёҖз§Қжӣҙй«ҳж„Ҹд№үдёҠзҡ„еҜ№дәҺеӣҪ家е’Ңж°‘ж—Ҹзҡ„и®ӨеҗҢе’Ңжғ…ж„ҹ пјҢ еӣ дёәе®ғжӣҙеӨҡжҳҜе»әз«ӢеңЁдёҖз§ҚзҗҶжҖ§зҡ„еҹәзЎҖдёҠ пјҢ иҖҢдёҚжҳҜеҚ•зәҜжғ…ж„ҹзҡ„гҖҒзӣІзӣ®зҡ„зғӯжғ… гҖӮ
жҜ”еҰӮжҲ‘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ж№–еҚ—дәә пјҢ еҜ№дәҺж№–еҚ—ж–ҮеҢ–йҮҢе®№жҳ“з”ҹй•ҝеҮәжқҘзҡ„жһҒз«Ҝдё»д№үжҖ§ж је’Ңе°Ғй—ӯзӢӯйҡҳзҡ„иҮӘжҒӢж–ҮеҢ–з»ҸеёёжңүжүҖжү№иҜ„ пјҢ дҪҶиҝҷ并дёҚд»ЈиЎЁжҲ‘еҜ№ж№–еҚ—жІЎжңүжғ…ж„ҹе’Ңи®ӨеҗҢ пјҢ жү№иҜ„зӣёеҸҚжӣҙиғҪеҜ№дәҺж –иә«зҡ„е…ұеҗҢдҪ“жһ„жҲҗеҶ…еңЁзҡ„иҝһеёҰж„ҹе’Ңжӣҙж·ұеұӮж¬Ўзҡ„з»“еҗҲ пјҢ иҖҢдёҚжҳҜз®ҖеҚ•зҡ„еҹәдәҺзӣІзӣ®жғ…ж„ҹзҡ„зј з»•е’ҢжҠ•е°„ гҖӮ иҝҷз§Қзј з»•еҸҜиғҪжҳҜжІЎжңүеҠһжі•з»Ҹеҫ—иө·зҗҶжҖ§е°әеәҰзҡ„жЈҖйӘҢзҡ„ пјҢ з”ҡиҮід№ҹжІЎжңүеҠһжі•з»Ҹеҫ—иө·жҹҗдәӣеҚұжңәж—¶еҲ»зҡ„иҖғйӘҢ 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иҙҫж–ҜжұҖВ·жҜ”дјҜ|27еІҒиҙҫж–ҜжұҖжҜ”дјҜеүғе…үеӨҙпјҢдёҖж”№йӮӢйҒўеӨ§еҸ”еҪўиұЎпјҢзҪ‘еҸӢиөһд»–жҳҜзІҫзҘһе°ҸдјҷпјҒ
- з©ҝиЎЈжҗӯй…Қ|жқҺеҳүж¬Јз—…ж„ҲеҗҺзҺ°иә«йҳ”еӨӘиҒҡдјҡпјҢзү№ең°жҹ“еҸ‘жҸҗзІҫзҘһпјҢе…ЁеүҜжӯҰиЈ…з©ҝиЎЈжңҖдҝқе®Ҳ
- зҺӢеҠӣе®Ҹ|зҺӢеҠӣе®ҸдәӢ件еҗҺз»ӯпјҒд»ҺзІҫзҘһиҷҗеҫ…еҲ°вҖңжӯ»дәЎеЁҒиғҒвҖқпјҢ他们дҝ©зҺ°еңЁжҖҺж ·дәҶпјҹ
- йғӯеҫ·зәІ|ж”№еҸҳйғӯеҫ·зәІе‘Ҫиҝҗзҡ„дёӨдёӘдәәпјҡзІҫзҘһдёҠжҳҜиөөжң¬еұұпјҢдё“дёҡдёҠжҳҜжқҺз«ӢзҫӨпјҒ
- йЎҫй•ҝеҚ«|и’ӢйӣҜдёҪ64еІҒиҖҒе…¬иҝ‘з…§жӣқе…үпјҢдёҺеӨҡдҪҚжҲҸйӘЁеҗҢжЎҶпјҢжҲҙеёҪеӯҗзІҫзҘһеҘҪ
- йӮ“дјҰ|40еІҒжӯҢжүӢжј”е”ұдјҡдёҠзӘҒжӣқзҰ»е©ҡпјҒеӨ§иөһз”·ж–№жҳҜеҘҪз”·дәәпјҢиҮӘе·ұе°ҶеҺ»зңӢзІҫзҘһ科
- иғЎжһ«|иғЎжһ«90еӨ§еҜҝдҪҺи°ғеәҶзҘқпјҢзІҫзҘһеҘ•еҘ•зҠ¶жҖҒеҘҪпјҢжІЎжғіиҝҮйҖҖдј‘дёҚд»Ӣж„ҸзҶ¬еӨңжӢҚжҲҸ
- жқҺеҳүж¬Ј|жқҺеҳүж¬ЈжӮЈйҮҚз—…еҗҺйңІйқўпјҢж¶ҲзҳҰдёҚе°‘дҪҶзІҫзҘһеҘ•еҘ•пјҢз”ҹе‘ҪеҠӣйЎҪејәд»ӨеҘҪеҸӢжғҠеҸ№
- жһ—дҝҠжқ°|еҘізҪ‘еҸӢеҶҚж¬Ўе–ҠиҜқжһ—дҝҠжқ°пјҢжҷ’еҮәеӨҡеј иҒҠеӨ©и®°еҪ•пјҢзҪ‘еҸӢе»әи®®е…¶дёҠзІҫзҘһз—…еҢ»йҷў
- еҫҗжҖҖй’°|10дҪҚиҝҮж°”д№җеқӣжӯҢеҗҺзҺ°зҠ¶пјҡжңүдәәзқЎеӨ§иЎ—пјҢжңүдәәи·‘е°Ҹе•Ҷжј”пјҢжңүдәәзІҫзҘһеӨұеё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