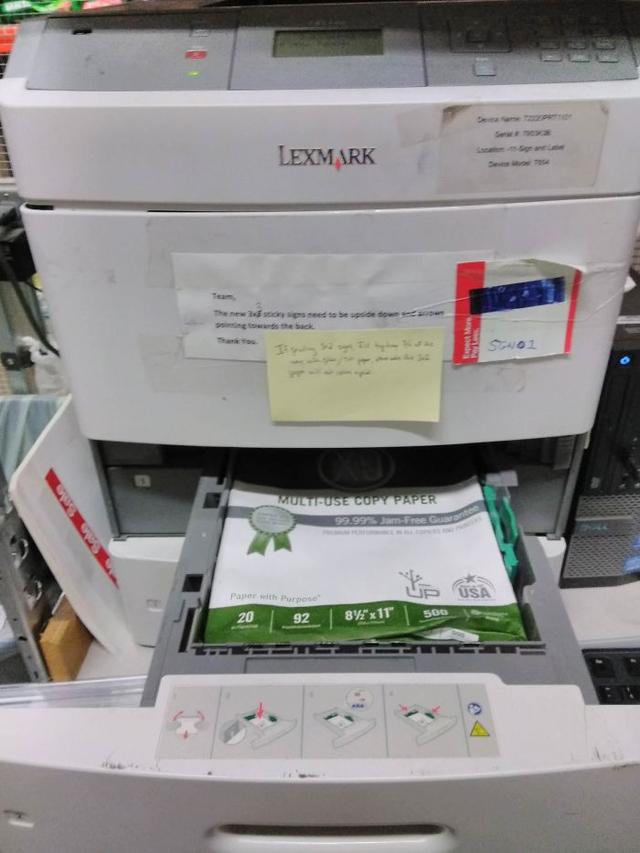жңұиҖҒеёҲ|гҖҠ收иҺ·гҖӢејҖж”ҫд№Ұжһ¶ | йҪҗйӮҰеӘӣпјҡжңұе…үжҪңе…Ҳз”ҹзҡ„иӢұиҜ—иҜҫ( дёү )
иҝҷд№ҲдёҖдҪҚеӨ§еӯҰиҖ…жҖҺдјҡеҸ¬и§ҒжҲ‘иҝҷдёӘдёҖе№ҙзә§еӯҰз”ҹе‘ўпјҹиҜҙзңҹзҡ„ пјҢ жҲ‘жҳҜжғҠйӘҮеӨҡдәҺиҚЈе№ёең°иө°иҝӣд»–йӮЈеңЁж–ҮеәҷжӯЈж®ҝвҖ”вҖ”еӨ§жҲҗж®ҝвҖ”вҖ”森然ж·ұй•ҝзҡ„еҠһе…¬е®Ө гҖӮ иҖҢйӮЈдҪҚеқҗеңЁе·ЁеӨ§жңЁжӨ…йҮҢ并дёҚеЈ®зЎ•зҡ„з©ҝзҒ°й•ҝиўҚзҡ„вҖңиҖҒеӨҙвҖқпјҲйӮЈдёҖе№ҙжңұиҖҒеёҲеӣӣеҚҒдёғеІҒ пјҢ еңЁжҲ‘йӮЈдёӘе№ҙйҫ„дәәзҡ„зңјдёӯ пјҢ жүҖжңүи¶…иҝҮеӣӣеҚҒеІҒзҡ„дәәйғҪжҳҜвҖңиҖҒдәәвҖқпјүд№ҹжІЎжңүд»Җд№Ҳж…ҲзҘҘзҡ„笑容 гҖӮ
д»–зңӢдәҶжҲ‘ пјҢ иҜҙпјҡвҖңдҪ иҒ”иҖғеҲҶеҸ‘еҲ°е“ІеӯҰзі» пјҢ дҪҶжҳҜдҪ иӢұж–ҮеҫҲеҘҪ пјҢ иҖғе…Ёж Ўз¬¬дёҖеҗҚ пјҢ дҪ дёәд»Җд№ҲдёҚиҪ¬еӨ–ж–Үзі»е‘ўпјҹвҖқ
жҲ‘иҜҙжҲ‘зҡ„第дёҖеҝ—ж„ҝжҳҜе“ІеӯҰзі» пјҢ жІЎжңүеЎ«жң¬ж Ўзҡ„еӨ–ж–Үзі» пјҢ дёҚжҳҜжІЎжңүиҖғдёҠ гҖӮ й«ҳдёӯжҜ•дёҡзҡ„ж—¶еҖҷ пјҢ зҲ¶дәІе’ҢеӯҹиҖҒеёҲйғҪеёҢжңӣжҲ‘дёҠдёӯж–Үзі» гҖӮ
д»–еҸҲй—®дәҶжҲ‘дёәд»Җд№ҲиҰҒвҖңиҜ»вҖқе“ІеӯҰзі» пјҢ е·Із»ҸеҝөдәҶдәӣд»Җд№Ҳе“ІеӯҰзҡ„д№ҰпјҹжҲ‘зҡ„еӣһзӯ”еңЁд»–еҗ¬жқҘеӨ§зәҰзӣёеҪ“вҖңе№јзЁҡж— зҹҘвҖқпјҲжҲ‘зҲ¶дәІе·Іе§”е©үең°еҜ№жҲ‘иҜҙиҝҮпјү пјҢ д»–жғідәҶдёҖдёӢиҜҙпјҡвҖңзҺ°еңЁжӯҰеӨ§жҗ¬иҝҒеҲ°иҝҷд№Ҳеғ»иҝңзҡ„ең°ж–№ пјҢ иҖҒеёҲеҫҲйҡҫиҜ·жқҘ пјҢ е“ІеӯҰзі»жңүдёҖдәӣиҜҫйғҪејҖдёҚеҮәжқҘ гҖӮ жҲ‘е·Із”ұеӣҪж–ҮиҖҒеёҲеӨ„зңӢеҲ°дҪ зҡ„дҪңж–Ү пјҢ дҪ еӨӘеӨҡж„Ғе–„ж„ҹ пјҢ дјјд№ҺжІЎжңүй’»з ”е“ІеӯҰзҡ„ж…§ж № гҖӮ дёӯж–Үзі»зҡ„иҜҫдҪ еҸҜд»Ҙж—Ғеҗ¬ пјҢ д№ҹеҸҜд»ҘдёҖз”ҹиҮӘдҝ® гҖӮ дҪҶжҳҜеӨ–ж–Үзі»зҡ„иҜҫзЁӢеҝ…йЎ»жңүиҖҒеёҲеёҰйўҶ пјҢ еҠ дёҠеҘҪзҡ„иӢұж–ҮеҹәзЎҖжүҚеҸҜд»Ҙи®Өи·Ҝе…Ҙй—Ё гҖӮ жҡ‘еҒҮеӣһеҺ»дҪ еҸҜд»ҘеӨҡжғіжғіеҶҚеҶіе®ҡ пјҢ дҪ еҰӮжһңиҪ¬е…ҘеӨ–ж–Үзі» пјҢ жҲ‘еҸҜд»ҘеҒҡдҪ зҡ„еҜјеёҲ пјҢ жңүй—®йўҳеҸҜд»ҘйҡҸж—¶й—®жҲ‘ гҖӮ вҖқ
иҝҷжңҖеҗҺдёҖеҸҘиҜқ пјҢ иҮід»ҠиҗҰз»•жҲ‘еҝғеӨҙ гҖӮ
6 еӨ–ж–Үзі»зҡ„еӨ©з©ә
жҡ‘еҒҮжҲ‘дёҺеҗҢдјҙж¬ўеӨ©е–ңең°з”ұдә”йҖҡжЎҘжҗӯеІ·жұҹжұҹиҪ®еҲ°е®ңе®ҫ пјҢ з”ұй•ҝжұҹйЎәжөҒиҖҢдёӢеӣһдәҶйҮҚеәҶ гҖӮ 家 пјҢ еҜ№дәҺжҲ‘жңүдәҶжӣҙзҫҺеҘҪзҡ„ж„Ҹд№ү гҖӮ иў«иҒ”иҖғеҶІж•Јзҡ„дёӯеӯҰеҘҪеҸӢд№ҹйғҪеңЁеҗ„家зӣёиҒҡ пјҢ жңүиҜҙдёҚе®Ңзҡ„еҲ«еҗҺз»ҸйӘҢиҰҒеҖҫиҜү гҖӮ дёҖе№ҙеүҚжҲ‘зӢ¬иҮӘдёҖдәәиў«еҲҶеҸ‘еҲ°йҒҘиҝңзҡ„е·қиҘҝ пјҢ еӣһеҲ°жІҷеқӘеққ пјҢ еҘҪдјјеӨұзҫӨзҡ„еӯӨйӣҒеӣһеҲ°еӨ§йҳҹж –жҒҜд№Ӣең° пјҢ ж¬ўе”ұдёҚе·І гҖӮ ж•…дәӢж–№йқў пјҢ ж—Ҙжң¬йЈһжңәеӣ дёәзҫҺеӣҪеҸӮжҲҳиҖҢжҚҹиҖ—еӨӘеӨ§ пјҢ е·Іж— еҠӣеҶҚйў‘з№ҒиҪ°зӮёйҮҚеәҶ пјҢ дё»еҠӣ移еҲ°ж»Үзј…и·Ҝ пјҢ жҜҸж¬ЎеҮәиўӯйғҪиў«дёӯзҫҺеҚҒеӣӣиҲӘз©әйҳҹеӨ§йҮҸеҮ»иҗҪ гҖӮ иҝҷдёҖе№ҙеӨҸеӨ© пјҢ йҮҚеәҶиҷҪ然д»ҚжҳҜзӮҷзғӯеҰӮзҒ«зӮү пјҢ еӣ дёәдёҚеҶҚеӨ©еӨ©и·‘иӯҰжҠҘ пјҢ йҮҚе»әдёҺдҝ®еӨҚзҡ„ж°”ж°ӣ пјҢ еҫҲйҖӮеҗҲжҲ‘们иҝҷзҫӨеҸҪеҸҪе–іе–іеҲ°еҗ„家йҮҚиҒҡзҡ„еӨ§дёҖеҘіз”ҹ гҖӮ жңүжңҲдә®зҡ„жҷҡдёҠ пјҢ жҲ‘们常еҺ»еҳүйҷөжұҹиҫ№е”ұжӯҢе’Ңи°Ҳеҝғ гҖӮ йӮЈеӨ§зәҰжҳҜжҲ‘дёҖз”ҹдёӯжңҖеҝ«д№җзҡ„еӨҸеӨ© пјҢ д№ҹжҳҜзңҹжӯЈж— еҝ§зҡ„еҒҮжңҹ гҖӮ
еӣһеҲ°е®¶еҪ“然иҰҒе’ҢзҲ¶жҜҚе•ҶйҮҸиҪ¬зі»зҡ„дәӢ гҖӮ зҲёзҲёиҷҪжңӘжҳҺиҜҙвҖңжҲ‘ж—©е°ұзҹҘйҒ“дҪ еҝөдёҚдәҶе“ІеӯҰзі»вҖқ пјҢ дҪҶд»–иҜҙ пјҢ дҪ ж„ҹжғ…йҮҚдәҺзҗҶжҷә пјҢ еҝөж–ҮеӯҰжҜ”иҫғеҗҲйҖӮ гҖӮ жҲ‘еҸҲж•…дҪңиҪ»жқҫең°иҜҙиҘҝеҚ—иҒ”еӨ§еҺ»е№ҙеҸ‘жҰңеҗҺжӣҫж¬ўиҝҺжҲ‘еҺ»еӨ–ж–Үзі» пјҢ еҚ—ејҖеҗҢеӯҰеңЁйӮЈйҮҢеҫҲеӨҡ пјҢ жҲ‘д№ҹеҫҲжғіеҺ» пјҢ еҰӮжһңжҲҳдәүиғңеҲ© пјҢ жҲ‘д№ҹеҸҜд»ҘеӣһеҲ°еҢ—еӨ§гҖҒжё…еҚҺжҲ–еҚ—ејҖеӨ§еӯҰвҖҰвҖҰзҲёзҲёйқўиүІеҮқйҮҚең°иҜҙ пјҢ зҫҺеӣҪеҸӮжҲҳеҗҺ пјҢ дё–з•ҢжҲҳеұҖиҷҪеӨ§жңүиҪ¬жңә пјҢ жҲ‘们еӣҪеҶ…жҲҳзәҝеҚҙжҢ«иҙҘиҝһиҝһпјӣж№–еҚ—жІҰйҷ· пјҢ е№ҝиҘҝеҚұжҖҘ пјҢ иҙөе·һдәҰе·ІдёҚдҝқ пјҢ вҖңдҪ еҲ°дә‘еҚ— пјҢ зҰ»е®¶жӣҙиҝң гҖӮ д№җеұұиҷҪ然д№ҹиҝң пјҢ еҲ°еә•д»ҚеңЁеӣӣе·қ пјҢ жҲ‘з…§йЎҫдҪ жҜ”иҫғиҝ‘дәӣ гҖӮ е…¶е®һд»ҘдҪ зҡ„иә«дҪ“ пјҢ жңҖеҘҪз”іиҜ·иҪ¬еӯҰдёӯеӨ®еӨ§еӯҰ пјҢ з•ҷеңЁжІҷеқӘеққ пјҢ д№ҹе°‘и®©жҲ‘们жӮ¬еҝө пјҢ еұҖеҠҝеҰӮеҸҳжӣҙеқҸ пјҢ жҲ‘们дёҖ家дәәиҮіе°‘еҸҜд»ҘеңЁдёҖиө·вҖқ гҖӮ
жҲ‘еӣһ家дёҚ久收еҲ°еӨ§йЈһе“Ҙзҡ„дҝЎ пјҢ д»–еқҡеҶідёҚиөһжҲҗжҲ‘иҪ¬еӯҰеҲ°жҳҶжҳҺеҺ» пјҢ д»–йҡҸж—¶иҝҒ移驻йҳІеҹәең° пјҢ е®һеңЁжІЎжңүиғҪеҠӣз…§йЎҫжҲ‘пјӣжҲҳдәүзҺ°еҶөдёӢ пјҢ иҝһдёүеӨ©еҒҮжңҹйғҪжІЎжңү пјҢ д№ҹжІЎжңүеҠһжі•еӣһеӣӣе·қзңӢжҲ‘ пјҢ жңӣжҲ‘е®үеҝғең°еӣһд№җеұұиҜ»д№Ұ пјҢ еӨ§е®¶е”ҜдёҖзҡ„з”ҹи·ҜжҳҜжҲҳдәүиғңеҲ© гҖӮ иҝҷж—¶д»–зҡ„еҸЈж°”еҸҲжҳҜе…„й•ҝеҜ№е°ҸеҘіеӯ©иҜҙиҜқдәҶ гҖӮ
еңЁиҝҷжңҹй—ҙ пјҢ жҲ‘д№ҹжӣҫиҜ·ж•ҷгҖҠж—¶дёҺжҪ®ж–ҮиүәгҖӢзҡ„дё»зј–еӯҷжҷӢдёүж•ҷжҺҲжңүе…іжңұе…үжҪңе…Ҳз”ҹзҡ„е»әи®® гҖӮ еӯҷе…Ҳз”ҹеҪ“ж—¶жҳҜдёӯеӨ®еӨ§еӯҰеӨ–ж–Үзі»зҡ„еҗҚж•ҷжҺҲ пјҢ жһҒеҸ—жҲ‘зҲ¶дәІзҡ„е°ҠйҮҚ гҖӮ еңЁд»–дё»жҢҒд№ӢдёӢ пјҢ гҖҠж—¶дёҺжҪ®ж–ҮиүәгҖӢзҷ»иҪҪжІҲд»Һж–ҮгҖҒе·ҙйҮ‘гҖҒжҙӘж·ұгҖҒеҗҙз»„зјғгҖҒиҢ…зӣҫгҖҒжңұе…үжҪңгҖҒй—»дёҖеӨҡгҖҒжңұиҮӘжё…гҖҒзҺӢиҘҝеҪҰгҖҒзў§йҮҺгҖҒиҮ§е…Ӣ家гҖҒеҫҗзӯүзҡ„ж–°дҪңе“Ғ пјҢ 他们дёҚд»…еҪ“ж—¶е№ҝеҸ—иҜ»иҖ…ж¬ўиҝҺ пјҢ дәҰжҳҜзҺ°д»Јж–ҮеӯҰеҸІдёҠзҡ„йҮҚиҰҒдҪң家 гҖӮ иҖҢжҹіж— еҝҢгҖҒжқҺйңҒйҮҺгҖҒж–№йҮҚгҖҒжқҺй•ҝд№ӢгҖҒеҫҗд»Іе№ҙгҖҒдәҺиө“иҷһгҖҒиҢғеӯҳеҝ гҖҒйҷҲзҳҰз«№гҖҒжҲҙй•Ҹйҫ„гҖҒдҝһеӨ§гҖҒеҸ¶еҗӣеҒҘзӯүдәәзҝ»иҜ‘зҡ„еҗ„еӣҪз»Ҹе…ёдҪңе“Ғ пјҢ д№ҹйғҪеҸҜд»ҘзңӢеҮәйӮЈдёӘж—¶д»Јж–Үдәәзҡ„й«ҳж°ҙеҮҶ гҖӮ жҜҸжңҹйғҪжңүж–ҮеқӣеҠЁжҖҒе’ҢеӣҪеҶ…еӨ–иүәж–Үжғ…жҠҘ пјҢ жҳҜдёҖд№қеӣӣдәҢиҮідёҖд№қеӣӣдә”е№ҙй—ҙзҡ„зҸҚиҙөи®°еҪ• гҖӮ еҸҜжғңжҠ—жҲҳиғңеҲ©дёҚд№…еӣҪе…ұжҲҳдәүеҚіиө· пјҢ жҲ‘зҲ¶дәІе·Іж— еҠӣж”Ҝж’‘дёүд»ҪжңҹеҲҠ пјҢ гҖҠж—¶дёҺжҪ®ж–ҮиүәгҖӢдәҺдёҖд№қеӣӣдә”е№ҙеҒңеҲҠ 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е…»з”ҹиҖҒеёҲиҜҙиҗҘе…»|жһ«йҰҷеҸ¶жҳҜдёҖдёӘиҚҜжқҗпјҢе‘ійҒ“зү№еҲ«зҡ„йҰҷпјҢиҝҳжңүејәеӨ§зҡ„еҠҹж•ҲпјҒдёҖе®ҡ收и—ҸзңӢ
- е·Ёжө·жҲҗжқ°иҖҒеёҲ|е·ҘдҪңи¶ҠеҒҡи¶ҠзҙҜжҖҺд№ҲеҠһпјҹж•ҷдҪ 3жӢӣи®©йўҶеҜјж»Ўж„ҸпјҢдёҚ然зҙҜжӯ»д№ҹеҫ—дёҚеҲ°жҸҗжӢ”
- еӯ©еӯҗ|жҡ‘еҒҮжқҘдәҶпјҢиҝҷдәӣйҳІжәәж°ҙзҹҘиҜҶ家й•ҝе’ҢиҖҒеёҲ们дёҖе®ҡиҰҒи®Із»ҷеӯ©еӯҗеҗ¬
- жҳҹеә§|еҜ№зҲұжғ…е§Ӣз»ҲеҰӮдёҖзҡ„жҳҹеә§пјҢ收иҺ·зҡ„йғҪжҳҜж»Ўж»Ўе№ёзҰҸпјҒ
- з”ҹиӮ–|жҮӮеҫ—жӣҝеҸҰдёҖеҚҠзқҖжғіпјҢдёҚдјҡи®ЎиҫғеӨӘеӨҡпјҢеҫҲеҝ«е°ұиғҪеӨҹ收иҺ·е№ёзҰҸзҡ„з”ҹиӮ–
- з”ҹиӮ–|дёҖж—ҰжҠ•е…ҘдёҖж®өж„ҹжғ…е°ұдјҡйқһеёёз”ЁеҝғпјҢеҫҲеҝ«ж”¶иҺ·еұһдәҺиҮӘе·ұзҲұжғ…зҡ„з”ҹиӮ–
- йғ‘委иҖҒеёҲ|ж— и®әзҲұдёҺе№ёзҰҸжҖҺд№Ҳж ·пјҢдҪ еҸӘиҰҒжҲҗй•ҝиҮӘе·ұе°ұеҘҪ
- з”ҹиӮ–еӨңиҜ»|7жңҲеә•пјҢж—§жғ…дәәжғҠж…ҢеӨұжҺӘпјҢжңҹеҫ…еӨҚеҗҲпјҢ3з”ҹиӮ–ж—§жғ…еӨҚзҮғпјҢд»Ҙ收иҺ·е®үе…Ёж„ҹ
- е°ҸзҺІжҳҹеә§|иҝ‘жңҹпјҢеӣӣеӨ§з”ҹиӮ–ж— еӨ„е®үж”ҫзҡ„йӯ…еҠӣдјҡеҸ—еҲ°йқ’зқҗпјҢдјҡ收иҺ·жңҖжё©жҹ”зҡ„зҲұжғ…пјҒ
- жЁӘжқҗ|7жңҲеә•пјҢжңҖеҗҺ10еӨ©пјҢжңүжЁӘжқҗд»ҺеӨ©иҖҢйҷҚпјҢж„ҸеӨ–收иҺ·йўҮеӨҡпјҢе–ңдәӢиҝһиҝһпјҢжҢЎйғҪжҢЎдёҚдҪҸ3з”ҹи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