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梦蝶、悼亡与旅行:青年本雅明的爱与迷狂( 二 )
谈及此处 , 就不能不提到本雅明写作《彩虹》同时倾心已久的荷尔德林 。
本雅明在1914年冬天着手已经小有积累的荷尔德林研究 , 之后形成了他的第一篇论文《论荷尔德林的两首诗》
(“Zwei Gedichte von Friedrich H?lderlin”)
。 1916年初他致赫伯特·贝尔莫赫
(Hebert Belmore)
的信提及同时完成了这两部作品 。 这年底他向这位早年的知交讲述了自己的批评观念 。
批评应触及对象物的灵魂 , 如同化学物质分解事物 , 于毫发无损中呈现其内在 , 好比一道光洞穿其中 。 而奠定这一批评观念的是荷尔德林多年来的启示:生命必须从一切名、言和征兆的灵魂之中寻求 。 《论荷尔德林的两首诗》分析《诗人之勇气》
(“Dichtermut”)
、《虚弱》
(“Bl?digkeit”)
时提到了荷尔德林后期诗作中“神圣的清醒” , 指向了诗人的灵魂状态 。 那是一种悖论式的勇敢本质 , 敢于完全被动 , 在完全投身于世界的关系中 , 与之纯然合一 。
荷尔德林还以此总括德意志这个夕域的
(abendl?ndish)
民族秉性 , 那是天神“尤诺式的清醒无华”
(Junonische Nüchternheit)
。 而这在本雅明稍后《评歌德的<亲和力>》
(“Goethes Wahlverwandtschaften”, 1924—1925)
一文化为德国艺术实践的最终目标 。 “脱离表达/言外之物”
(Ausdruckslos)
这个术语在构词上的张力一望而知 , 显示了超越有机形式的倾向 。
这个启发来自本雅明对荷尔德林关于肃剧韵律反常合道的形态——停顿
(Z?sur)
的领会 。 说到底 , 言说愈少意味着诗人不受自身感知意识的支配 。 如此而言 , 清醒之所以被称为神圣、至高状态 , 是因为诗人不再受到人的主观意识局限 。 与万有合为一体意味着生命因之化为纯机能的运行 。
荷尔德林的思路来自于与万有合一的真切体验 , 不妨说其写作念兹在兹的便是这个神圣状态 。 绝对合一被他称作“存在” , 那是主体与客体如此密切地合二为一 , 因而不会有任何人类的意识判断萌发出来
(《初断与存在》“Urteil und Sein” , 1794/95)
。 存在的体会发端于荷尔德林对柏拉图《会饮》之美的了悟 。 凡人通过灵魂瞥视与美融为一体 , 美本身“自体自根、自存自在 , 永恒地与自身为一” 。
若触及合一的幽微瞬间 , 就不能不提到荷尔德林熟读的《斐德若》 , 苏格拉底讲述美的迷狂状态时提到了一个精彩绝伦的灵魂活动 。 真正的美来自一个灵魂长出翅翼的活动 , 伴随着苦乐交织的奇妙感知 。 荷尔德林引用赫拉克利特的箴言以蔽其奥妙:“在自身中与本己相异的太一”
(εν διαφερον εαυτ?, das Eine in sich selber unterschiedne)
。
可以说 , 美的体验并非羚羊挂角不落痕迹 , 唯有人出离自身意识 , 也就是说在感知判断消亡的情形下才是进入太一的途径 。 《会饮》中介于人神之间生育灵魂的精灵爱若斯最为恰切地代表这一奥妙 。 爱若斯在古希腊创世神话中本身就是一位身着羽翼推动万物繁衍的创世神 , 在贫乏与丰盈之间不息转变的样态代表着人类从分裂走向合一生生不息之规律 。
在经验贫乏的时代 , 寻找生育灵魂的爱若斯
一些相似的言说隐约地透视出本雅明对荷尔德林这一意识转化的领会 。 在1925年那部关于德国肃剧的《认识论批判导言》中 , 他以柏拉图美的理念作为真理内容 , 那已不再是先验哲学的预先规定 , 而是人主观意图的“消亡” 。 早在那篇探讨迷醉的对话草稿中 , 他还构造了去知直观一词 , 与观念论前辈们“智性直观”的言说形成了鲜明对照 , 展露出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先辈的对立面 。
如此来看 , 本雅明在1930年代《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谈论Aura时引介的那个意识消失的中国画家传说 , 实在是去知直观的完美例证 。 这也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本雅明在巴黎《国家图书馆的中国画》
推荐阅读
- 新京报|抑郁症患者不是天天想着自杀,他们无时不刻不在承受折磨
- 新京报|好玩│北京繁华秋景将至,去这些“赏秋”打卡点看展品美味
- 新京报|抑郁症患者背后的“燃灯人”
- 新京报|质朴的夜晚
- 新京报|露易丝·格丽克诗歌选读
- 新京报|格丽克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保守选择?
- 新京报|格丽克诗歌的艺术特征
- 新京报|13岁“猪坚强”已相当于人类百岁,国庆每日有千余人探访
- 新京报|国庆假期北京特色商街人气高,前门大街、南锣鼓巷日均客流超8万
- 新京报|“十八弯”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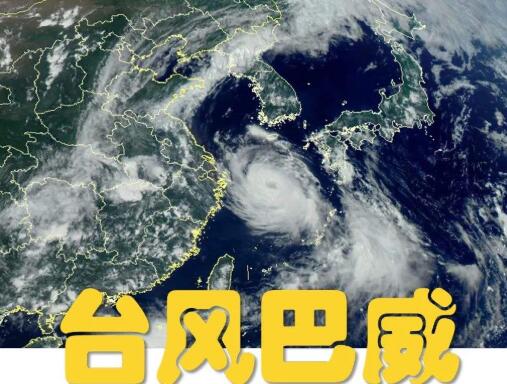



![[芬姨的故事会]国乒队在澳门进行混上循环对抗赛!王楚钦和孙颖莎排名第二!](https://imgcdn.toutiaoyule.com/20200418/20200418154109944806a_t.jp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