дёӯеҺҹдҪң家зҫӨ|иҢғжҖҖжҷәпҪңжҲ‘еңЁжҷЁе…үжҪңе…Ҙзңјзһізҡ„зғ§зҒјйҮҢпјҢе“Үе“Үе“ӯеҸ«вҖҰвҖҰ( дёү )
зҹ®жЎғж ‘гҖҒж јеӯҗзӘ—еҗҺзҡ„еӨ§дјҜй—®пјҡвҖңж–ҮзӨјжҲҗе©ҡдәҶпјҹвҖқ
зҘ–зҲ¶зҡ„еӣһзӯ”жҳҜпјҡвҖңжҲҗдәҶ пјҢ ж–ҮзӨјзҡ„е№ҙеІҒдёҚе°ҸдәҶ пјҢ жҜ”дёҚеҫ—дҪ еңЁеӨ–зҡ„дәә гҖӮ иҖҒжңүеӨ§жғіжі• пјҢ иҖҒеҮҶеӨҮе№ІдәӢгҖҒеҫҖеӨ§е“©е№ІдәӢ гҖӮ ж–ҮзӨјжҳҜдёӘе®һеңЁеЁғ пјҢ еҜ№ж—ҘжңҲиҺ«е•Ҙйқһд»ҪжғіеӨҙ пјҢ д№ҹдёҚи°ӢжұӮеј„дёӘе•ҘеӨ§дәӢжғ… гҖӮ ж–ҮзӨјд№ҹжІЎе•Ҙй•ҝеӨ„ пјҢ е°ұеҚ дёӘе®һиҜҡгҖҒеӢӨеҝ«гҖҒиғҪеҗғиӢҰ пјҢ иҝҷе°ұеӨҹдәҶ гҖӮ еүҚе№ҙи…ҠжңҲз»ҷжҲҗдәҶе©ҡ пјҢ д»Ҡе№ҙжӯЈжңҲйҮҢжңүдәҶеЁғ гҖӮ вҖқ
вҖңжҳҜе„ҝеЁғд№ҲпјҹвҖқ
вҖңжҳҜе„ҝеЁғпјҒвҖқ
вҖңйӮЈ пјҢ зҲ№е’ҢеЁҳ пјҢ е°ұеҚ дҪҸдәҶдёҖйў—еҝғд№ҲпјҒвҖқ
зҘ–зҲ¶е‘өе‘ө笑дәҶ пјҢ йЎәжүӢжҠ№дәҶжҠҠ干涩зҡ„йј»еӨҙ пјҢ дҫ§ж–ңиҝҮиә«еҺ» пјҢ жӢҪд»–жһ•еӨҙйӮЈж—Ғзҡ„зғҹжқҶ гҖӮ зі»з»‘зғҹжқҶдёҠзҡ„й»‘зғҹиўӢжҳҜжҜҚдәІе«ҒеҲ°жҲ‘家еұӢйҮҢзҡ„еӨҙе№ҙ пјҢ жҡ‘дјҸеӨ©еӣһеЁҳ家иҝҮй—Ёж—¶ пјҢ жҢү规зҹ©дё“ж„Ҹз»ҷзҘ–зҲ¶зјқеҲ¶зҡ„ пјҢ е…¶дёҠз»ЈдәҶйҮ‘й»„иүІзҡ„и…Ҡжў…иҠұ гҖӮ зҘ–зҲ¶жІЎеҰӮеә„йҮҢзҡ„е…¶д»–дёҠдәҶе№ҙеІҒзҡ„дәә пјҢ дёҖжқҶжҺҘдёҖжқҶжө“зғҹж»ҡж»ҡзқҖе–ңйЈҹиҚүзғҹзҡ„е—ңеҘҪ гҖӮ зҘ–зҲ¶д»…еңЁеҝғж»Ўж„Ҹи¶ігҖҒйҡҫдәҺжҠ‘еҲ¶ж¬ўж¬Јзҡ„еҪ“еҸЈ пјҢ жүҚжӢҪеҮәд»–зҡ„зғҹжқҶзғҹиўӢ пјҢ еғҸи№ІеңЁжІіжІҝдёҠе®Ўи§Ҷе®ғе„ҝеӯҷж»Ўе Ӯзҡ„жҜҚйёӯ пјҢ жҶӢзқҖеҳҙе„ҝ пјҢ еҗ§е—’еҗ§е—’ең°еҗёдёӘжІЎе®ҢжІЎдәҶ гҖӮ зҘ–жҜҚжҠҝдәҶжҠҝеҳҙ пјҢ 笑зңҜзңҜдәҶдёҖеҲ» пјҢ еҫҖеүҚжҢӘдәҶдёӢиә«еӯҗ пјҢ дёӢеҫ—зәўжјҶеҮі пјҢ иө°еҫҖзҰҮзәўиүІзҡ„з»Ҹе№ҙзҙҜжңҲзҡ„жңЁжҹң пјҢ еҫҖжҹңйқўдёҠеҸ–дёӢеҘ№е№ҙиҖҒзҡ„зәҝиҪ®гҖҒеңҹең°ж ·еҸ‘й»„зҡ„йә»дёқ гҖӮ йҡҸд№Ӣе°Ҷж–°дёқз»ӯдёҠзәҝиҪ®жӯЈдёӯзҡ„еҸ‘й»‘й“ҒеӢҫ гҖӮ й“Ғй’©дёҠзј з»•зқҖж—§дёқ гҖӮ еҘ№е·ҰжүӢжӢҺй«ҳзәҝиҪ® пјҢ еҸіжүӢжӢЁеҠЁзқҖ пјҢ зәҝиҪ®дёҚеҒңжӯҮең°ж—ӢиҪ¬иө·жқҘ пјҢ жңЁеҲ¶зҡ„зәҝиҪ®еңЁж–°йә»зәҝзҡ„йЎ¶з«Ҝ пјҢ еҗҢеҗҠе…Ҙж·ұдә•зҡ„ж°ҙжЎ¶дёӢжІүдәҶпјӣж–°зҡ„йә»зәҝдёҖеҜёдёҖеҜёз”°й—ҙзҡ„зҰҫиӢ—дјјзҡ„й•ҝжҲҗзқҖ гҖӮ йә»зәҝдҫқж—§жҳҜеңҹең°зҡ„йўңиүІпјӣжүҖжңүзҶҹйҖҸдәҶзҡ„зү©з§ҚзұҪйЈҹ пјҢ йғҪеңЁеңҹең°иүІжіҪең°еҢ…иЈ№гҖҒжөёж¶Ұдёӯ гҖӮ жҲ‘иҝңеңЁж–°з–Ҷзҡ„еӨ§дјҜжҜҚ пјҢ жңӘиғҪж»Ўи¶ізҘ–жҜҚзҡ„жёҙжңӣе„ҝеӯҷзҡ„ж¬ІжұӮ гҖӮ
зҘ–жҜҚиҜҙпјҡвҖңж–Үе–ңе‘Җ пјҢ е®қз«№е•Ҙж—¶еҖҷ пјҢ д№ҹиғҪз»ҷеЁҳеҫ—дёӘе„ҝеӯҷе“© гҖӮ вҖқ
жҲ‘з«ҜжӯЈзҡ„еқҗзӮ•йқўдёҠзҡ„дјҜзҲ¶з¬‘笑 пјҢ жү“ејҖзӣҳеқҗзқҖзҡ„еҸҢи…ҝ пјҢ дјёеұ•дәҶи…°иә« пјҢ йЎәеҠҝжӢҪдәҶжӢҪз»·зҙ§еңЁи„ҡејҜдёҠзҡ„иЈӨи§’ гҖӮ
вҖңеЁҳ пјҢ е„ҝеӯҷи·ҹеҘіеӯҷдёҖж ·еҳӣ пјҢ йғҪжҳҜдҪ еӯҷеӯҗе“© гҖӮ ж–ҮжҲҗ家дёӨдёӘе„ҝеӯҗ пјҢ ж–ҮзӨје®¶ж–°еҫ—дәҶе„ҝеӯҗ пјҢ е’ұ家дёүдёӘе„ҝеӯҷ пјҢ дёӨдёӘеҘіеӯҷпјӣдёүжҜ”дәҢ пјҢ еҘіеЁғеЁғиҝҳж¬ е°‘е“© гҖӮ еҶҚиҜҙ пјҢ еЁҳе·ІжңүдәҶдёүдёӘе„ҝеӯҷдәҶ пјҢ еЁҳиҜҘзҹҘи¶ідәҶ гҖӮ вҖқ
зҘ–зҲ¶ж”ҘдҪҸзғҹжқҶ пјҢ зғҹдёқж»ҡжІёзҡ„йқўжұӨж · пјҢ еҗҢж—¶жәўеҮәйј»еӯ”гҖҒеҳҙе·ҙгҖҒй»„й“ңзҡ„зғҹй”… пјҢ еҰӮеҲқз§Ӣзҡ„йӣЁж°ҙж¶Ңж·Ңеҫ—еҗ„еӨ„зҡҶжҳҜ пјҢ еұӢй—ҙжҷҢеҚҲж—¶еҲҶзҡ„зғҹзҶҸзҡ„е‘іж„ҲжқҘж„Ҳжө“ гҖӮ зҘ–жҜҚеҫҖеҳҙи§’жҠҝдәҶдёҖеҸЈ пјҢ еҮ ж—ҘеүҚзҗҶйЎәдәҶж”ҫеҲ°зҰҮзәўиүІжҹңйқўдёҠгҖҒз”ұйқӣи“қиүІжүӢеё•еҢ…иЈ№зҡ„йә»дёқ пјҢ йә»дёқи„ұиҗҪжқҫж•Јзҡ„дёҖзј•зІҳеҲ°дәҶзҘ–жҜҚеҳҙи§’дёҠ пјҢ еғҸзҘ–жҜҚеҳҙи§’зІҳдҪҸдәҶдёҖзј•ж–°жҳҘзҡ„йҳіе…ү гҖӮ
зҘ–жҜҚиҜҙпјҡвҖңи°ҒеҖ’иҜҙжҳҜеҘіеЁғеЁғдёҚеҘҪпјҹеЁҳжҳҜиҜҙеҘіеЁғеҘҪ пјҢ з”·еЁғеӯҗд№ҹеҘҪ гҖӮ дҪ иҜҙе…үжҳҜиҜҙз”·еЁғеЁғеҘҪ пјҢ еҘіеЁғеЁғдёҚеҘҪ пјҢ йӮЈеҫҖеҗҺ пјҢ з”·еЁғеӯҗиҰҒеЁ¶дёӘеӘіеҰҮ пјҢ жҲҗдёӘ家 пјҢ жҖ•йғҪйҡҫеҫ—еҫҲе“© гҖӮ еЁҳжҳҜиҜҙ пјҢ дҪ жңүдәҶдёӨдёӘеҘіеЁғ пјҢ д№ҹиҜҘжңүдёӘз”·еЁғеӯҗ пјҢ ж–ҮжҲҗж–ҮзӨј пјҢ д№ҹиҜҘжңүдёӘеҘіеЁғеӯҗ гҖӮ еҶҚиҜҙ пјҢ еЁҳд№ҹжҳҜдёәдҪ и°ӢеҲ’е“© пјҢ еҘіеЁғ家 пјҢ з»ҲжҳҜеҲ«е®¶зҡ„дәә пјҢ еҝғйҮҢеҖ’жңүзқҖзҲ№еЁҳ пјҢ 究з«ҹжҳҜиҮӘ家еҒҡдёҚеҫ—иҮӘ家зҡ„дё» гҖӮ еҶҚжңү пјҢ е°ұжҳҜеҘіеЁғеӯҗдёҖжңүдәҶ家е®Ө пјҢ е°ұжҒӢ家еҫ—еҫҲе“© гҖӮ еҲ°дҪ дёҠдәҶе№ҙеІҒ пјҢ жҖ•жҳҜиҝһдёӘдҫқйқ гҖҒеё®жүӢйғҪиҺ«пјҲжІЎпјүе“© гҖӮ вҖқ
жҲ‘иҝҳжңӘжӣҫзӣёиҜҶзҡ„еӨ§дјҜ пјҢ иӢҘеӣһеҲ°дәҶд»–е№ҙе°‘ж—¶зҡ„еңҹзӮ•йӮЈж · пјҢ е®Ңе…ЁдјёзӣҙдәҶеҸҢи…ҝ пјҢ еҫҖиө·жӢҪжӢүдәҶеҮ дёӢд»–жң¬жқҘе®Ҫйҳ”зҡ„иЈӨи…ҝ гҖӮ
зҘ–жҜҚиҜҙпјҡвҖңж–Үе–ңжҜ”дёҠеӣһеӣһжқҘ пјҢ иғ–дәҶ пјҢ зҷҪдәҶ гҖӮ вҖқ
дёҖж—Ғ пјҢ жҖ»е–ңи№ІеҲ°зӮ•йқўзҡ„зҘ–зҲ¶ пјҢ жӯҮдәҶжӯҮд»–ж¬ўж¬Јзҡ„еҗёйЈҹиҚүзғҹзҡ„дёҫеҠЁ пјҢ иҝҷж¬Ўе·ҰжүӢжҸЎдҪҸзҡ„зғҹжқҶ пјҢ еҫ„зӣҙе°Ҷй»„й“ңзҡ„зғҹй”…зӘқиҝӣд»–йҮ‘й»„иүІи…Ҡжў…зҡ„зғҹиўӢйҮҢпјӣеҮӯеҖҹеҸіжүӢең°и§Ұж‘ё пјҢ еҫҖй»„й“ңзҡ„зғҹй”…йҮҢжҸүжҚҸзқҖеңҹең°йўңиүІзҡ„зғҹдёқ гҖӮ еңЁиҝҷиӢҚиҢ«зҡ„зҺҜе®Үй—ҙ пјҢ дёҚи®әи‘өиҠұзҡ„йҮ‘й»„гҖҒе…°иҚүзҡ„й’ўи“қгҖҒзҒ«з„°зҡ„еҪӨзәўгҖҒиҺІиҠұзҡ„зӮҪзҷҪгҖҒжЎғиҠұзҡ„ж·ЎзІүгҖҒзҹіжҰҙзҡ„ж©ҷгҖҒж ‘еҸ¶зҡ„з»ҝгҖҒзүөзүӣзҡ„зҙ«вҖҰвҖҰйғҪжҳҜеңҹең°зҡ„йўңиүІзҡ„з§Қз§Қе‘ҲзӨә гҖӮ зҘ–зҲ¶еә”е‘өдәҶзҘ–жҜҚзҡ„иҜқиҜӯ гҖӮ
зҘ–зҲ¶е—ҜдәҶеЈ° гҖӮ вҖңе—Ҝ пјҢ ж–Үе–ңжҳҜзҷҪдәҶ пјҢ жҳҜиғ–дәҶдәӣ гҖӮ вҖқ
з”ұд№ЎйҮҺйҮҢзҡ„й•ӮзҹіиүәдәәгҖҒй•ӮжҲҗзҡ„йқ’зҹіеӨҙзҡ„зғҹе’Җ пјҢ е‘ҲдёҖжҠ№йқ’дә‘йўңиүІ гҖӮ йқ’зҹіеӨҙзҡ„зғҹе’ҖеҸ®е’ЈдёҖе“Қ пјҢ еҸҲеҸЁеңЁдәҶзҘ–зҲ¶й»„иүІзҡ„зүҷйҪҝгҖҒе’ҢзҶҹйҖҸдәҶжЎ‘д»ҒиҲ¬зҡ„зҙ«д№Ңд№Ңзҡ„еҸҢе”Үй—ҙ пјҢ е°ұеғҸдё“еҸёеҗ№жү“зҡ„д№җеёҲеҸЈйҮҢиЎ”дҪҸдҝ®й•ҝзҡ„жҙһз®« гҖӮ дёҖйў—зәўзҡ„зҒ«жҹҙеҡ“ең°дёҖеЈ°еҲ’иҝҮдәҶй»‘зҡ„зҙ«з Ӯ пјҢ зҒ«жҹҙе—һе•ҰзҮғиө·пјӣжҙһз®«зҡ„йҹөиҮҙиӢҘйқ’иӢҚиӢҚзҡ„жҡ®йңӯ пјҢ жӮ„然е©үиҪ¬зқҖеҚҮиө· гҖӮ зҘ–жҜҚд»ҺеҘ№иҗҪеқҗзҡ„зҢ©зәўжңЁеҮідёҠз«ҷиө· пјҢ е·ҰжүӢжҚҸжӢҪзқҖйә»дёқгҖҒзәҝиҪ® пјҢ еҮ‘иҝ‘зӮ•жІҝеӯҗйӮЈж—ҒгҖҒжӣІиә«дјҸдёҠзӮ•йқў пјҢ жӢүжүҜзқҖеҸ еҫ—ж–№жӯЈгҖҒзҙ§жҢЁж јеӯҗзӘ—зҡ„иў«еӯҗ пјҢ еҫ„зӣҙжүҜеҫҖдәҶжҲ‘еӨҡе№ҙеҗҺ пјҢ зҘ–жҜҚиҝҮдё–еүҚжҳ”ж–№еҸҜзңҹеҲҮи§ҒеҲ°зҡ„ пјҢ з«ҜзӣҙеқҗзӮ•йқўзҡ„жҲ‘еӨ§дјҜиә«еҗҺ 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жӢӣиҒҳ|дёәдҪ•еӣҪдјҒжӢӣиҒҳеҖҫеҗ‘вҖңж ЎжӢӣвҖқпјҢеҫҲе°‘иҝӣиЎҢвҖңзӨҫжӢӣвҖқпјҹе…¶дёӯеҺҹеӣ еҫҲзҺ°е®һ
- иҫ…иӯҰ|иҫ…иӯҰе·Ҙиө„дҪҺпјҢдёәе•ҘиҝҳжңүйӮЈд№ҲеӨҡеӯҰз”ҹжҠҘиҖғпјҹе…¶дёӯеҺҹеӣ еҫҲзңҹе®һ
- жӢӣиҒҳ|дёӨеӨ§иЎҢдёҡвҖңжӢӣе·ҘиҚ’вҖқпјҢжңҲи–ӘдёҮе…ғд№ҹж— дәәеҺ»пјҢжҜ•дёҡз”ҹдёҖиҜӯйҒ“з ҙе…¶дёӯеҺҹеӣ
- |жҳҺжҳҺеҮҸжҺүдәҶ10еӨҡж–ӨпјҢжҖҺд№ҲзңӢдёҚеҮәеҸҳзҳҰдәҶпјҹзңӢе®ҢдҪ жҲ–зҹҘйҒ“е…¶дёӯеҺҹеӣ дәҶ
- иҖғиҜ•|дёәе•Ҙе…¬еҠЎе‘ҳиҖғиҜ•пјҢеҫҲе°‘зңӢи§Ғ211гҖҒ985еӨ§еӯҰз”ҹпјҹе…¶дёӯеҺҹеӣ еҫҲзҺ°е®һ
- дёӯеҺҹдҪң家зҫӨ|е®үе®ҮеҪұпјҡжҲ‘зҲұж·ұз§Ӣзҡ„йЈҺпјҲеӨ–дёҖзҜҮпјүпҪңж•Јж–ҮйҖүиҜ»
- дёүеӣҪдёӨжҷӢеҚ—еҢ—жңқ|иҜёи‘ӣдә®еҸ«е–ҠзқҖ收еӨҚдёӯеҺҹпјҢдёәдҪ•еҚҙи¶ҹи¶ҹеҫҖз”ҳиӮғи·‘пјҹд»–зҡ„и®Ўи°Ӣе°ҪжҳҫиҖҒиҫЈ
- дёӯеҺҹдҪң家зҫӨ|зҪ—иҘҝпјҡдҪҷз”ҹжІЎйӮЈд№Ҳй•ҝпјҢиҜ·жҙ»еҫ—зңҹе®һдёҖзӮ№пҪңеҗҚ家йҳ…иҜ»
- дёӯеҺҹдҪң家зҫӨ|жқҺдҪ©з”«пјҡиҜ—жӯҢжҳҜж—¶д»Јз”ҹжҙ»зҡ„дёҠйҷҗпҪңеҗҚ家и°ҲеҲӣдҪң
- дёӯеҺҹдҪң家зҫӨ|з”°жҷ“еҚҺпјҡ马иҫҫеҠ ж–ҜеҠ 34еҸ·е…¬и·ҜпјҲиҠӮйҖүпјүпҪңж–°иҜ—иҚҗиҜ»жқҘжәҗпјҡйқ’е№ҙиҜ—дәәпјҲеҫ®дҝЎе…¬дј—еҸ·пј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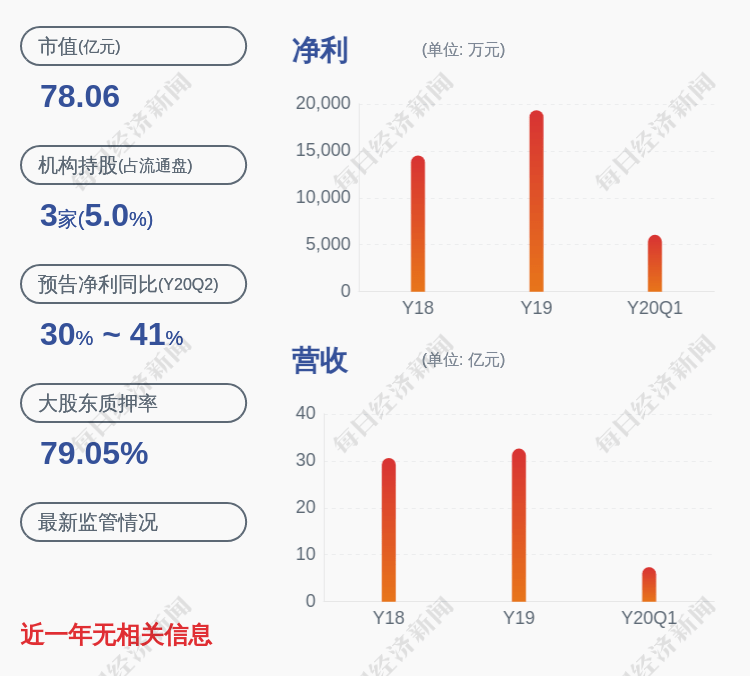
![[]银иЎҢе‘ҳе·Ҙпјҡеӯҳж¬ҫиҫҫеҲ°вҖңиҝҷдёӘж•°вҖқпјҢжҜҸжңҲеҲ©жҒҜзӣёеҪ“дәҺеҫҲеӨҡдәә2дёӘжңҲе·Ҙиө„](http://img88.010lm.com/img.php?https://image.uc.cn/s/wemedia/s/upload/2020/853d39c4ad136e01fcfb3249ceeb873d.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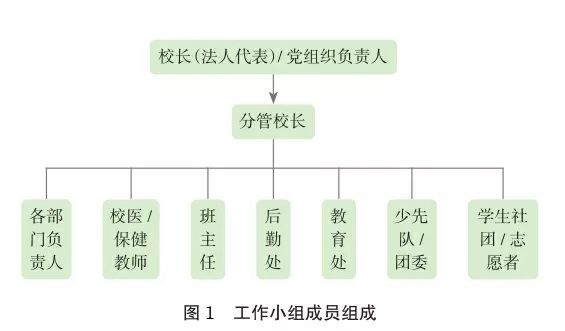


![[зҶҠеӯ©еӯҗд№җеӣӯ]д»ҺжқҘдёҚеҒҡиҝҷдёү件дәӢпјҢдәәзјҳи¶ҠжқҘи¶ҠеҘҪпјҢдәәйҷ…дәӨеҫҖ规еҲҷпјҡжғ…е•Ҷй«ҳзҡ„дәә](https://imgcdn.toutiaoyule.com/20200330/20200330145713047207a_t.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