д»Һиҷҗеҫ…еҠЁзү©еҲ°иҷҗеҫ…дәәпјҢиғҢеҗҺжңүзқҖе…ұеҗҢзҡ„еҝғзҗҶеҹәзЎҖ( дәҢ )

и—Ҹж—Ҹ姑еЁҳжӢүе§Ҷ гҖӮеҪ“и®ёеӨҡи®Ёи®әж¶үеҸҠеңЁгҖҠеҸҚ家еәӯжҡҙеҠӣжі•гҖӢе·Із»Ҹе®һж–Ҫеӣӣе№ҙзҡ„еҪ“дёӢеҚҙдҫқж—§еҮәзҺ°еҰӮжӯӨеӨҡзҡ„家жҡҙе’Ңиҷҗеҫ…дәӢ件еҫ—дёҚеҲ°жңүж•ҲеӨ„зҗҶж—¶ пјҢ жҲ‘们д№ҹдёҚиғҪеҝҪи§ҶжӢүе§ҶеүҚеӨ«зҡ„иҷҗеҫ…еҝғзҗҶдёҺиЎҢдёәдёәдҪ•ж— жі•дҝ®жӯЈжҲ–иў«йҳ»жӯўзҡ„еҺҹеӣ гҖӮ еңЁжҹҗз§ҚзЁӢеәҰдёҠ пјҢ е°ұеҰӮиҷҗеҫ…еҠЁзү©дёҖж · пјҢ 家жҡҙеҗҢж ·жҳҜдёҖз§Қжңүйў„и°Ӣзҡ„иЎҢдёә пјҢ ж–ҪжҡҙиҖ…жё…жҘҡең°зҹҘйҒ“иҮӘе·ұзҡ„иЎҢдёәеҸҜиғҪз»ҷеҜ№ж–№еёҰжқҘзҡ„иә«дҪ“дёҺзІҫзҘһдјӨе®і пјҢ д»ҘеҸҠйҖҡиҝҮиҝҷдёҖиЎҢдёәеҫ—еҲ°жі„ж„Өзҡ„еҝ«ж„ҹ пјҢ 并且з”ұжӯӨе»әз«Ӣиө·иҮӘиә«зҡ„з»ҹжІ»ең°дҪҚ пјҢ еҲ°еӨҙжқҘиҝҳдёҚеҝ…дёәжӯӨеҸ—еҲ°жғ©зҪҡ гҖӮеӣ жӯӨ пјҢ еңЁз”ұжҡҙеҠӣжүҖж”Ҝж’‘е’ҢеЎ‘йҖ зҡ„иҷҗеҫ…иЎҢдёәе’ҢеҝғзҗҶдҫҝжҲҗдёәдёӘдҪ“жүҖдҫқиө–д»ҘеҸҠжүҖжҺҢжҸЎзҡ„жңҖжңүж•ҲжӯҰеҷЁ пјҢ еҲ©з”Ёе…¶иҫҫеҲ°иҮӘе·ұзҡ„зӣ®зҡ„ гҖӮ иҖҢеңЁз”·жҖ§зҫӨдҪ“еҶ…йғЁ пјҢ иҝҷдёҖзңӢдјјеҸӨиҖҒе®һеҲҷжҪңжөҒдёҚжӯўзҡ„жҖ§еҲ«ж°”иҙЁе§Ӣз»ҲеӯҳеңЁ пјҢ еҚід»ҘжҡҙеҠӣдҪңдёәжқғеҠӣе’ҢжқғеЁҒзҡ„еӨ–еңЁиЎЁзҺ° пјҢ иҖҢз”ұжӯӨеЎ‘йҖ еҮәйңёжқғжҖ§з”·жҖ§ж°”иҙЁ гҖӮ иҖҢз”ұдәҺе…¶еҶ…ж¶өдёӯеӯҳеңЁзқҖејәзғҲзҡ„жҡҙеҠӣеҖҫеҗ‘е’Ңз»ҹжІ»ж¬І пјҢ дҫҝдҪҝе…¶иҪ»иҖҢжҳ“дёҫең°еҸҜд»ҘиҪ¬еҸҳдёәиҷҗеҫ…еҝғзҗҶе’ҢиЎҢдёә гҖӮ
зҫҺеӣҪз”өеҪұгҖҠз…Өж°”зҒҜдёӢгҖӢеү§з…§ гҖӮ
гҖҠдёҚиҰҒе’ҢйҷҢз”ҹдәәиҜҙиҜқгҖӢеү§з…§ гҖӮд№ҹжӯЈеӣ жӯӨ пјҢ жҲ‘们дҫҝдјҡеҸ‘зҺ°еңЁзӣёдјјзҡ„жғ…еҶөдёӢ пјҢ з”·жҖ§ж–ҪжҡҙиҖ…иҝңиҝңеӨҡдәҺеҘіжҖ§ гҖӮ еңЁ1944е№ҙзҫҺеӣҪз”өеҪұгҖҠз…Өж°”зҒҜдёӢгҖӢдёҺ2001е№ҙзҡ„еӣҪдә§еү§гҖҠдёҚиҰҒе’ҢйҷҢз”ҹдәәиҜҙиҜқгҖӢдёӯ пјҢ еүҚиҖ…зҡ„дёҲеӨ«йҮҮеҸ–еҗ„з§Қз»Ҷеҫ®зҡ„жүӢж®өжқҘиҗҘйҖ еҮәдёҖз§ҚеҸҜжҖ–зҡ„з”ҹжҙ»зҺҜеўғ пјҢ д»ҘжӯӨжҠҳзЈЁеҰ»еӯҗзҡ„иә«дҪ“е’ҢзҘһз»Ҹ пјҢ жңҖз»ҲдҪҝе…¶жҝ’дёҙеҙ©жәғиҖҢиғҪеӨҹдёәе…¶жүҖжҺ§пјӣеҗҺиҖ…зҡ„дёҲеӨ«еҲҷ家еҶ…家еӨ–дёӨеј йқўеӯ” пјҢ еӨ–йқўзҡ„вҖңеҘҪз”·дәәвҖқдёҺ家еҶ…еҜ№еҰ»еӯҗж–Ҫжҡҙзҡ„иҷҗеҫ…иҖ…еҪўиұЎе®ҢзҫҺең°иһҚдәҺдёҖдҪ“ гҖӮ3вҖңйқһдәәеҢ–вҖқ пјҢжҳҜиҷҗеҫ…дәәдёҺеҠЁзү©иғҢеҗҺе…ұеҗҢзҡ„еҝғзҗҶе°ұеҰӮзҫҺеӣҪзәӘеҪ•зүҮгҖҠйқўе…·д№ӢеҶ…гҖӢжүҖжҢҮеҮәзҡ„ пјҢ е…·жңүејәзғҲдҫөз•ҘжҖ§е’ҢжҡҙеҠӣжҖ§зҡ„йңёжқғжҖ§з”·жҖ§ж°”иҙЁе°ұеғҸдёҖеј йқўе…· пјҢ жҜҸдёӘдәәйғҪеҝ…йЎ»жҲҙдёҠ пјҢ жүҚиғҪеңЁдё»жөҒзҡ„жҖ§еҲ«еҲ¶еәҰдёӯеҚ жҚ®жңүеҲ©зҡ„з»ҹжІ»ең°дҪҚ пјҢ иҖҢиҰҒиҫҫжҲҗиҝҷдёҖзӮ№дҫҝйңҖиҰҒжҠҠйқўе…·еҶ…еҢ–зҡ„еҗҢж—¶д№ҹжёҗжёҗжҺ’ж–ҘйӮЈдәӣиў«и®ӨдёәжҳҜдҪҺдёӢе’ҢеҘіжҖ§еҢ–зҡ„жҖ§еҲ«ж°”иҙЁ гҖӮ еӣ жӯӨ пјҢ еҪ“иҝҷдәӣз”·жҖ§ејҖе§ӢиЎЁиҫҫиҮӘе·ұзҡ„и§ӮзӮ№е’Ңж¬Іжңӣж—¶ пјҢ еү©дёӢзҡ„д№ҹе°ұеҸӘжңү他们дёҖзӣҙиў«ејәеҢ–е’Ңйј“еҠұзҡ„жҡҙеҠӣжүӢж®ө пјҢ йҖҡиҝҮжңҖеҺҹе§Ӣзҡ„дёӘдҪ“зҡ„иҮӘ然еҠӣжқҘиҺ·еҫ—иҮӘиә«зҡ„ж¬ІжұӮ гҖӮ иҖҢиҝҷдёҖиЎҢдёәиҮӘе§ӢиҮіз»ҲйғҪиў«зңӢдҪңжҳҜжӯЈеёёзҡ„гҖҒжҳҜдёҖдёӘвҖңзңҹз”·дәәвҖқиҜҘжңүзҡ„ж ·еӯҗ пјҢ д»ҺиҖҢеӨұеҺ»дәҶеҸҚжҖқе’Ңж”№еҸҳзҡ„еҠӣйҮҸ гҖӮжӯЈжҳҜиҝҷдәӣеҲ¶еәҰжҖ§зҡ„з»“жһ„ пјҢ дҪҝеҫ—жҲ‘们其е®һдёҚеҝ…еҶҚеҺ»еҜ»жүҫвҖңйӯ”й¬јвҖқ пјҢ еңЁжңҖжҷ®йҒҚдё”ж—Ҙеёёд№Ӣдәәзҡ„иә«дёҠ пјҢ е°ұеҸҜд»Ҙиў«еЎ‘йҖ е’Ң规и®ӯдёәж–ҪиҷҗиҖ…иҖҢиЎҢйӯ”й¬јд№ӢдәӢ гҖӮ еңЁиҸІеҲ©жҷ®В·жҙҘе·ҙеӨҡж•ҷжҺҲжүҖеҒҡзҡ„вҖңж–ҜеқҰзҰҸзӣ‘зӢұе®һйӘҢвҖқдёӯ пјҢ дёҚжӯЈжҳҜжҸӯйңІдәҶзҺҜеўғеҜ№дёӘдҪ“жүҖиғҪдә§з”ҹзҡ„еҪұе“Қе’ҢеҪўеЎ‘иғҪеҠӣеҗ—пјҹеҚідҪҝжҳҜи°Ұи°Ұеҗӣеӯҗ пјҢ еңЁжҷ®йҒҚдё”зү№е®ҡзҡ„зҺҜеўғдёӢйғҪеҸҜиғҪиЎҢиҷҗжқҖд№ӢдәӢ гҖӮ дј з»ҹжҖ§е–„жҖ§жҒ¶зҡ„йў„и®ҫеңЁжӯӨд№ҹеӨұеҺ»ж №жҚ® пјҢ иҖҢи®©жҲ‘们еҸ‘зҺ°ж–ҪиҷҗиҖ…еҸҜиғҪжӯЈжҳҜжҜҸдёҖдёӘжҷ®йҖҡдәә гҖӮ еӣ дёәдјӨе®іејұе°ҸиҖ…дёҖж–№йқўдёҚйңҖиҰҒеӨҚжқӮзҡ„и°ӢеҲ’жҲ–иғҪеҠӣ пјҢ еҸҰдёҖж–№йқўд№ҹеӣ дёәдёҚдјҡеӣ жӯӨеҸ—еҲ°жғ©зҪҡ пјҢ дҪҝеҫ—е®ғжҲҗдёәж»Ўи¶із§Ғж¬Іе’ҢиҝӣиЎҢиҮӘжҲ‘иҶЁиғҖзҡ„жңҖз®Җжҳ“жүӢж®ө гҖӮдёҺжӯӨеҗҢж—¶ пјҢ еңЁиҷҗеҫ…еҝғзҗҶе’Ңж„ҸиҜҶдёӯ пјҢ еҜ№дәҺиў«дјӨе®іиҖ…зҡ„вҖңйқһдәәеҢ–вҖқд№ҹдҪҝеҫ—ж–ҪиҷҗиҖ…дёҚдјҡдёәжӯӨеҸ—еҲ°йҒ“еҫ·е’Ңжғ…ж„ҹвҖ”вҖ”и¶…жҲ‘пјҲеҚідҪңдёәзӨҫдјҡ规иҢғзҡ„еӨ§д»–иҖ…пјүе§Ӣз»Ҳзӣ‘и§ҶзқҖжҜҸдёӘдәәвҖ”вҖ”зҡ„еҲ¶зәҰе’Ң愧з–ҡ пјҢ жӣҙдёҚиҰҒиҜҙеҪ“他们иҷҗеҫ…зҡ„жҳҜзҢ«зӢ—иҝҷдәӣжң¬иә«е°ұйқһдәәзҡ„еҠЁзү©ж—¶ гҖ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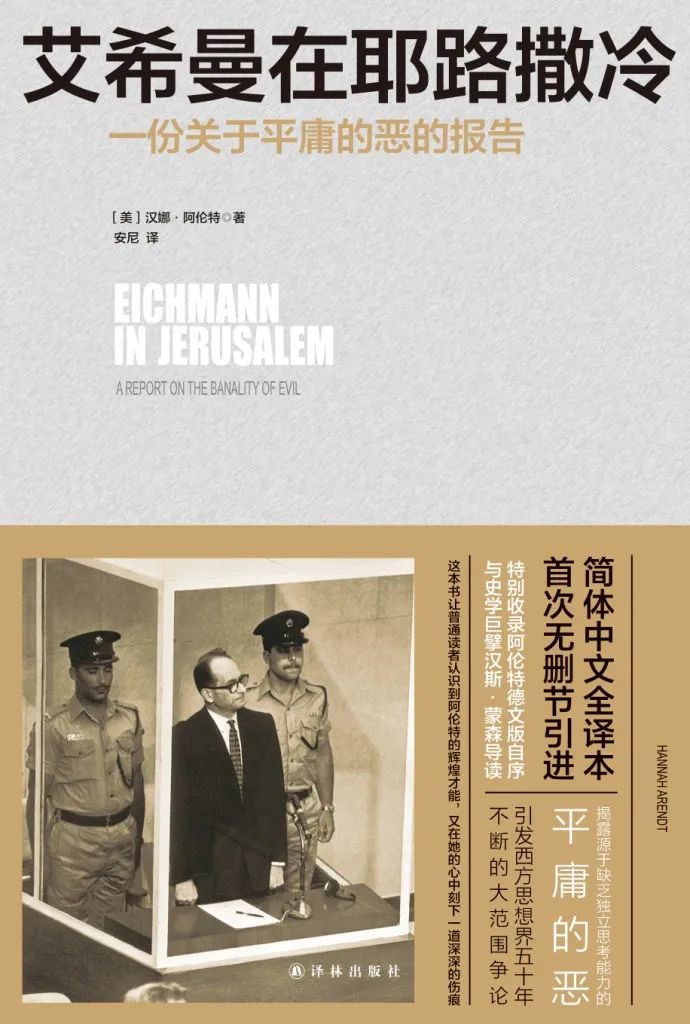
гҖҠиүҫеёҢжӣјеңЁиҖ¶и·Ҝж’’еҶ·гҖӢ пјҢ дҪңиҖ…: [зҫҺ] жұүеЁңВ·йҳҝдјҰзү№ пјҢ иҜ‘иҖ…: е®үе°ј пјҢ зүҲжң¬: иҜ‘жһ—еҮәзүҲзӨҫ 2017е№ҙ1жңҲеңЁзәізІ№жҗңйӣҶгҖҒиҝҗйҖҒгҖҒеӨ„зҗҶе’ҢжқҖе®ізҠ№еӨӘдәәж—¶ пјҢ жҲ‘们еҸ‘зҺ°д»–们жүҖдҪҝз”Ёзҡ„иҜӯиЁҖйғҪеңЁжҠҠзҠ№еӨӘдәәвҖңеҺ»дәәеҢ–вҖқ пјҢ еҚіеҲ©з”ЁиҜёеҰӮжқӮиҚүгҖҒиҙ§зү©дёҺз»ҸжөҺиЎҢдёәзӯүж–№ејҸжқҘеҜ№е…¶зү©еҢ– пјҢ жңҖз»ҲдҪҝеҫ—жқҖ害他们вҖ”вҖ”е°ұеҰӮйІҚжӣјеңЁе…¶гҖҠзҺ°д»ЈжҖ§дёҺеӨ§еұ жқҖгҖӢдёӯжүҖжҢҮеҮәзҡ„вҖ”вҖ”е°ұеҘҪдјјйҷӨеҺ»иҠұеӣӯдёӯзҡ„жқӮиҚүиҲ¬ пјҢ дёҚдјҡеј•иө·жҲ–йҖ жҲҗд»»дҪ•зҡ„еҝғзҗҶгҖҒйҒ“еҫ·дёҺжғ…ж„ҹдёҠзҡ„дёҚйҖӮ гҖӮ еҸ‘з”ҹеңЁеҗ„дёӘйӣҶдёӯиҗҘдёӯзҡ„зҫһиҫұгҖҒдјӨе®іе’Ңиҷҗеҫ…д№ҹдҫҝеӨ§йқўз§Ҝең°еҮәзҺ° гҖӮ иҖҢеҪ“йӮЈдәӣзәізІ№еңЁжҲҳеҗҺеӣһзӯ”жЈҖеҜҹе®ҳиҙЁй—®дёәд»Җд№Ҳж—¶ пјҢ 他们其е®һе·Із»ҸеҜ№иҝҷдёӘй—®йўҳжң¬иә«еӨұеҺ»дәҶзҗҶи§ЈиғҪеҠӣ гҖӮ йҳҝдјҰзү№еңЁе…¶гҖҠиүҫеёҢжӣјеңЁиҖ¶и·Ҝж’’еҶ·гҖӢдёӯдҫҝжҢҮеҮә пјҢ еҪ“дј з»ҹзҡ„еҫӢд»ӨвҖңжұқдёҚеҸҜжқҖдәәвҖқеҸҳжҲҗвҖңжұқеҝ…йЎ»жқҖдәәвҖқж—¶ пјҢ еүҚиҖ…дҫҝжҲҗдәҶйқһжӯЈеёёзҠ¶жҖҒ гҖӮ
зәӘеҪ•зүҮгҖҠе…іеЎ”йӮЈж‘©д№Ӣи·ҜгҖӢеү§з…§ гҖӮе°ұеҰӮеңЁ2004е№ҙзҫҺеӣҪзҲҶеҮәзҡ„йҳҝеёғж јиҺұеёғзӣ‘зӢұзҡ„иҷҗеӣҡдәӢ件дёӯ пјҢ жңұиҝӘж–ҜВ·е·ҙзү№еӢ’дҫҝд»ҘвҖңи„ҶејұдёҚе Әзҡ„з”ҹе‘ҪвҖқжҢҮеҮәеҪ“йӮЈдәӣиў«е…іжҠјдәҺжӯӨзҡ„еӣҡзҠҜеңЁеӨұеҺ»дәҶвҖңдәәвҖқзҡ„иө„ж јеҗҺ пјҢ еҜ№е…¶зҡ„зҫһиҫұе’Ңиҷҗеҫ…жң¬иҜҘдә§з”ҹзҡ„йҒ“еҫ·дёҺжғ…ж„ҹдёҠзҡ„еҲ¶зәҰдҫҝдјҡж¶ҲеӨұ гҖӮ д№ҹжӯЈжҳҜеңЁиҝҷйҮҢ пјҢ е·ҙзү№еӢ’и®©жҲ‘们注ж„ҸвҖңи°ҒжҳҜвҖҳдәәвҖҷвҖқдё”иғҪеҫ—еҲ°жүҝи®ӨиҝҷдёӘй—®йўҳиғҢеҗҺжүҖйҡҗи—Ҹзҡ„йңёжқғе’ҢжҡҙеҠӣ гҖӮ еңЁвҖңжҲ‘们вҖқдёҺвҖң他们вҖқзҡ„еҢәеҲҶдёӯеҫҖеҫҖеӯҳеңЁзқҖйҡҗз§ҳзҡ„вҖңйқһдәәеҢ–вҖқеҖҫеҗ‘ пјҢ иҖҢдҪҝеҫ—еҜ№еҗҺиҖ…зҡ„дјӨе®іеҸҳеҫ—еҗҚжӯЈиЁҖйЎәдё”еҸҜиў«жҺҘеҸ— пјҢ д№ҹжӣҙдёҚеҝ…еҶҚжҸҗеҗҢжғ…жҲ–жҳҜеҜ№д»–дәәз—ӣиӢҰж„ҹзҹҘзҡ„иғҪеҠӣ пјҢ иҖҢз”ұжӯӨж’•ејҖеңЁжҷ®йҒҚдәәжҖ§е’Ңдәәжқғд№ӢдёӢзҡ„еұҖйҷҗдёҺйҳҙжҡ—д№ӢеӨ„ пјҢ д»ҘеҸҠжҲ‘们жғ…ж„ҹиғҪеҠӣжүҖеҸ—еҲ¶зҡ„жЎҶжһ¶дёҺжЁЎејҸзҡ„е°Ғй—ӯ гҖӮиҷҗеҫ…е’ҢиҷҗжқҖеҠЁзү© пјҢ еӣ дёәе®ғ们йқһдәә пјҢ жүҖд»ҘеңЁжҹҗз§ҚзЁӢеәҰдёҠеҸҜд»Ҙиў«е®Ҫе®ҘпјҹдҪҶе…¶е®һе®ғдёҺиҷҗеҫ…е’ҢиҷҗжқҖдәәд№Ӣй—ҙжңүзқҖзҙ§еҜҶзҡ„ж„ҸиҜҶеҪўжҖҒиҒ”зі» пјҢ еҚівҖңйқһдәәеҢ–вҖқ гҖӮ иҖҢд№ҹдёҚжӯЈжҳҜеӣ дёәи§үеҫ—дјӨе®івҖңйқһдәәвҖқзҡ„вҖ”вҖ”еҰӮеҠЁзү©зӯүвҖ”вҖ”жҳҜеҸҜиў«жҺҘеҸ—зҡ„ пјҢ иҖҢеҮәзҺ°дәҶиӮҶж— еҝҢжғ®зҡ„жҡҙеҠӣе’ҢиҷҗжқҖеҗ—пјҹеҚідҪҝеңЁдәІеҜҶе…ізі»дёӯ пјҢ е…ұжғ…иғҪеҠӣзҡ„еҢ®д№Ҹд»ҘеҸҠеҜ№еҜ№ж–№зҡ„вҖңйқһдәәеҢ–вҖқиҙ¬дҪҺиҖҢдҪҝе…¶ж„ӨжҖ’гҖҒдёҚж»ЎгҖҒз§Ғж¬Іе’ҢжҡҙеҠӣеҸҳеҫ—дёәжүҖж¬Ідёә пјҢ иҖҢеҪ“еӨ–з•ҢеҜ№жӯӨжҲ–жҳҜеҶ·зңјж—Ғи§ӮгҖҒжҲ–иӯҰеҜҹд»ҘвҖңжё…е®ҳйҡҫж–ӯ家еҠЎдәӢвҖқиҖҢжҗӘеЎһжёҺиҒҢ пјҢ д»ҘеҸҠдё»жөҒжҖ§еҲ«еҲ¶еәҰдёӯжңүе®ізҡ„з”·жҖ§ж°”иҙЁиў«йј“еҠұе’ҢејҘж•Јж—¶ пјҢ дҫҝдјҡеҜјиҮҙиҝҷдәӣиҷҗеҫ…еҝғзҗҶе’ҢиЎҢдёәдёҚд»…ж— жі•еҫ—еҲ°зҰҒжӯўе’Ңж”№жӯЈ пјҢ иҝҳеҸҜиғҪеҸҳжң¬еҠ еҺү пјҢ жңҖз»ҲйҖ жҲҗеҜ№еҸ—е®іиҖ…зҡ„жӣҙеӨ§дјӨе®і гҖӮеңЁиҜ„и®әиҷҗжқҖеҠЁзү©ж—¶ пјҢ дәә们常常ејәи°ғж–ҪиҷҗиҖ…зҡ„йҒ“еҫ·зҙ иҙЁдҪҺдёӢ пјҢ жғ…ж„ҹвҖ”вҖ”е°Өе…¶жҳҜе…ұжғ…е’ҢзҗҶи§Јд»–дәәд»–зү©з—ӣиӢҰиғҪеҠӣвҖ”вҖ”зҡ„еҢ®д№Ҹ пјҢ дҪҶж— и®әжҳҜйҒ“еҫ·иҝҳжҳҜжғ…ж„ҹ пјҢ йғҪ并йқһе…ҲеӨ©д№Ӣзү© пјҢ иҖҢжҳҜиҜһз”ҹдәҺдёӘдҪ“жҲҗй•ҝзҡ„家еәӯгҖҒзӨҫдјҡе’ҢеӣҪ家д№Ӣдёӯ гҖӮ ж–Ҫиҷҗе’ҢжҡҙеҠӣжҲ–и®ёжҳҜдёӘдҪ“зҡ„иЎҢдёә пјҢ дҪҶжҲ‘们еҚҙдёҚеҫ—дёҚиҝҪзҙўеҜјиҮҙиҝҷдәӣдёӘдҪ“иЎҢдёәиҜһз”ҹзҡ„жӣҙдёәеӨҡе…ғдё”еӨҚжқӮзҡ„еҺҹеӣ гҖӮ еӣ дёәиҷҗеҫ…вҖ”вҖ”ж— и®әжҳҜеҜ№еҠЁзү©иҝҳжҳҜдәәвҖ”вҖ”дёӯжҪңи—ҸзқҖжӣҙдёәзӨҫдјҡжҖ§зҡ„зі»з»ҹй—®йўҳ пјҢ д»ҺдёӘдҪ“зҡ„жҲҗй•ҝдёҺж•ҷиӮІеҲ°е®¶еәӯгҖҒдёӨжҖ§е…ізі»дёҺжҖ§еҲ«еҲ¶еәҰ пјҢ дҪңдёәзҫӨдҪ“зҡ„зӨҫдјҡдәәйҷ…е’Ңз”ҹжҙ» пјҢ д»ҘеҸҠеӣҪ家зҡ„ж”ҝжІ»ж–ҮеҢ–е’ҢеӣҪйҷ…дәӨеҫҖдёӯзҡ„з§Қз§Қж‘©ж“ҰдёҺеҶІзӘҒ 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жҒҗжҖ–ж…Һе…ҘпјҢе°јж—ҘеҲ©дәҡеҠЁзү©еӣӯйӣ„зӢ®йҘҝиҮійӘ·й«…д»ҚеңЁеұ•и§Ҳ
- жү¶ж‘ҮиһҚеӘ’|еұұиҘҝеҲқдёӯеҘіз”ҹиў«еҗҢеӯҰиҷҗеҫ…пјҢжү“иҖіе…үжөҮејҖж°ҙиҮҙйҮҚдјӨпјҢж–ҪжҡҙиҖ…д»…иў«жү№иҜ„ж•ҷиӮІ
- еҠЁзү©д»ҺиЎҖиӮүд№ӢиәҜиҪ¬еҗ‘дёҚжӯ»д№ӢиәҜ,жҳҜдәәз”Ёдҝ®иҫһе®ҢжҲҗзҡ„
- ж’ӯжҠҘеӨҡзңӢзӮ№|йҹ©еӣҪеҘіеӯҗиҺ·вҖңеӨ©дҪҝеҰҲеҰҲвҖқд№Ӣз§°пјҢиҠӮзӣ®ж’ӯеҮә12еӨ©еҗҺпјҢеҚҙе°Ҷе…»еҘіиҷҗеҫ…иҮҙжӯ»
- 12еј е№ҙеәҰжҸҗеҗҚйҮҺз”ҹеҠЁзү©ж‘„еҪұпјҢеёҰдҪ йўҶз•ҘеЈ®йҳ”зҡ„еӨ§иҮӘ然
- з”Ёеҝғеҫ…дәә
- жЈҖеҜҹжңәе…і|жү“еҮ»з ҙеқҸйҮҺз”ҹеҠЁзү©иө„жәҗзҠҜзҪӘ еүҚдёүеӯЈеәҰе…ұиө·иҜүдёҖдёҮдә”еҚғдҪҷдәә
- 2020жҗһ笑йҮҺз”ҹеҠЁзү©ж‘„еҪұеҘ–
- 68еІҒиҖҒдәәжңҲиҠұ8дёҮж•‘еҠ©1300еҸӘжөҒжөӘеҠЁзү©
- еЁұд№җеҪ“家|е°ҸеӯҰз”ҹдҪңж–ҮгҖҠе°Ҹе°ҸеҠЁзү©еӣӯгҖӢ, жҠҠжҸЎиҝҷ4дёӘеҶҷдҪңж–№жі•, еӯҰдјҡжҸҸеҶҷдәәзү©














![[зұіеәҰ科жҠҖе®һйӘҢе®Ө]ProжёІжҹ“еӣҫдә®зӣё/жҜ”е°”зӣ–иҢЁи°ҙиҙЈзҫҺеӣҪж”ҝеәңпјҢзӣҳзӮ№пјҡiPhone12](https://imgcdn.toutiaoyule.com/20200429/20200429190353237395a_t.jp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