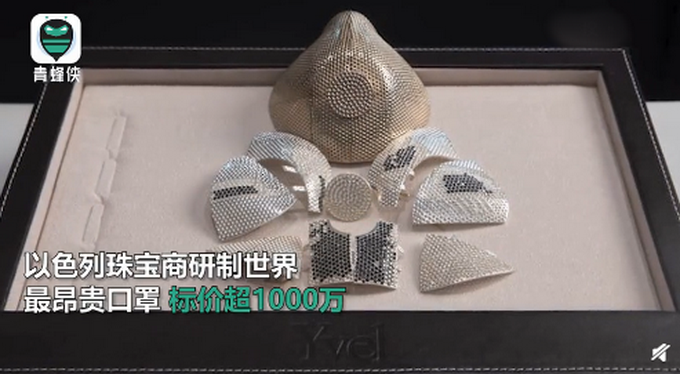ж”№еҸҳдёҖйғЁе…ідәҺгҖҢйҮҺе‘ігҖҚзҡ„жі•еҫӢпјҢжңүеӨҡйҡҫ( дәҢ )
в—Ҹ 2020е№ҙиҮӘ然д№ӢеҸӢиҒ”еҗҲе…¶д»–еӨҡ家зҺҜдҝқжңәжһ„е…ұеҗҢжҸҗдәӨз»ҷе…ЁеӣҪдәәеӨ§зҡ„дҝ®жі•е»әи®® / еҸ—и®ҝиҖ…жҸҗдҫӣвҖңеҚҒдёғе№ҙеүҚеҜ№е…¬е…ұеҚ«з”ҹе®үе…ЁйҖ жҲҗзҡ„з ҙеқҸзҡ„еҸҚжҖқжІЎиғҪеңЁз«Ӣжі•еұӮйқўеӣәе®ҡдёӢжқҘ пјҢ жІЎиғҪжҲҗдёәзӨҫдјҡе®үе…Ёзәҝ пјҢ иҝҷжҳҜеҫҲеҸҜжғңзҡ„ гҖӮ вҖқеј дјҜй©№иҜҙ пјҢ вҖңеҲ°дәҶд»Ҡе№ҙ пјҢ зӨҫдјҡе…¬дј—е’ҢеҶізӯ–иҖ…зҡ„ж„ҸиҜҶйғҪеңЁиҝӣжӯҘ пјҢ иҖҢжҲ‘们зҡ„зӨҫдјҡи’ҷеҸ—дәҶжӣҙеӨ§зҡ„жҚҹеӨұ пјҢ иҝҷжҲ–и®ёиғҪеӨҹжҲҗдёәдёҖж¬Ўжӣҙе…ій”®зҡ„еҘ‘жңә гҖӮ вҖқвҖңеҰӮжһңжҲ‘еҗғдәҶдёҖдёӘзҺ»з’ғзҗғ пјҢ еҜјиҮҙиӮҡеӯҗз–ј пјҢ жҳҜеә”иҜҘиҜҙдёҚиҰҒеҗғдёҚиҜҘеҗғзҡ„дёңиҘҝ пјҢ иҝҳжҳҜдёҚиҰҒеҗғзҺ»з’ғзҗғпјҹвҖқжҖ»з»“иҝҮеҺ»еҮ е№ҙе®һи·өдёӯзҡ„з»ҸйӘҢж•ҷи®ӯ пјҢ еј дјҜй©№з”ЁдәҶдёҖдёӘжҜ”е–» пјҢ вҖңжі•еҫӢе°ұжҳҜиҰҒжҠҠжҷ®йҒҚжҖ§е’ҢйҖҡз”ЁжҖ§жӢүеҮәжқҘ пјҢ иҰҒеңЁеҲ¶еәҰеұӮйқўжңү规еҲ¶ гҖӮ вҖқиҖҢжңӘзҹҘз—…жҜ’еёҰз»ҷжҲ‘们зҡ„жңҖеӨ§ж•ҷи®ӯ пјҢ жҲ–и®ёе°ұжҳҜдёҚиҰҒиҝҮеәҰдҫқиө–еҫҖж—Ҙзҡ„з»ҸйӘҢеҺ»иҜ„дј°жңӘзҹҘдәӢзү©зҡ„еҚұйҷ©жҖ§ пјҢ жӯЈи§Ҷдәәзұ»иғҪеҠӣд»Қ然жңүйҷҗзҡ„зҺ°е®һ гҖӮ вҖңйқһдәәзұ»й©ҜеҢ–зҡ„еҠЁзү©жңүеӨӘеӨҡжңӘзҹҘе’ҢйЈҺйҷ© пјҢ иҰҒжҠҠиҝҷдәӣжңүж•ҲжҺ§еҲ¶дҪҸжүҚиЎҢ гҖӮ вҖқеј дјҜй©№иҜҙ гҖӮйҮҺдҝқжі•еңЁдҝқжҠӨи°Ғ2020е№ҙ пјҢ жҲ‘们еңЁе…ЁзҗғжҖ§зҒҫйҡҫжқҘдёҙд№Ӣйҷ…и®ӨиҜҶеҲ°дәҶиҮӘе·ұзҡ„жёәе°Ҹ пјҢ жң¬ж¬ЎеҮ д№ҺжүҖжңүжҸҗдәӨз»ҷе…ЁеӣҪдәәеӨ§зҡ„дҝ®жі•е»әи®®ж–№жЎҲйғҪжҸҗеҸҠ пјҢ иҰҒе°ҶвҖңз”ҹжҖҒе®үе…ЁвҖқвҖңе…¬дј—еҒҘеә·вҖқеҠ е…ҘйҮҺдҝқжі•зҡ„з«Ӣжі•зӣ®ж Ү гҖӮдҪҶдёҺжӯӨеҗҢж—¶ пјҢ з»қеӨ§еӨҡж•°дҝ®жі•е»әи®®йғҪд»Қе°ҶвҖңж”№еҶҷвҖҳеҲ©з”ЁвҖҷжі• пјҢ е»әз«ӢвҖҳдҝқжҠӨвҖҷжі•вҖқзҪ®дәҺдҝ®и®ўе·ҘдҪңзҡ„йҰ–иҰҒдҪҚзҪ® гҖӮиҝҷжҳҜ2016е№ҙдёҠдёҖж¬ЎеӨ§и§„жЁЎдҝ®жі•йҒ—з•ҷдёӢжқҘзҡ„жңӘз«ҹд№Ӣдёҡ гҖӮ йӮЈдёҖж¬Ў пјҢ жҠ•е…ҘеҲ°дҝ®жі•е·ҘдҪңдёӯзҡ„规模е’Ңйҳөе®№еҸҜи°“з©әеүҚ пјҢ дҪҶжңҖз»Ҳзҡ„з»“жһңеҚҙ并дёҚеҰӮдәәж„Ҹпјҡ2016е№ҙзүҲгҖҠйҮҺз”ҹеҠЁзү©дҝқжҠӨжі•гҖӢе°Ҫз®Ўд№ҹеңЁејҖзҜҮеҶҷе…ҘдәҶвҖңз»ҙжҠӨз”ҹзү©еӨҡж ·жҖ§е’Ңз”ҹжҖҒе№іиЎЎ пјҢ жҺЁиҝӣз”ҹжҖҒж–ҮжҳҺе»әи®ҫвҖқ пјҢ еҚҙд»ҚжҠҠйҮҺз”ҹеҠЁзү©и§ҶдёәдёҖз§ҚвҖңиө„жәҗвҖқ пјҢ е°ұе…¶иҗҪең°еҠҹиғҪиҖҢиЁҖ пјҢ дҫқ然жҳҜдёҖйғЁвҖңеҲ©з”ЁвҖқжі• гҖӮвҖң2016е№ҙжҲ‘们жңҹжңӣеҫҲй«ҳ пјҢ вҖқй—®еҸҠжӯӨдәӢ пјҢ еј дјҜй©№жүҝи®Ө пјҢ вҖңдҪҶжңҖз»ҲжІЎиғҪжҲҗеҠҹ пјҢ дҝ®жі•иҝҮзЁӢеңЁдёҚж–ӯеҗҺйҖҖ пјҢ е’Ңз«Ӣжі•жңәжһ„иғҪеӨҹе®һзҺ°еҜ№иҜқзҡ„е…¬зӣҠз»„з»Үе’ҢеҠЁдҝқз»„з»Үд»Қ然еҫҲе°‘ пјҢ еӨӘе°‘дәҶ гҖӮ вҖқ
в—Ҹ 2020е№ҙ4жңҲ2ж—Ҙжё…жҷЁ пјҢ еңЁеҢ—дә¬жҲҝеұұеҢәеӨ§зҹіжІіж»Ёж°ҙе…¬еӣӯ пјҢ й»‘иұ№йҮҺз”ҹеҠЁзү©дҝқжҠӨз«ҷзҡ„е·ҘдҪңдәәе‘ҳеңЁз”ЁеҠЁзү©еЈ°йҹіжҗңзҙўеҷЁеҜ»жүҫйқ’еӨҙжҪңйёӯзҡ„дҪҚзҪ® / IC photoеңЁжҺЁеҠЁдҝ®и®ўзҡ„иҝҷдёҖдҫ§ пјҢ еҜ№дәҺдҝ®жі•ж–№еҗ‘е·Іжңүеҹәжң¬е…ұиҜҶпјҡ第дёҖдёӘд»»еҠЎ пјҢ жҳҜиҰҒе°ҶвҖңжңү规е®ҡзҡ„зү©з§ҚдҝқжҠӨ пјҢ жІЎжңү规е®ҡзҡ„зү©з§Қе°ұеҸҜд»Ҙд»»ж„ҸеҲ©з”ЁвҖқзҡ„ж—§жҖқи·ҜжҺЁзҝ» пјҢ еҸҳжҲҗвҖңжңү规е®ҡзҡ„зү©з§ҚжңүйҷҗеәҰеҲ©з”Ё пјҢ жІЎжңү规е®ҡзҡ„зү©з§ҚдёҖдҪ“дҝқжҠӨвҖқпјӣ第дәҢдёӘд»»еҠЎ пјҢ еҲҷжҳҜе°ҶдҝқжҠӨзҡ„еҶ…е®№дёҚд»…жү©еӨ§еҲ°е…ЁйғЁйқһ规е®ҡйҮҺз”ҹеҠЁзү©дёӘдҪ“дёҠ пјҢ иҝҳиҰҒе°ҶйҮҺз”ҹеҠЁзү©ж –жҒҜең°д№ҹзәіе…ҘиҝӣжқҘ гҖӮиҝҷдәӣеҠӘеҠӣзҡ„ж №жң¬зӣ®ж ҮеңЁдәҺз»ҙжҠӨз”ҹзү©еӨҡж ·жҖ§вҖ”вҖ”йңҖиҰҒдҝқжҠӨзҡ„дёҚеҸӘжҳҜжҹҗдёҖдёӘзҸҚзЁҖзү©з§Қ пјҢ д№ҹдёҚеҸӘжҳҜжҹҗдёҖдәӣвҖңеӨ–иЎЁеҸҜзҲұзҡ„вҖқйҮҺз”ҹеҠЁзү© пјҢ иҖҢжҳҜиҰҒдҝқдҪҸеӨҡе№ҙж— йҷҗеәҰејҖеҸ‘д»ҘеҗҺ пјҢ еңЁи®ёеӨҡең°ж–№е·Із»Ҹж‘Үж‘Үж¬Іеқ зҡ„з”ҹжҖҒзі»з»ҹ пјҢ жҳҜиҰҒж”№еҸҳд»ҘзЁҖжңүзЁӢеәҰе’ҢеҲ©з”Ёд»·еҖјжқҘиЎЎйҮҸйҮҺз”ҹеҠЁзү©д»·еҖјзҡ„жҖқи·Ҝ пјҢ д»Ҙз»ҙжҠӨз”ҹзү©еӨҡж ·жҖ§дёәзӣ®зҡ„ пјҢ жүҝи®Өеҗ„з§ҚйҮҺз”ҹеҠЁзү©еңЁз”ҹжҖҒзі»з»ҹдёӯеә”жңүзҡ„дҪҚзҪ® гҖӮдҪҶеҜ№дәҺе…¬дј—жқҘиҜҙ пјҢ вҖңдҝқжҠӨз”ҹзү©еӨҡж ·жҖ§вҖқдёҖзұ»е®ҸеӨ§зӣ®ж Үжҳҫеҫ—еӨӘиҝҮиҷҡж— зјҘзјҲ пјҢ 2016е№ҙзҡ„дҝ®жі•е·ҘдҪңжңҖз»ҲеҮ д№ҺйҖҖеӣһиө·зӮ№ пјҢ зҺҜдҝқеңҲеӨ–зҡ„еӨ§йғЁеҲҶжҷ®йҖҡдәәз”ҡиҮіжІЎжңүз•ҷж„ҸеҲ°иҝҷдёӘж¶ҲжҒҜ гҖӮиҖҢз ҙеқҸиҝҳеңЁз»§з»ӯ гҖӮ йӮЈдәӣд»Өдәәз—ӣеҝғзҡ„ж–°й—» пјҢ еҰӮд»Ҡе·Із»ҸеҸёз©әи§ҒжғҜеҲ°дәә们дёҚеҶҚеҺ»ж„ӨжҖ’е’ҢиҙЁз–‘пјҡжҜ’жқҖеҮ еҚғеҸӘеҖҷйёҹеҸӘдёәзүҹеҲ© пјҢ иө°з§ҒеҚҒдҪҷеҗЁйҮҺз”ҹеҠЁзү©жҜӣзҡ®иў«жө·е…іжҹҘиҺ· пјҢ еӨұеҺ»дәҶеӨ©ж•ҢеҗҺеҶңдҪңзү©з—…иҷ«е®ізҲҶеҸ‘ пјҢ дёәдәҶзҒӯиҷ«еҸҲж–Ҫз”ЁдәҶи¶…йҮҸеҶңиҚҜвҖҰвҖҰ2017е№ҙ пјҢ дә‘еҚ—зәўжІіе№ІжөҒжҲӣжҙ’жұҹдёҖдёӘж°ҙз”өз«ҷйЎ№зӣ®дёҠ马ејҖе·Ҙ пјҢ жһҒеҚұзү©з§Қз»ҝеӯ”йӣҖгҖҒеӣҪ家дёҖзә§дҝқжҠӨжӨҚзү©вҖңйҷҲж°ҸиӢҸй“ҒвҖқзҡ„жңҖеӨ§дёҖеқ—е®Ңж•ҙж –жҒҜең°гҖҒдёҖеӨ„е·Із»ҸжһҒдёәзҪ•жңүзҡ„еұҖйғЁз”ҹжҖҒзі»з»ҹ пјҢ е°Ҷиў«ж·№жІЎ гҖӮ
в—Ҹ жҲӣжҙ’жұҹз•”зҡ„з»ҝеӯ”йӣҖ / вҖңиҮӘ然д№ӢеҸӢвҖқеҫ®еҚҡиҖҢеңЁе…¬дј—еҜҹи§үдёҚеҲ°зҡ„ең°ж–№ пјҢ иҮӘ然жңүе®ғеҸҚеҮ»зҡ„йҖ»иҫ‘ гҖӮ2020е№ҙејҖе№ҙ пјҢ йҡҸзқҖз–«жғ…жҠҠжүҖжңүдәәжүЈз•ҷеңЁеҺҹең° пјҢ и®ёеӨҡдәәжүҚ第дёҖж¬Ўеҫ—зҹҘжҲ‘еӣҪеҶңдҪңзү©е·ІеҮ д№ҺеҸӘиғҪдҫқйқ дәәе·Ҙе…»ж®–зҡ„иңңиңӮжҺҲзІү пјҢ еҰӮжһңиҠұжңҹеҶ…е…»иңӮдәәдёҚиғҪеҸҠж—¶иө¶еҲ° пјҢ дҪңзү©е°ұйқўдёҙеӨ§е№…еҮҸдә§з”ҡиҮіз»қ收вҖ”вҖ”з”ұдәҺж»Ҙз”ЁеҶңиҚҜжқҖиҷ«еүӮе’ҢйҮҺеӨ–ж –жҒҜең°зҡ„жҢҒз»ӯз ҙеқҸ пјҢ йҮҺиңӮз§ҚзҫӨе·Із»ҸеӨӘе°‘еӨӘе°‘ гҖӮеҸҰдёҖз§ҚжҳҶиҷ«еҗҢж ·жҲҗдёәзӨҫдәӨзҪ‘з»ңзҡ„зғӯи®®зӣ®ж Үпјҡи°ҒиғҪжғіеҲ°иҝҮеҺ»дёӨе№ҙжқҘдёӯдёңе’ҢйқһжҙІзҡ„еҮ еңәејӮеёёеӨ§йӣЁ пјҢ дјҡеңЁдёӨе№ҙеҗҺй…ҝжҲҗиӮҶиҷҗдёӨдёӘеӨ§жҙІзҡ„иқ—зҒҫпјҹйҮҺз”ҹеҠЁзү©йҒӯеҲ°зҢҺжқҖгҖҒж –жҒҜең°дёҚж–ӯиў«дҫөеҚ зҡ„еҸҰдёҖйқў пјҢ еҲҷжҳҜеҺҹжң¬еӯҳеңЁдәҺиҮӘ然з•Ңзҡ„еӨҡз§Қз—…еҺҹдҪ“ејҖе§ӢеңЁдәәзұ»иҒҡеұ…ең°дёӯиҺ·еҫ—еүҚжүҖжңӘжңүзҡ„жү©ж•Јжңәдјҡ гҖӮдәәзұ»жҡҙйңІдәҺз–«з—…зҡ„йЈҺйҷ©дёҚж–ӯеҚҮй«ҳ пјҢ иҖҢиҝҪиёӘе…¶жқҘжәҗеҚҙ并йқһеҰӮеҫҲеӨҡдәәжғіиұЎдёӯйӮЈж ·иҪ»иҖҢжҳ“дёҫпјҡеңЁдё–з•ҢеҚ«з”ҹз»„з»ҮпјҲWHOпјүзҡ„е®ҳж–№зҪ‘з«ҷдёҠ пјҢ еҢ…жӢ¬еҹғеҚҡжӢүз—…жҜ’гҖҒй©¬е°”е Ўз—…жҜ’е’ҢеҜЁеҚЎз—…жҜ’еңЁеҶ…зҡ„еҗ„з§Қе·Із»ҸеӨҡж¬ЎжӢүе“ҚиҝҮе…ЁзҗғиӯҰжҠҘзҡ„зҹҘеҗҚз—…жҜ’ пјҢ иҝ„д»Ҡд»Қ然жҳҜвҖңиҮӘ然е®ҝдё»дёҚжҳҺ пјҢ еҸҜиғҪеҢ…жӢ¬вҖҰвҖҰвҖқ
жҺЁиҚҗйҳ…иҜ»
- е…ідәҺе…»иҖҒдҝқйҷ©иҙ№зјҙзәідёӯзҡ„еҮ дёӘй—®йўҳ
- еҘҘе·ҙ马关дәҺжҳҺе°јиӢҸиҫҫжҡҙд№ұеЈ°жҳҺ
- еј е…Ҳз”ҹ|иў«йҒ—еҝҳ28е№ҙжҲҝеӯҗдҪҸжҲ·жӯЈеңЁжҗ¬е®¶пјҒе…ідәҺ收жҲҝж—¶й—ҙпјҢеҸҢж–№еҶҚж¬ЎеҜ№иҜқ
- е·қжҷ®е…ідәҺе…ЁеӣҪжҡҙд№ұзҡ„еЈ°жҳҺ
- ж‘ҶдёӘе°Ҹж‘ҠиғҪе…»жҙ»иҮӘе·ұеҗ—пјҹ
- е…ідәҺдёӯиҚҜпјҢеҢ—дә¬еҚ«еҒҘ委
- зҫҺеӣҪеҚ•ж–№ж”№еҸҳеҜ№йҰҷжёҜж”ҝзӯ–е°ҶиҮӘйЈҹиӢҰжһң
- жҲ‘们еҮ д»Јдәәзҡ„еҠӘеҠӣд»Җд№ҲйғҪжІЎж”№еҸҳпјҢеӯ©еӯҗдҪ иҰҒгҖӮгҖӮ
- ж–№иҲҹеӯҗдёҺзҪ‘еҸӢиҝӣиЎҢе…ідәҺдёӯеҢ»иҚҜзҡ„зІҫеҪ©еҜ№иҜқ
- е…ідәҺзҫҺеӣҪвҖңе®һдҪ“жё…еҚ•вҖқ жҲ‘们еҝ…йЎ»зҹҘйҒ“зҡ„дёҖеҲҮпј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