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之道( 二 )
梁启超晚年因病住院 , 依然忍不住要写信给远在国外的孩子们:“你们这些孩子真是养得娇 , 三个礼拜不接到我的信就噘嘴了 , 想外面留学生两三个月不接家信不算奇怪 。 我进医院有三个礼拜了 , 再不写信 , 你们又不知道怎么抱怨了……”他的孩子们愿意亲近父亲 , 是因为梁启超首先对他们给予了关注和爱 。 与一部分中国传统的、内敛的“严父”形象相反 , 梁启超思想现代 , 情感热烈 , 擅长表达且毫不含蓄 。 虽然分隔各地 , 直接而频繁的情感交流使聚少离多的一家人紧密地凝聚在了一起 。
一切皆以修身为本作为中国近代百科全书的学者 , 梁启超在教育子女时对知识性学问的重视是十分自然的 , 他让思顺留在日本求学 , 不但专门为其请了几位家庭教师 , 学习内容遍涉西方社会学科的主要门类——其目的并非进行学术研究 , 而是立足于知其大意和了解大势 。
他也注重发挥孩子们“传帮带”的作用 , 比如在1912年11月9日、10日写给思顺的信中 , 就特别交代了思顺要监督思成的学业 , 如有进步 , 则奖励仿宋本《四书》一部 。 梁启超常常寻购旧书、字画 , 一方面自己读赏 , 一方面作为给孩子们的礼物和奖励 , 这也是一种文化和审美的引导 。
如果仅做到了重视知识性学问 , 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也只不过是“学校教育的延伸”而已 , 从书中收录的写给子女的信件、教育文章中能够读出的是:他实际上是在借助所有叙述表达的机会 , 向孩子们传递自己的人生态度、理念 , 夯实教育的基础“修身” , 处处渗透着儒家文化的气息 。 张文江教授表示 , 在近代的人物中间 , 梁启超会通“儒释道”三教而归宗于儒 , 其做人做事有其鲜明的特色 , 其实就是《易经》所说的自强不息——这也是梁氏家庭教育的根本 。
比如 , 他对子女说:“我自己常常感觉要拿自己做青年人的人格模范 , 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兄弟的模范 。 我又相信我的孩子们 , 个个都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 , 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 。 ”对人格、道德修养的重视使他认为这些乃是“做人的基础” , 只有“先打定了” , 才能接下来谈做学问 。 梁启超一生践行了自己的修身之道 , 做到了如是说、如是行 , 修身即生活即教育 。
在梁启超生命的最后四五年 , 1925至1929年初 , 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 , 但笔耕不辍、不时演讲之外 , 仍主持清华研究院 , 出任北京图书馆、京师图书馆馆长 , 创办司法储才馆等 。 在此阶段 , 他将传统的修身之学与自己的经验结合 , 对孩子们总结出了“得做且做”主义:“你们别要以为我心境不好 , 我现在讲学正讲得起劲哩……我总是抱着‘有一天做一天’的主义(不是‘得过且过’ , 却是‘得做且做’) , 所以一样的活泼、愉快 。 ”
梁启超把学术研究也当做修身的途径之一 , 强调学术的“薰染陶镕”之功 , 虽然希望子女学有所成 , 但极力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 。 他曾经再三告诫思顺不要因为赶进度学习而过于劳累 , 星期天必须休息 , 多游戏、多运动 。 对待在国外留学的梁思成 , 梁启超也一度担心他“渐渐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 , 于是致信对他说希望思成能像从前一样“活泼有春气” , 他就心满意足了 。 梁启超的家庭教育 , 可谓一面重视知识性学问 , 同时又对其可能带来的生命的损耗时刻保持警惕 。 若引用古来先哲的话 , 做学问最重优游涵泳 , 使自得之——这是梁启超对子女在学术研究功夫上的具体指点 。
与如今不少父母极力为子女提供优裕的生活环境不同 , 梁启超最为重视培养子女的忧患意识 , 时刻教导孩子们要在忧患和挫折中成长 , 以此磨炼意志 , 砥砺人格 。 1916年 , 梁启超与蔡锷策划反对袁世凯的“护国运动”时 , 内心非常清楚有可能失败 , 从而使家庭陷入困顿 。 但他也认为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 对思顺说:“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 , 此乃最足以自豪者 , 安能逐腥膻而丧吾所守耶?”他还表示 , 即使运动成功了自己也不再做官 , 以免子女易成为纨绔子弟 , 丧失了个人志向与自立能力 。 在这样的言传身教和精神指引之下 , 梁家的孩子们都刻苦求知 , 极为节俭 , 最后倒要梁启超劝说他们“不必太苦 , 反变成寒酸” 。
推荐阅读
- 提醒|徐志摩婚礼结束后,梁启超写下一封信提醒林徽因别忘记这件事
- 婚姻|梁启超为何将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姻视为自己的得意之作!
- 梁启超|晚清造假第一人: PS和皇帝的合影照, 伪造圣旨, 拿到国外骗吃骗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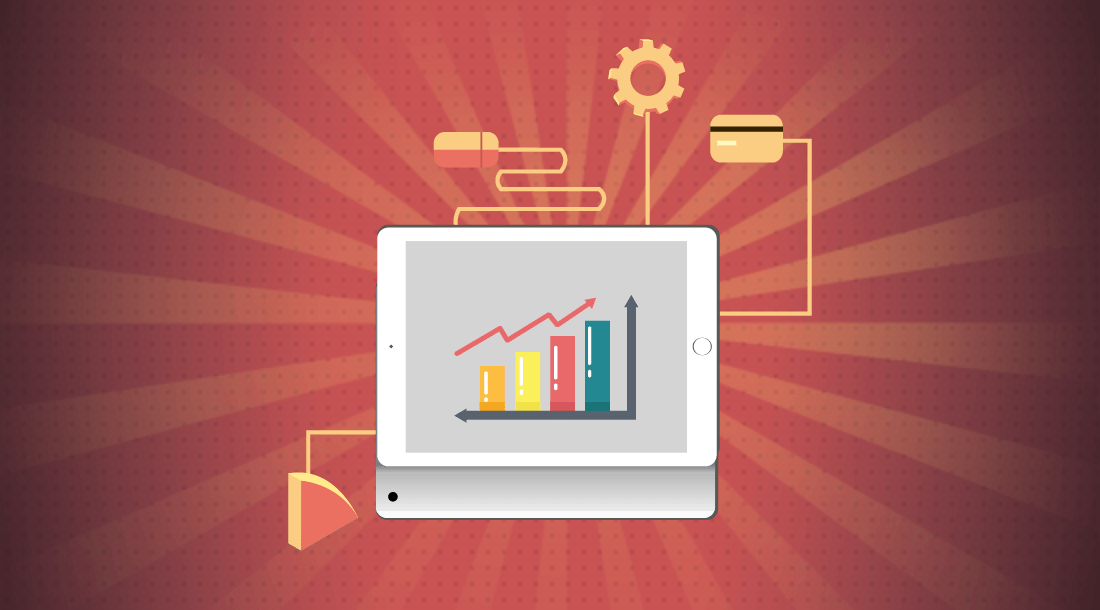









![[聊聊圈里事]外观极具未来感,加速5秒以内,续航超600KM,特斯拉迎来最强对手](https://imgcdn.toutiaoyule.com/20200403/20200403162020957175a_t.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