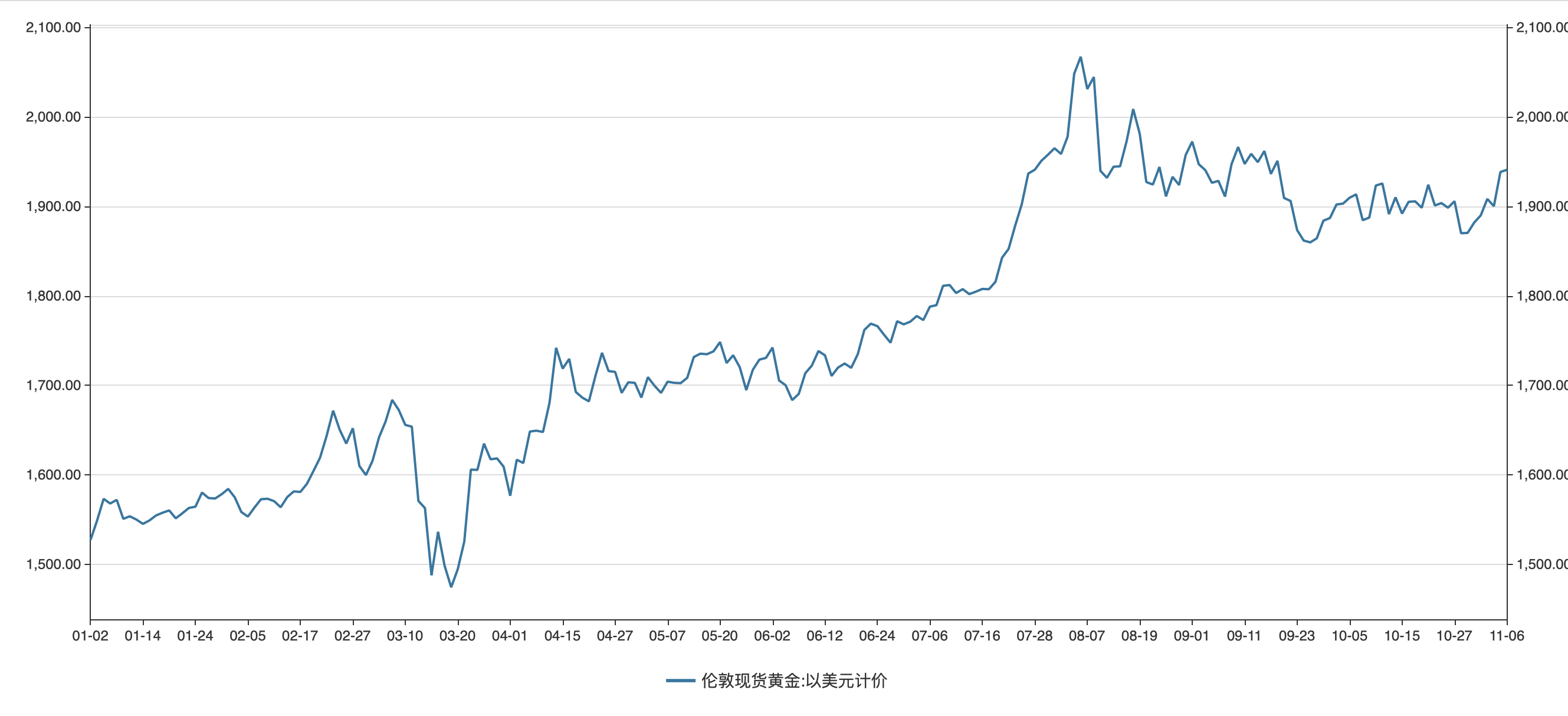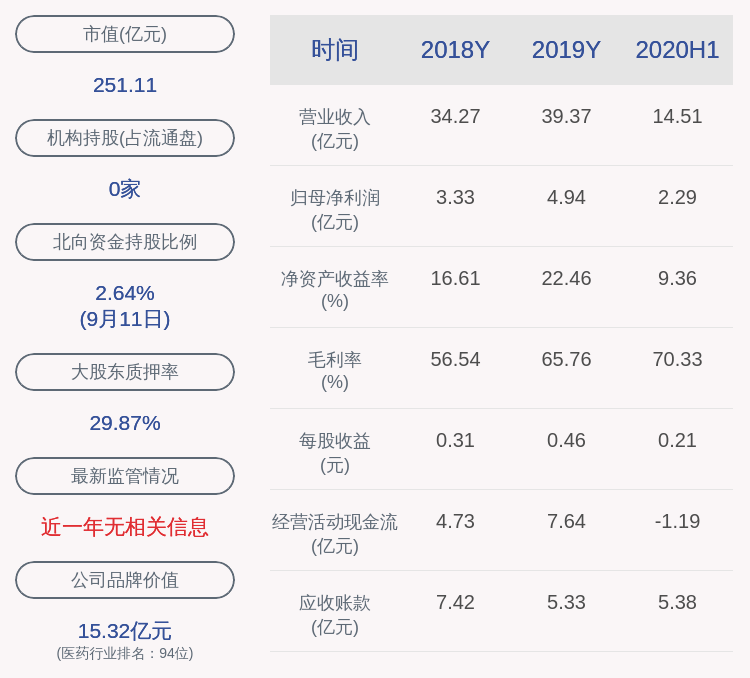е§ңж–ҮиҝҳиҜҙпјҡвҖңиҜҙжҳҺз®ұзҠ¶еұҸйЈҺејҸжЈәеәҠз»„еҗҲеҗҺпјҢз«ӢдәҺеҸ°еә§дёҠпјҢдё”й“әдёҠзҹіжқҝпјҢжүҝж”ҫзҒөжһўгҖӮвҖқеүҚйқўиҜҙиҝҮпјҢвҖңжЈәеәҠвҖқз§°и°“дёҚзЎ®пјҢз§°е‘јвҖңеӣҙеұҸзҹіжҰ»вҖқиҫғжҺҘиҝ‘еҺҶеҸІзңҹе®һгҖӮд»Һе®үдјҪеў“еҸ‘жҺҳзңӢпјҢдәҰдёҚе…·вҖңжүҝж”ҫзҒөжһўвҖқзҡ„дҪңз”ЁгҖӮеңЁеҢ—жңқж—¶жңҹпјҢдёҚз”ЁзҹіжҰ»жүҝж”ҫзҒөжһўпјҢд№ғжҳҜе…ід№Һе…ҘеҚҺзІҹзү№иў„ж•ҷеҫ’дҝқз•ҷжң¬еңҹ葬дҝ—д№Ӣдј з»ҹпјҢж•…дёҚеҸҜдёҚиҫЁгҖӮ
еұҸйЈҺеӣҫеғҸиӢҘе№Ій—®йўҳ
е®үдјҪеў“зҹіжҰ»з¬¬1е№…еұҸйЈҺпјҢдёәиҝӣдәәеӨ©еӣҪзҡ„еӣҫеғҸпјҢдёҠйқўз»ҳзҠҠиҪҰдёҖиҫҶпјҢеҸҰжңүеӨҙжҲҙжҜЎеёҪпјҢиә«зқҖеңҶйўҶй•ҝиўҚпјҢжқҹи…°еёҰзҡ„йӘ‘马дәәпјҢе…¶еҗҺи·ҹйҡҸж“ҺеҚҺзӣ–зҡ„дҫҚд»ҺдәҢдәәпјҢдёӢйқўз»ҳдёҖжӢұжЎҘгҖӮжЎҘеҸідёәеӨҙжҲҙе°ҸеёҪпјҢзі»еёҰзқҖйқҙпјҢиә«зқҖеңҶйўҶиўҚжңҚзҡ„еў“дё»дәәз”»еғҸпјҢе…¶еҗҺжңүдәҢдҫҚд»ҺпјӣжЎҘе·ҰжңүдёҖд»ҷеҘіпјҢжҗәдёҖз«ҘеӯҗпјҢиә«еҗҺдәҰжңүдәҢеҘідҫҚгҖӮжҠҠиҝҷе№…еӣҫеғҸз®ҖеҚ•зңӢжҲҗжҳҜеӨ«еҰ»жёёд№җжҳҜдёҚеҰҘзҡ„пјҢе®ғеҸҜиғҪдёҺзҘҶж•ҷж•ҷд№үдёӯзҡ„жҹҗдәӣи®°еҸҷжңүе…ігҖӮ
еј е№ҝиҫҫгҖҒе§ңдјҜеӢӨдәҢдҪҚе…Ҳз”ҹеқҮжӣҫжҢҮеҮәпјҡзҘҶж•ҷеҫ’дәЎзҒөзҰ»ејҖдёӢз•Ңзҡ„ж—…зЁӢпјҢ第дёҖжӯҘжҳҜйҒҮи§ҒдәҶиҮӘе·ұзҡ„иүҜзҹҘпјҢеҚівҖңдҝЎд»°вҖқзҡ„еҢ–иә«гҖӮеӣ жӯӨпјҢ第1е№…зҡ„дёҠеҚҠйғЁеә”жҳҜеў“дё»дәәд№ҳиҪҰйӘ‘马еҗ‘еӨ©еӣҪиҝӣеҸ‘д№Ӣе§ӢйҖ”зҡ„еӣҫеғҸгҖӮеј е№ҝиҫҫе…Ҳз”ҹжҚ®гҖҠйҳҝз»ҙж–ҜеЎ”гҖӢз»Ҹ19з« 30иҠӮз»Ҹж–ҮиҜҙпјҡвҖңеҪ“е–„еЈ«пјҲnar ashavanпјүзҡ„зҒөйӯӮдәҺжӯ»еҗҺ第дёүж—Ҙжё…жҷЁжқҘеҲ°вҖҳзӯӣйҖүд№ӢжЎҘвҖҷд№ӢеүҚпјҢе§җеҺ„еЁңд»Ҙз«ҘеҘіеҪўиұЎеҮәйқўиҝҺжҺҘпјҢиә«иҫ№жңүдёӨзҠ¬зӣёдјҙгҖӮвҖқе®үдјҪ墓第 1е№…еұҸйЈҺдёҠиҷҪж— дәҢзҠ¬дҪҶеҚҙжңүдәҢдҫҚеҘіпјҢиҝҷеӨ§зәҰжҳҜдёӯеӣҪеҢ–зҡ„иЎЁзҺ°гҖӮдҪҶеў“дё»дәәд№Ӣе·ҰпјҢзЎ®жңүдёҖдҪҚдҪідёҪе°‘еҘіпјҢеҚіе§җеҺ„еЁңпјҢйқўеүҚдәҰжңүжӢұжЎҘдёҖеә§пјҢжҲ–еҚіз»Ҹж–ҮдёӯжүҖжҢҮзҡ„вҖңзӯӣйҖүд№ӢжЎҘвҖқгҖӮеңЁиҝҷйҮҢдәЎзҒөжҺҘеҸ—е§җеҺ„еЁңпјҢиҝҷдҪҚиў«жҠҪиұЎеҢ–дёәеҙҮжӢңжңҖй«ҳзҘһйҳҝиғЎжӢү·马兹иҫҫзү№е®ҡдҝЎд»°еҢ–иә«зҡ„жЈҖйӘҢе’ҢеҲӨеҶівҖңжӯЈдҝЎд№Ӣеҫ’з”ұеҘід»ҷеј•и·ҜпјҢз»ҸиҝҮе–„жҖқгҖҒе–„иЁҖе’Ңе–„иЎҢдёүйҒ“е…іеҸЈпјҢеҚіеҸҜеҚҮдәәж— йҷҗе…үжҳҺзҡ„еӨ©еӣҪгҖӮвҖқиҝҷзұ»еҘізҘһжҺҘеј•еӣҫпјҢеңЁиҷһејҳзҹіжӨҒ第2е№…еӣҫеғҸдёӯдәҰжӣҫи§ҒеҲ°гҖӮдҪҶиҷһејҳеў“д№ӢеҘізҘһжңүеӨҙе…үпјҢиҖҢе®үдјҪеў“еҚҙдёҚд»ҘеӨҙе…үжңүеҗҰеҢәеҲҶзҘһдәәд№Ӣиә«д»ҪпјҢеә”жҳҜжӣҙдёӯеӣҪеҢ–дәҶзҡ„иЎЁзҺ°гҖӮ
е§җеҺ„еЁңзҡ„жҺҘеј•пјҢдёәзҡ„жҳҜи®©дәЎзҒөиҝӣдәәеӨ©еӣҪгҖӮеңЁз¬¬7е№…еӣҙеұҸпјҲи§Ғжң¬жңҹз®ҖжҠҘеҗҺеұҸ第3е№…пјүдёӯпјҢдёҠйғЁз»ҳжңүжӯҮеұұйЎ¶е®«ж®ҝдёҖеә§пјҢж®ҝеҶ…зҪ®зҹіжҰ»дёҖй“әпјҢе§җеҺ„еЁңеқҗдәҺзҹіжҰ»жӯЈдёӯеҒҸе·Ұзҡ„дҪҚзҪ®дёҠпјҢзҹіжҰ»еҒҸеҸіеҲҷдёәеў“дё»пјҢе§җеҺ„еЁңеҸіжүӢжҢҒжқҘйҖҡпјҲи§’еҪўжқҜпјүпјҢеў“дё»е·ҰжүӢжҸЎй«ҳи¶іжқҜпјҢеҸҢж–№дҪңдәӨи°ҲзҠ¶пјҢиҜҙжҳҺеў“дё»з»ҸеҸ—дәҶиҖғйӘҢе·ІиҝӣдәәеӨ©еӣҪгҖӮдёҺеүҚе№…з”»зӣёиҒ”зі»зҡ„жҳҜвҖңзӯӣйҖүд№ӢжЎҘвҖқе·ІеңЁеӨ©еӣҪе®«ж®ҝд№ӢеүҚпјҢдәҢдҫҚеҘіз«ӢдәҺеҰІйЎҫеЁңд№ӢеҗҺпјҢеў“дё»д№ӢдҫҚд»ҺжҠұй…’еЈ¶з«ӢдәҺдё»дәәд№ӢеҗҺгҖӮеӨ©еӣҪеҶ…ж®ҝе®ҮйҮҚйҮҚпјҢйҒҚең°йІңиҠұзҒөиҚүпјҢдёҖжҙҫжһҒд№җдё–з•Ңж°”иұЎгҖӮзұ»дјјзҡ„з”»йқўеңЁйҡӢиҷһејҳеў“зҹіжӨҒзҡ„第3е№…д№ҹжӣҫеҸ‘зҺ°гҖӮд»ҘеӨ«еҰҮеҜ№еқҗйҘ®е®ҙи§ЈйҮҠжҒҗйқһжҳҜпјҢеӣ дёәиҜҘе№…з”»дёӯдҪідёҪжңүе…үеӨҙпјҢз”·дё»дәәж— еӨҙе…үпјҢжҳҫ然具жңүзҘһдҝ—дёҚеҗҢиә«д»ҪгҖӮеҢ—е‘Ёе®үдјҪеў“дёӯпјҢеқҮдёҚеҲ»з”»еӨҙе…үпјҢжӯӨд№ғдёҺеҢ—йҪҗгҖҒйҡӢд»ЈеңЁеұұиҘҝгҖҒжІіеҚ—зӯүең°еҮәеңҹзҡ„зІҹзү№зҘҶж•ҷйӣ•еҲ»з”»д№ӢйҮҚеӨ§еҢәеҲ«гҖӮдҪҶд№ҹжңүеҢ—йҪҗж—¶жңҹе§җеҺ„еЁңжІЎжңүеӨҙе…үзҡ„еӣҫеғҸпјҢеҰӮж—Ҙжң¬ж»ӢиҙәеҺҝејҘејҳеҚҡзү©йҰҶжүҖи—Ҹзҡ„еҢ—йҪҗеҠ еҪ©зҹійӣ•й•¶жқҝпјҢеҰІеҺ„еЁңдёҺеў“дё»дәәпјҢеқҗдәҺеӨ©зӣ–帷幕дёӢзҡ„жҰ»еәҠдёҠпјҢеҜ№йқўйҘ®й…’пјҢе…¶жғ…иҠӮдёҺе®үдјҪзӯүеў“з”»ж— ејӮпјҢеҰІеҺ„еЁңе·ҰжүӢжү§жқҘйҖҡпјҢеў“дё»е·ҰжүӢжүҳй«ҳи¶ій…’жқҜпјҢжҰ»д№ӢдёӢеҲҷдёәиҲһи№ҲеңәйқўгҖӮиҝҷзұ»еј•иҝӣеӨ©еӣҪпјҢиҝӣдәәеӨ©еӣҪзҡ„еӣҫеғҸпјҢеңЁеҢ—йҪҗгҖҒеҢ—е‘Ёзҡ„еӣҙеұҸзҹіжҰ»дёӯеҸҚеӨҚеҮәзҺ°жүҖйҖҸйңІеҮәзҡ„дҝЎжҒҜпјҢе°ұжҳҜиҝҷз§Қеўғз•ҢдёәдәәеҚҺзІҹзү№зҘҶж•ҷеҫ’еҜ№дәЎзҒөзҡ„жңҖй«ҳзҘҲжұӮпјҢд№ҹжҳҜ他们иҷ”иҜҡдҝЎд»°зҡ„йӣҶдёӯеҸҚжҳ пјҢе’ҢдҪӣж•ҷеҫ’жӯ»еҗҺиҝӣе…ҘиҘҝж–№жһҒд№җдё–з•Ңзҡ„ж„ҝжңӣе…·жңүеҗҢзӯүеҗ«д№үгҖӮ
еңЁе®үдјҪ墓第6е№…еұҸйЈҺз”»дёӯпјҢдёҠеҚҠйғЁдёҖзІҹзү№дәәдёҺдёҖиў«й•ҝеҸ‘дәәйӘ‘马зӣёйҒҮпјҢдә’дёҫжүӢиҮӮпјҢдәІеҲҮиҮҙзӨјпјҢдёӢеҚҠйғЁеҲҷжҳҜеңЁжңүж—ҘжңҲж Үеҝ—зҡ„еёҗзҜ·дёӢпјҢжҢүеҸ‘дәәд»Ҙи·Әе§ҝдёҺзӣҳиҶқзҡ„зІҹзү№дәәеқҗдәҺзҹіжҰ»е·ҰеҸіпјҢдәҢдәәд№Ӣй—ҙзҪ®й©¬жүҺдёҖеүҜгҖӮжҰ»дёӢж‘Ҷи®ҫеҗ„з§Қй…’е…·гҖҒзӣҳеҷЁпјҢдәҢдәәд№ӢеҗҺеқҮжңүдёҖдҫҚд»ҺпјҢдёӯй—ҙз«ҷз«ӢдёҖжү§й…’瓶зҡ„еҰҮеҘігҖӮй•ҝеҸ‘д№ӢдәәпјҢеӯҰз•ҢдёҖиҲ¬и®ӨдёәжҳҜзӘҒеҺҘдәәпјҢиҖҢиҝҷзұ»жҠҖй•ҝеҸ‘зҡ„зӘҒеҺҘдёҺзІҹзү№дәәдәӨеҘҪзҡ„еңәйқўпјҢеңЁе®үдјҪеў“зҡ„第3гҖҒ4гҖҒ6гҖҒ9е№…зҡ„еұҸйЈҺз”»дёӯйғҪжңүеҮәзҺ°пјҢ第6е№…дёӢеӣҫзҡ„帷幕дёҠзјҖж—ҘжңҲи„ҠйҘ°пјҢжё…жҘҡиЎЁжҳҺдәҶзІҹзү№дёҺзӘҒеҺҘдәәжңүзқҖе…ұеҗҢдҝЎд»°гҖӮеңЁеҸӨзӘҒеҺҘдәәзҡ„еҺҹе§ӢдҝЎд»°дёӯпјҢдәӢзҒ«е’ҢжӢңеӨ©жёҠжәҗжөҒй•ҝгҖӮе”җиҙһи§ӮеҲқе№ҙзҺ„зұ»йҖ”з»ҸдёӯдәҡзўҺеҸ¶еҹҺеҸ—еҲ°зӘҒеҺҘеҸҜжұ—йҡҶйҮҚжҺҘеҫ…гҖӮжҚ®гҖҠеӨ§ж…ҲжҒ©еҜәдёүи—Ҹжі•еёҲдј гҖӢдә‘пјҡвҖңзӘҒеҺҘдәӢзҒ«пјҢдёҚж–ҪпјҲжңЁпјүеәҠпјҢд»ҘжңЁеҗ«зҒ«пјҢ故敬иҖҢдёҚеұ…пјҢдҪҶең°ж•·йҮҚиҢөиҖҢе·ІгҖӮвҖқиҝҷиҜҙжҳҺдәӢзҒ«гҖҒжӢңеӨ©еңЁзӘҒеҺҘжұ—еәӯзҡ„дҝЎд»°дёӯеҚ жңүжҳҫи‘—ең°дҪҚгҖӮж®өжҲҗејҸгҖҠй…үйҳіжқӮдҝҺгҖӢеҚ·еӣӣжӣҫи®°иҪҪзӘҒеҺҘеҜ№зҘҶзҘһзҡ„еҙҮжӢңпјҡвҖңзӘҒеҺҘдәӢзҘҶзҘһпјҢж— зҘ еәҷпјҢеҲ»жҜЎдёәеҪўпјҢзӣӣдәҺзҡ®иўӢпјҢиЎҢеҠЁд№ӢеӨ„пјҢд»Ҙи„ӮиӢҸж¶Ӯд№ӢпјҢжҲ–зі»д№Ӣз«ҝдёҠпјҢеӣӣж—¶зҘҖд№ӢвҖқгҖӮдёҚз®Ўе…¶еҙҮжӢңж–№ејҸжҳҜеҗҰдёҺзІҹе°ҶзӣёеҗҢпјҢзӘҒеҺҘдәәеҙҮжӢңзҘҶзҘһжҳҜдёҺзІҹзү№дәәдёҖиҮҙзҡ„гҖӮжүҖд»ҘпјҢеңЁиў„ж•ҷеҫ’зҡ„зҹіеҲ»иүәжңҜдёӯпјҢеҮәзҺ°дј—еӨҡзҡ„зӘҒеҺҘдәәжӯЈжҳҜеҹәдәҺиҝҷдёӘеҺҹеӣ гҖӮиҝҷз§ҚзІҹзү№дёҺзӘҒеҺҘдәәе…ұеҗҢзҘӯзҘҖгҖҒжӯҢиҲһгҖҒзӢ©зҢҺгҖҒйҘ®е®ҙзҡ„еӣҫеғҸпјҢеңЁж—Ҙжң¬ж»ӢиҙәеҺҝејҘејҳеҚҡзү©йҰҶ收и—Ҹзҡ„зҹіеұҸдёҠд№ҹйў‘йў‘еҮәзҺ°гҖӮеҰӮдәҰжңүеңЁеёҗзҜ·дёӢпјҢзІҹзү№дәәе®ҙиҜ·жҠҖеҸ‘зӘҒеҺҘдәәеҸҠиҚүеҺҹеҗ„ж—Ҹдәәзү©зҡ„еӣҫеғҸпјӣд№ҹжңүеҸҚжҳ зӘҒеҺҘдәәй•ҝдәҺйһҚ马пјҢж°‘жҖ§ејәжӮҚзҡ„еӣҫеғҸпјӣд»ҘеҸҠзӘҒеҺҘдәәеұ…еёҗзҜ·гҖҒж”ҫзү§йӘҸ马еҸҠзӢ©зҢҺзҡ„еӣҫеғҸпјҲеӣҫдёҖеӣӣпјүгҖӮеңЁзІҹзү№дәәзҡ„зҹіжҰ»еұҸйЈҺз”»дёӯпјҢдҪ•д»Ҙжңүиҝҷд№ҲеӨҡзҡ„зӘҒеҺҘдәәеҪўиұЎеҮәзҺ°пјҢйҷӨдәҶжңүе…ұеҗҢдҝЎд»°еӨ–пјҢиҝҳдёҺзІҹзү№дәәеңЁдёқи·ҜдёҠзҡ„зү№ж®ҠдҪңз”Ёжңүе…і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йҮ‘з»һиңң|жҖҺд№Ҳз…®иңңиңЎпјҹ
- зҲ¶еӯҗ|з»ҸзҲ¶еӯҗдёүдәәи°Ӣз®—пјҢеҰӮдҪ•е»әз«ӢеҢ—йҪҗпјҢеҸҲжҖҺж ·йҒӯйҒҮеҢ—е‘ЁиҰҶзҒӯ
- жІіеҢ—ж ҫеҹҺе‘Ё|жІіеҢ—周家еә„еў“ең°дёҺж®·еўҹеҸ‘зҺ°еұһеҗҢдёҖж–ҮеҢ– еЎ«иЎҘеҶҖдёӯеҚ—ең°еҢәеҺҶеҸІз©әзҷҪ
- еҢ—ж–№|е…ідәҺеҢ—йӯҸеӨӘжӯҰеёқвҖңзҒӯдҪӣвҖқдёҺеҢ—е‘ЁжӯҰеёқвҖңзҒӯдҪӣвҖқпјҢдәҢиҖ…жңүе•Ҙзӣёдјјд№ӢеӨ„
- йҡӢе”җ|жқЁеқҡе»әз«ӢйҡӢжңқд№ӢеҗҺпјҢеҢ—е‘Ёе®Јеёқзҡ„дә”дҪҚзҡҮеҗҺе‘ҪиҝҗеҰӮдҪ•пјҹ
- зҡҮеёқ|еҸІдёҠжңҖзүӣзҡ„еІізҲ¶пјҢиҮӘе·ұжҳҜеҢ—е‘ЁжҹұеӣҪпјҢдёүдёӘеҘіе©ҝйғҪжҳҜзҡҮеё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