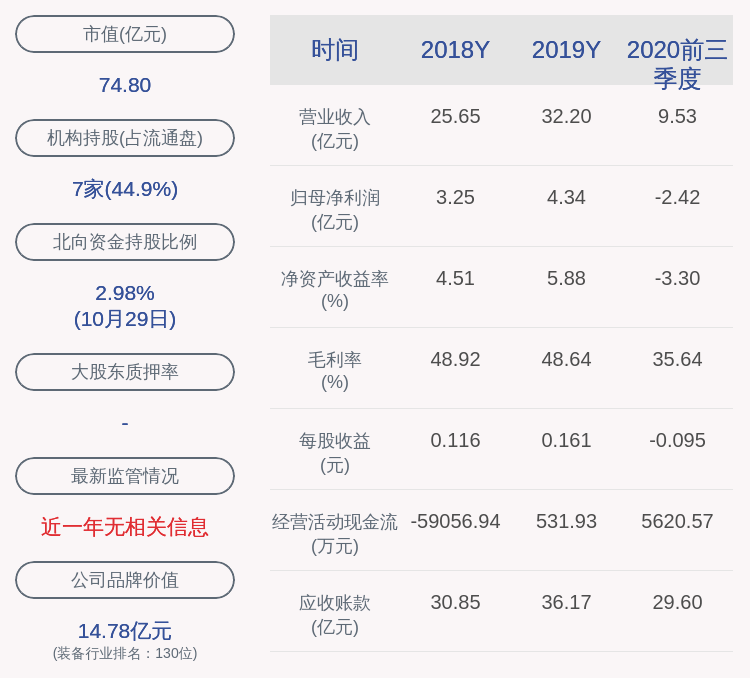йҖғеҮәзҹҝеұұпјҡиҜ—дәәйҷҲе№ҙе–ңзҡ„зҲҶиЈӮдёҺеҜӮйқҷ( еӣӣ )
зҹҝеұұз”ҹжҙ»еӯӨеҜӮ пјҢ дҝЎеҸ·еёёеёёдёҚйҖҡ пјҢ жү“дёҚеҮәз”өиҜқ гҖӮ е·ҘеҸӢд№Ӣй—ҙ пјҢ жҜҸдёӘдәәйғҪжңүиҮӘе·ұзҡ„йӮЈдёҖжң¬иҙҰ пјҢ жІЎд»Җд№ҲеҸҜдәӨеҝғзҡ„ең°ж–№ гҖӮ 他们д№ҹзҹҘйҒ“йҷҲе№ҙе–ңжңүдәӣдёҚдёҖж ·вҖ”вҖ”еӨ§е®¶жү“зүҢзҡ„ж—¶еҖҷ пјҢ д»–е–ңж¬ўиҜ»д№Ұ гҖӮ
жҜҸдёӘзҲҶз ҙе·ҘеәҠеӨҙжңүдёҖйғЁз”өиҜқжңә пјҢ е’Ңзҹҝжҙһзӣёиҝһ пјҢ й“ғеЈ°дјҡеңЁд»»дҪ•ж—¶еҖҷжҜ«ж— еҫҒе…Ҷең°е“Қиө·жқҘ гҖӮ йҖҡеёёжҳҜзҲҶз ҙдёҚжҲҗеҠҹ пјҢ еҸ¬дәәеӣһеҺ»еӨ„зҗҶж®ӢзӮ® гҖӮ зҹҝдёҠжңүеҸҘеҸЈеҸ·пјҡвҖңеӨ©дёҚжҖ• пјҢ ең°дёҚжҖ• пјҢ жңҖжҖ•еҚҠеӨңжү“з”өиҜқ гҖӮ вҖқ
еҚҠеӨңз”өиҜқдёҖе“Қ пјҢ йҷҲе№ҙе–ңжҜ”е–»вҖңе°ұеғҸдёҖжқЎиӣҮдёҖж · пјҢ дёҖеҜёдёҖеҜёең°иө·жқҘвҖқ гҖӮ еҫҲеӨҡж—¶еҖҷжүҚдёӢе·ҘдёҚд№… пјҢ жҙ—еҘҪзҡ„иЎЈжңҚйғҪжІЎе№І пјҢ еҶ¬ж—ҘйҮҢжҷҫзқҖз»“жҲҗдәҶеҶ° пјҢ еҫ—з”ЁжЈҚеӯҗж•Іжү“ж•Іжү“з©ҝдёҠиә« пјҢ еҘ—дёҠйӣЁйқҙгҖҒзҹҝеёҪе’ҢжүӢеҘ— пјҢ й—ӯзқҖзңјеҫҖзҹҝжҙһжҢӘиҝҮеҺ» гҖӮ
йҷҲе№ҙе–ңи§үеҫ—иҝҷдәӣйғҪжҳҜдҪңдёәдёҲеӨ«е’ҢзҲ¶дәІзҡ„д»–зҗҶеә”жүҝеҸ—зҡ„ гҖӮ вҖңеҜ№и°ҒиҜҙпјҹжІЎдәәеҸҜиҜҙ гҖӮ вҖқ
жҜҸжҜҸд»ҺзІ—зІқзҡ„е·ҘдҪңдёӯжқҫжҮҲдёӢжқҘ пјҢ йҷҲе№ҙе–ңеҸҳеҫ—и„Ҷејұ пјҢ вҖңе°ұеғҸж·№жІЎеңЁжұӘжҙӢеӨ§жө·д№ӢдёӯвҖқ гҖӮ еңЁиҢ«иҢ«жҲҲеЈҒдёӯ пјҢ дёҖзңјжңӣдёҚеҲ°еӨҙ пјҢ д»–и§үеҫ—иҮӘе·ұе’ҢдёҖеҸӘиҷ«еӯҗжІЎжңүд»»дҪ•еҢәеҲ« пјҢ вҖңйҡҸж—¶йғҪжңүеҸҜиғҪиў«еӨӘйҳіи’ёеҸ‘жҺү пјҢ йӮЈж—¶еҖҷдҪ зңҹжӯЈж„ҹи§үдҪ жҳҜеӨҡд№Ҳзҡ„жёәе°ҸвҖқ гҖӮ
дҪҶеҶҷе®ҢдёҖйҰ–иҜ— пјҢ еҝғйҮҢе°ұиҲ’дёҖеҸЈж°”вҖ”вҖ”
дёҖжқЎйҡ§йҒ“жү“йҖҡз”ҹжӯ»
жҲ‘жҳҜдёҖйҒ“дҪ д»¬ж –еұ…зҡ„з§ҰеІӯ
3
йҖғзҰ»зҹҝеұұ
еңЁж–°з–Ҷзҡ„е–Җе–ҮжҳҶд»‘еұұејҖзҹҝ пјҢ жІЎжңүе·ҘжЈҡ пјҢ еәҹејғзҡ„зҹҝжҙһзӣ–дёҖеқ—еёҳеӯҗ пјҢ е°ұз®—е®ҝиҲҚдәҶ гҖӮ иҝҷеӨ©жҷҡдёҠ пјҢ йҷҲе№ҙе–ңе’ҢеӣӣдёӘе·ҘеҸӢзү№ж„ҸзқЎеңЁзҰ»жҙһеҸЈжңҖиҝ‘зҡ„еәҠдҪҚ пјҢ еӨ©й»‘йҖҸд№ӢеҗҺ пјҢ 他们жӮ„ж‘ёиө·иә« пјҢ иҝһеӨңйҖғдёӢеұұ гҖӮ и·ҜдёҠиҮӘ然没жңүзҒҜ пјҢ 他们зӯ–еҲ’еӨҡж—¶ пјҢ йҖүеңЁдёҖдёӘжңҲиүІеӨҹдә®зҡ„еӨңжҷҡеҗҜзЁӢ гҖӮ
еңЁж–°з–Ҷзҡ„е…«д№қдёӘжңҲйҮҢ пјҢ 他们дёҚзҹҘеӯЈиҠӮе’Ңж—¶ж—Ҙ пјҢ еҸӘиғҪйқ еҜ№йқўеұұе°–дёҠзҡ„йӣӘзәҝй«ҳдҪҺжқҘеҲҶиҫЁж°”еҖҷзҡ„еҸҳеҢ– гҖӮ еұұдёҠжІЎжңүжҠҘзәёгҖҒз”өи§Ҷ пјҢ еҒ¶е°”жңүдәәдёӢеұұ пјҢ еёҰеӣһдәәй—ҙзҡ„ж¶ҲжҒҜ гҖӮ
з”ҹжҙ»зү©иө„з”ұдёҖжқЎзҙўйҒ“еҗҠдёҠеұұ пјҢ е“ӘжҖ•дёҖж”ҜзүҷиҶҸ пјҢ д№ҹеҫ—й©ұиҪҰеӣӣзҷҫе…¬йҮҢеҲ°иҺҺиҪҰеҺҝеҹҺеҺ»д№° гҖӮ зӯүеҲ°д№°еҘҪеҗҠдёҠжқҘ пјҢ иұҶи…җй—»зқҖеҸ‘й…ё пјҢ йқ’иҸңе·Із»Ҹи”«дәҶ гҖӮ
иҝһз»ӯеҮ дёӘжңҲжІЎжңүжӢҝдёҖзӮ№е·Ҙиө„ гҖӮ жңүз»ҸйӘҢзҡ„зҹҝе·Ҙж №жҚ®жү“дёӢжқҘзҡ„зҹіжң« пјҢ е°ұиғҪж–ӯе®ҡиҝҷзҹҝйҮҢжІЎдёңиҘҝ гҖӮ
иҖҒжқҝжҠ•иө„дәҶдёӨдёӘдәҝ пјҢ зҹҘйҒ“иө”дәҶ пјҢ дҪҶзҹҝдёҚиғҪеҒң гҖӮ еҸӘжңү继з»ӯејҖйҮҮ пјҢ жүҚиғҪжүҫеҲ°вҖңжӣҝжӯ»й¬јвҖқвҖ”вҖ”дәҸй’ұеҗҺжүҫдәәжҺҘжүӢжүҝеҢ… пјҢ йҮ‘иқүи„ұеЈі гҖӮ зӣҙеҲ°жңҖеҗҺд№ҹжІЎдәәдёҠеҪ“ пјҢ жңәеҷЁе…ЁзғӮеңЁдәҶеұұдёҠ гҖӮ
йӮЈж®өж—ҘеӯҗжһҒеәҰиӢҰй—· пјҢ еӨ§е®¶дёӢдәҶзҸӯеңЁжҙһеӯҗйҮҢжү“йә»е°Ҷ пјҢ з”Ёи’ёеұүд»ЈжӣҝжЎҢеӯҗ пјҢ жҗҒеңЁи…ҝдёҠжү“ гҖӮ еҸӘжңүдёҖеүҜйҷ•иҘҝеёҰеҺ»зҡ„йә»е°Ҷ пјҢ иҪ®жөҒжү“ пјҢ жү“еҲ°жңҖеҗҺдёўдәҶеҮ еј зүҢ пјҢ 继з»ӯжү“ гҖӮ еҰӮжһңеҲҡеҘҪе’ҢйӮЈеҮ еј пјҢ вҖңиҜҘеҖ’йңүвҖқ гҖӮ
еҪ“ең°зҡ„й…’ пјҢ 50еқ—й’ұ50ж–Ө пјҢ дҫҝе®ңдҪҶйҡҫе–қ гҖӮ йҷҲе№ҙе–ңиҜҙйӮЈйҳөеӯҗжҜҸеӨ©йғҪиҰҒеҙ©жәғ пјҢ еӨ§е®¶е–қй…’е”ұжӯҢ пјҢ е”ұзҡ„жҳҜеӯқжӯҢ гҖӮ дёҖиҲ¬зҹҝиҖҒжқҝдёҚи®©е”ұйӮЈдёӘ пјҢ дҪҶеңЁиҝҷе„ҝж №жң¬жӢҰдёҚдҪҸ гҖӮ жӣІи°ғеҮ„еҺүйў“дё§ пјҢ д№қжӣІеҚҒе…«з»•пјҡвҖңеҫҲеӨҡеүҚжңқеҸӨдәәиҜҙ/жҙ»еңЁиҝҷдёӘдё–дёҠжңүд»Җд№ҲжқҘеӨҙ/дәәжӯ»дәҶе°ұжӯ»дәҶ/家иҙўдёҮиҙҜйғҪдёҚиҰҒдәҶ гҖӮ вҖқ
йҷҲе№ҙе–ңеҸ‘зғ§е’іе—Ҫ пјҢ еұұдёӢжҖ»йғЁжңүдёӘ家乡еёҰжқҘзҡ„еҢ»з”ҹ пјҢ жҗӯдәҶдёӘе°ҸиҜҠжүҖ пјҢ еҢ»з”ҹз»ҷд»–ејҖдәҶжё…ејҖзҒө пјҢ дёӨй’Ҳжү“дёӢеҺ» пјҢ д»–ејҖе§ӢиҝҮж•ҸжҠҪжҗҗ пјҢ ж•ҙдёӘдәәжҠҪжҲҗдёҖеӣў пјҢ жҷ•дәҶиҝҮеҺ» гҖӮ
еҺҝеҹҺеҢ»йҷўдёҚд»…иҝң пјҢ иҖҢдё”и·ҜйҖ”йў з°ё пјҢ жӣҫжңүдёҖдёӘе·ҘеҸӢиў«з ёж–ӯдәҶиӮӢйӘЁ пјҢ йҷҲе№ҙе–ңйҖҒд»–еҺ»еҢ»йҷў пјҢ еҗүжҷ®иҪҰеңЁжҲҲеЈҒдёҠйў дәҶдёҖеӨ© пјҢ йӮЈдёӘдәәз—ӣеҫ—жұ—жөҒжөғиғҢ пјҢ д»–иҜҙ пјҢ вҖңе“ӘжҖ•и®©жҲ‘жӯ»еңЁиҝҷйҮҢ пјҢ з®—дәҶеҗ§вҖқ гҖӮ
еҢ»з”ҹиҜҙ пјҢ жӢүеҺ»еҢ»йҷўд№ҹжқҘдёҚеҸҠ пјҢ жҳҜжӯ»жҳҜжҙ»еҗ¬еӨ©з”ұе‘ҪдәҶ гҖӮ д»–еҫҖйҷҲе№ҙе–ңиә«дёҠжіЁе°„жҝҖзҙ иҚҜ пјҢ жүҖжңүиҚҜйғҪжү“е®ҢдәҶ пјҢ дёҖе…ұ54й’Ҳ гҖӮ дёҚзҹҘйҒ“иҝҮдәҶеӨҡд№… пјҢ йҷҲе№ҙе–ңйҶ’иҝҮжқҘ пјҢ еәҠдёҠзҡ„иў«еӯҗиў«д»–еңЁжҠҪжҗҗдёӯж’•еҫ—зЁҖзғӮ пјҢ вҖңжҲ‘зңҹзҡ„е·®зӮ№е°ұжӯ»еңЁйӮЈдёӘең°ж–№дәҶвҖқ гҖӮ
йҷҲе№ҙе–ңе’ҢеҮ дёӘе·ҘеҸӢе•ҶйҮҸ пјҢ дёҚиғҪдёҚйҖғдәҶ гҖӮ йҖғдәҶдёҖеӨң пјҢ еҲ°еұұдёӢзҡ„е°Ҹй•Үж—¶еӨ©еҝ«дә®дәҶ гҖӮ 他们еҢ…дәҶдёҖиҫҶиҪҰ пјҢ еҲҡеқҗдёҠеҺ» пјҢ е°Ҹе·ҘеӨҙд»ҺеҗҺйқўејҖзқҖиҪҰиҝҪдёҠжқҘдәҶ гҖӮ д»–еҫҖең°дёҠдёҖи·ӘпјҡвҖңдҪ 们иҰҒжҳҜиө°дәҶ пјҢ жҲ‘иә«е®¶жҖ§е‘ҪйғҪдјҡдёўеңЁиҝҷйҮҢ гҖӮ вҖқ
жҺЁиҚҗйҳ…иҜ»
- дәҺиҗҪеҜһдёӯеүҚиЎҢвҖ”вҖ”дё“и®ҝиҜ—дәәиө«иө«жү¬жү¬|дәҺиҗҪеҜһдёӯеүҚиЎҢвҖ”вҖ”дё“и®ҝиҜ—дәәиө«иө«жү¬жү¬
- жөҷжұҹе®Ғжіўй•Үжө·еҢә:ејҖеұ•еәҹејғзҹҝеұұжІ»зҗҶе…¬зӣҠиҜүи®јдё“йЎ№жҙ»еҠЁ
- йҖғеҮә|зҘ–еӯҷ3дәәиҗҪж°ҙпјҢзҲ·зҲ·иҮӘж•‘йҖғеҮәеӯ©еӯҗеҚҙжәәж°ҙиә«дәЎпјҢ家дәәеӨұеЈ°з—ӣе“ӯ
- еҸӨд»ЈйЎ¶зә§иҜ—дәәпјҢеҶҷиҜ—жңүеӨҡеҝ«пјҹ
- е°Ҹ欧еңЁзәҝ|ж№–еҚ—зӣҠйҳіиҖҒдәәй©ҫиҪҰжҺүиҝӣжІійҮҢпјҢиҮӘж•‘йҖғеҮәпјҢ2дёӘеӯ©еӯҗжІЎиғҪж•‘еҮәпјҒ
- еқ жІі|2е°Ҹеӯ©еқҗзҲ·зҲ·з”өеҠЁиҪҰеқ жІіжәәдәЎ зҲ·зҲ·иҮӘж•‘йҖғеҮә
- зҲ·зҲ·|зҲ·еӯҷ3дәәйӘ‘иҪҰеҶІиҝӣжІідёӯпјҢзҲ·зҲ·иҮӘж•‘йҖғеҮәпјҢ3еІҒеӯҷеӯҗе’Ң10еІҒеӯҷеҘіжәәдәЎпјҒ
- 2е°Ҹеӯ©еқҗзҲ·зҲ·з”өеҠЁиҪҰеқ жІіжәәдәЎ зҲ·зҲ·иҮӘж•‘йҖғеҮә
- и§Ҷйў‘пҪңгҖҠеҗҜеҸ‘дҝұд№җйғЁгҖӢпјҡдҪ йҖғеҮәвҖңй«ҳиҖғжЁЎејҸвҖқдәҶеҗ—пјҹ
- еҹҺеёӮ|жңҖзҘһеҘҮеҹҺеёӮпјҒиў«е…ЁеӣҪдәәзӢӮйӘӮпјҢдҪҶеҚҙжІЎжңүи°ҒиғҪйҖғеҮәе®ғзҡ„еҘ—и·Ҝ